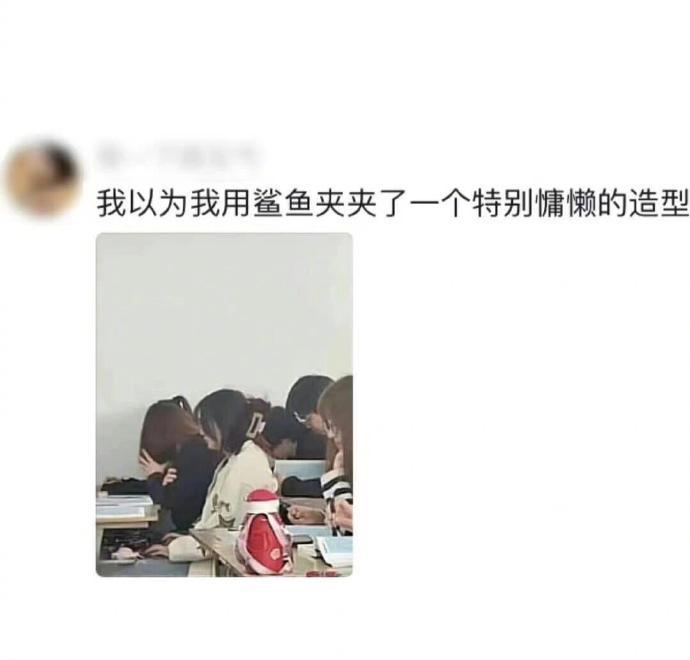1968年,张大千的四姨太徐雯波,正跪在地上拜师,她妆容精致,发型讲究,一身华丽的旗袍,勾勒出她娇好的身材,身上的珍珠项链和手镯首饰,让她显得尊贵又洋气,的确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8年,一张拜师仪式的老照片悄然定格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时光,画面中,39岁的徐雯波穿着合身的旗袍,脖颈间佩戴着一串温润的珍珠项链,手腕上环绕着精巧的首饰。 她双膝跪地,姿态优雅,眉目安然,侧脸略显低垂,却掩不住她骨子里流露出的沉静与自信,那一刻,她不是某位名人的夫人,也不是哪个家庭主妇,而是一位即将迈入艺术更高门槛的求道者。 身旁端坐的马寿华衣着庄重,神情肃穆,他是书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而站在角落、略带笑意的张大千,则在注视着这场意义非凡的仪式,他早年成名,如今功成名就,站在那里,也只是一个妻子的见证者。 这场拜师看似寻常,实则是徐雯波对自我身份的再一次确立,她并非凭借婚姻获得艺术地位的附属者,也不仅是张大千生活里的陪伴者,在这一跪之前,她用了整整二十五年,从一位成都少女,走到今天这座台前。 1920年,徐雯波出生于四川成都,自幼寄居于城中姑母家,家境不富,但她从小便喜好绘画,对丹青纸墨充满兴趣。 没有专业师资的指导,她靠着自己琢磨模仿,一笔一划地描画山水花鸟,少女时的她清丽端庄,举止温婉,但骨子里却藏着一股不动声色的坚韧。 1943年,她第一次进入“大风堂”,那时的张大千刚从敦煌考察归来,心中郁结烦闷,大女儿张心瑞带着闺中好友来访,徐雯波因此走入了这位画坛巨匠的视野。 那一年,她十四岁,眉眼清澈,衣着素净,对书画充满敬仰之意,张大千惯来不喜外人入画室,但这一次,他破了例。 少女对艺术的渴望唤起了他内心深处久违的柔情,原本不快的心情也因此松动,从那天起,徐雯波频繁出入张府,以学生的身份向他请教画理,日久生情的种子悄悄埋下。 此后几年,张大千与妻妾的关系渐趋紧张,原配黄凝素离意已决,而徐雯波在家中姑母的保护下,依旧坚持学习,逐步赢得张大千的欣赏与信任。 1947年,张大千年届四十八岁,正式迎娶年仅十八岁的徐雯波,舆论难以平息,但她知自己在选择什么,也明白自己要付出什么。 婚后的徐雯波没有沉溺于生活的安逸,她继续钻研绘事,在张大千身边不仅是妻子,更是研习者、合作者与记录者,每次外出写生,她总是随行,在山水古迹之间捕捉灵感的踪影。 她的画作既延续了张氏的雄浑潇洒,又悄然发展出自身独有的细腻与柔婉,对她而言,绘画不仅是夫妻间的交流方式,更是个人价值的拓展路径。 几十年的相守中,徐雯波面对的不只是笔墨丹青,迁徙香港、旅居巴西、定居台湾,生活不断变迁,家族成员众多,张大千的感情经历也远非简单单一。 她默默包容,一直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理解张大千性情中对自由与浪漫的执着,也深知维系长久关系靠的不是束缚,而是识趣。 那场拜师仪式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她的身份,也因为她的选择,马寿华作为艺坛泰斗,其门下弟子极为严选,徐雯波主动提出拜师,是在丈夫之外,为自己的艺术道路另辟一条支线。 这不仅为她赢得“正统承认”,更是在画界公开宣示:她的身份不仅是某某之妻,更是某某之徒,是一个拥有自我技艺脉络的独立个体。 张大千对此表示支持,从照片中他的神情来看,那一刻他并不主导,也不反对,他选择站在一旁观看,让妻子完成她艺术人生的一个转身,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默许的尊重。 1983年,张大千病逝台北,留下遗产分配清单,其中将绝大多数财产交由徐雯波继承,这个安排外界或许诧异,徐雯波却始终未曾炫耀,她继续居住在两人旧居中,整理书画,接受访客,偶尔也会重新拿起画笔。 时光远去,那张1968年的照片依旧清晰,那一跪,是仪式,是节点,更是一个女人默默奋斗多年之后,为自己争取到的公开肯定,她端坐其间,如一朵盛开的花,在自己的时区里,静静地绽放。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百度百科——徐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