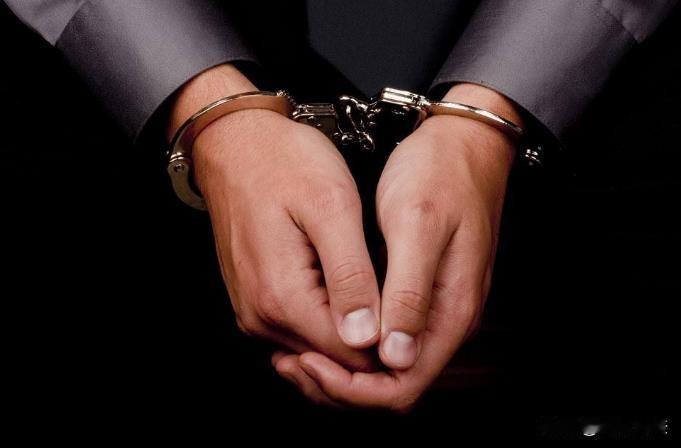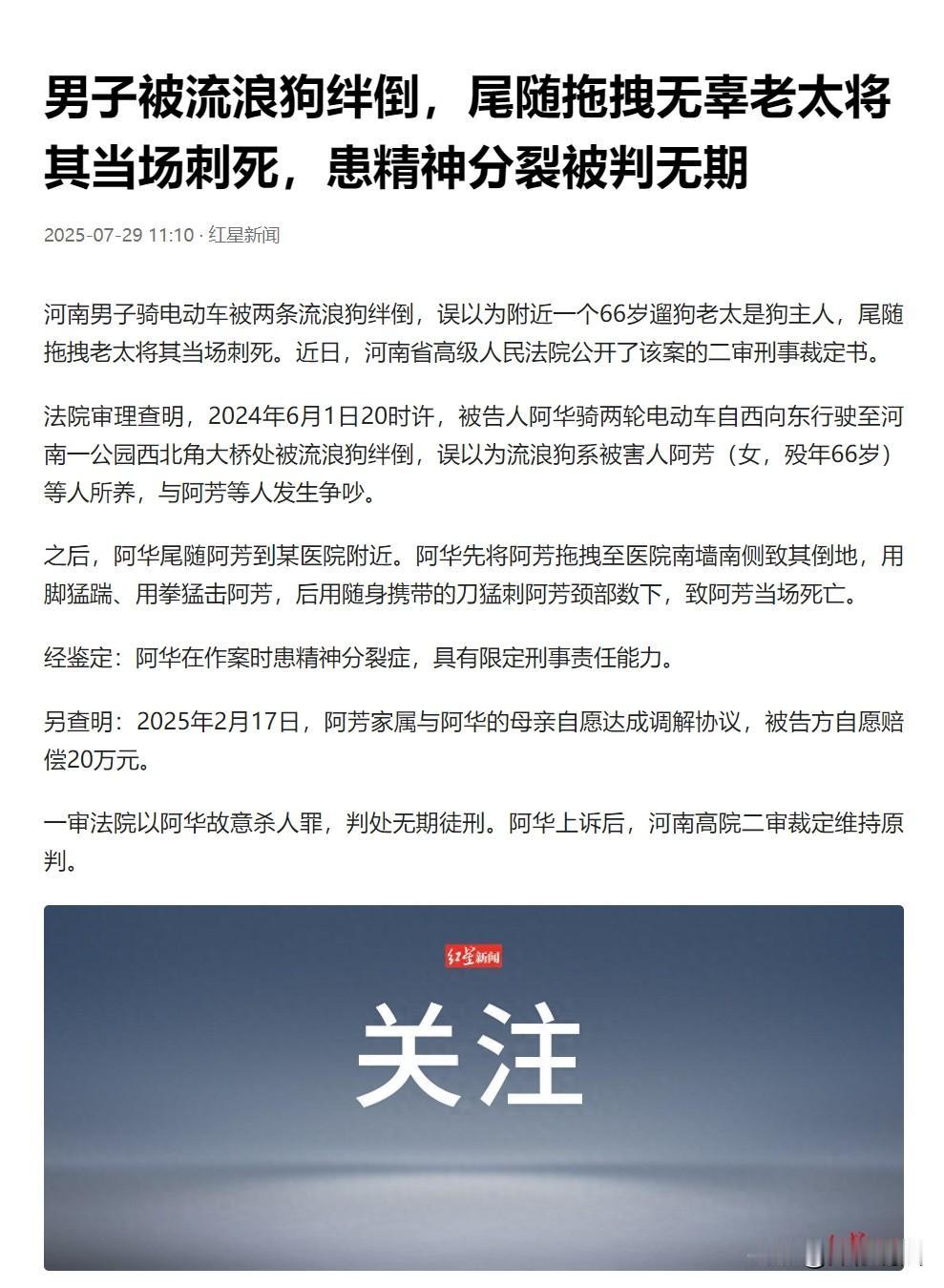河南,一小伙骑电驴被窜出的流浪狗绊倒,怒火中烧,错将附近遛狗的老太认作狗主,争吵无果,老太牵狗离开。不料,小伙在偏执驱使下,骑车尾随老太百米,在墙边将她猛拽倒地,还他掏出刀子,对着老太脖颈连捅数下,无辜的老太当场殒命。事后,小伙被诊断有精神分裂症,家人积极赔偿20万元获得老太家属谅解,以此换得重 活一次。一审法院判处小伙无期徒刑,小伙不服,认为处罚过重,继续上诉,二审法院这样判决。 据悉,某公园内,66岁的阿芳(化名)像往常一样牵着自家小狗在河边遛弯,路灯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 与此同时,25岁的阿华(化名)骑着一辆旧电动车,匆匆驶过公园西北角的大桥。 突然,两条追逐打闹的流浪狗窜到路中间,阿华躲避不及,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地。疼痛瞬间点燃了他的怒火。 他挣扎着爬起,目光扫向四周,恰在此时,阿芳牵着她的小狗从不远处经过。 在阿华混乱的思维里,那两条惹祸的流浪狗与阿芳的身影瞬间重叠,他认定:“就是她!她的狗害其摔倒!” 阿华冲上前去,不由分说地质问阿芳为何不管好自己的狗。阿芳一脸惊愕与茫然,连忙解释:“小伙子,你认错人了,那不是我家的狗,是没主人的野狗!”周围有人也帮着澄清。 但在阿华偏执的认知里,这些辩解都成了推卸责任的谎言。争吵了几句,阿芳觉得这人不可理喻,便牵着狗转身离开,想尽快摆脱这个纠缠不清的年轻人。 阿华已经失控,不打算放过阿芳,骑着车,远远地尾随着阿芳瘦小的身影。阿芳走到了医院附近,全然不知危险已如影随形。 突然,阿华猛地加速冲上前,一把将阿芳从人行道上粗暴地拖拽到医院南墙外的暗处,阿芳惊恐的呼救声还未完全出口,就被重重摔倒在地。 阿华没有停止,继续疯狂地用脚猛踹、用拳头狠砸地上的阿芳。 更可怕的是,他还掏出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刀,对着阿芳脆弱的颈部,连续、凶狠地刺了下去,阿芳当场不治身亡。 很快,阿华被警方抓获。 没想到的是,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阿华在作案时正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他当时对自身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疾病而显著削弱,但是,并未完全丧失,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 之后,在各方促使下,阿芳家属与阿华的母亲艰难地坐到了一起,自愿达成了一份调解协议:阿华的家人愿意一次性赔偿阿芳家属人民币2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阿华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结合其责任能力及积极赔偿等情节,判处阿华无期徒刑。 阿华认为一审判决刑罚畸重,遂提出上诉。 那么,二审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法院认为,阿华虽然错怪了阿芳,本意不是要伤害阿芳,属于对象错误,但这并不影响其构成故意杀人罪。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阿华主观上具有明确的杀人故意,他意图杀害他当时认为的“狗主人”即阿芳,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刺杀阿芳,结果导致阿芳死亡的结果。 故意杀人罪在法律上评价的是犯罪分子主观认知和客观行为的结合,而不是非得杀害对象必须与主观认定的对象一致,无论被害人是否真的是狗主人,均不影响其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阿华认为,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且家属事后积极赔偿取得阿芳家属的谅解,理应判处更轻的处罚,一审判决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第18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认可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即阿华作案时患精神分裂症,属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是,阿华依然要负刑事责任,且该条款说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只是作为考量因素而已。 同时,积极赔偿取得谅解在《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也只是酌定从宽情节,并不意味着必须依法酌减刑罚。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事实上已经考量了阿华是精神分裂患者以及积极赔偿取得谅解的情况,否则判处的刑罚只会更重。 在法院看来,阿华手段残忍、结果致命、社会影响恶劣,已达到故意杀人罪中后果“特别严重”的程度,最高可以处死刑。 正是因为基于赔偿谅解以及精神疾病因素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量,否则阿华在如此恶劣的犯罪中,死刑尤其是死缓是可能的选项。 最终,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处罚并无明显不当,依法驳回阿华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