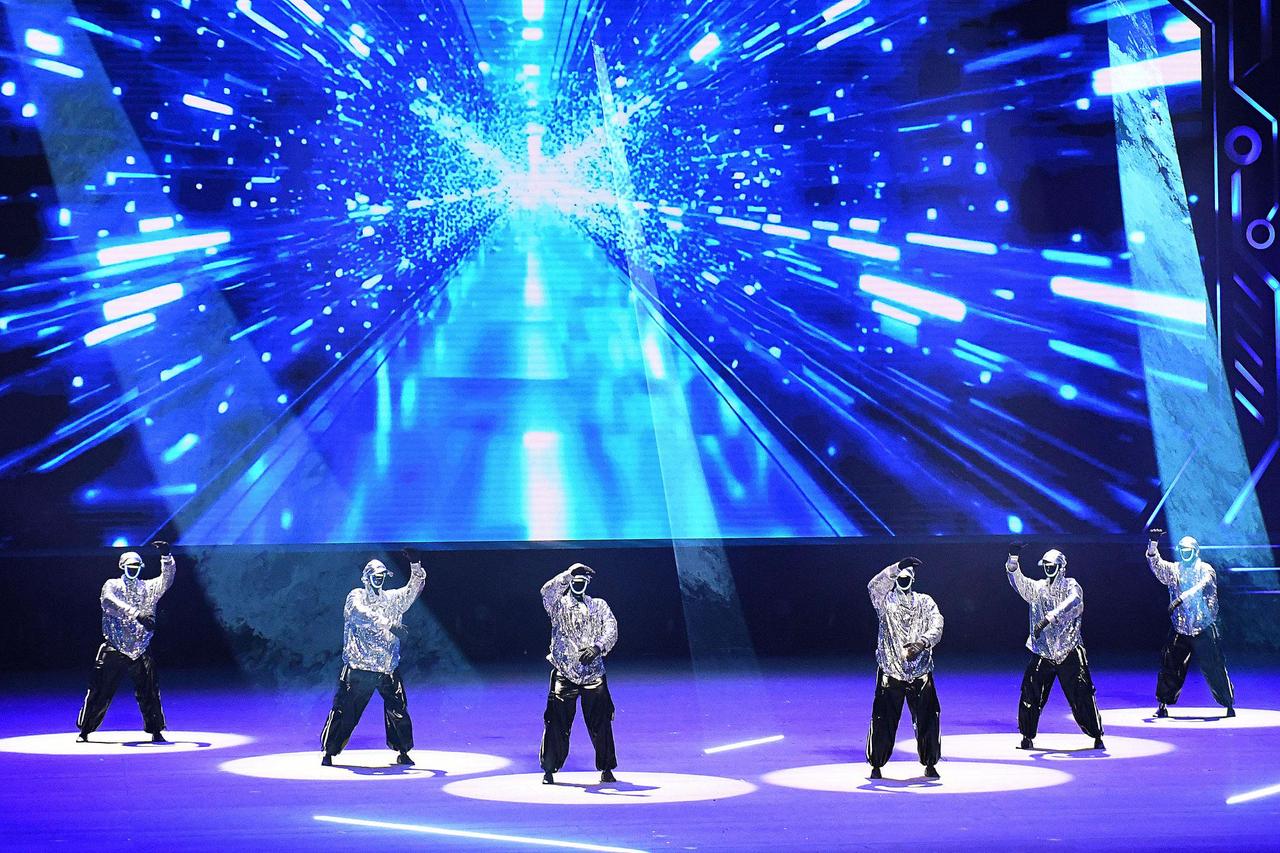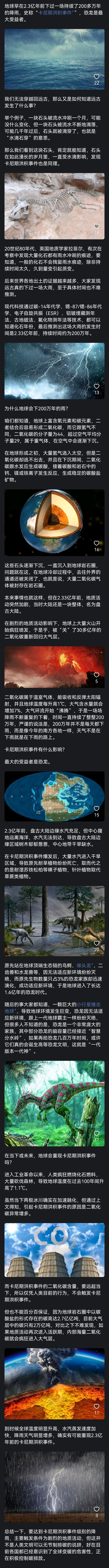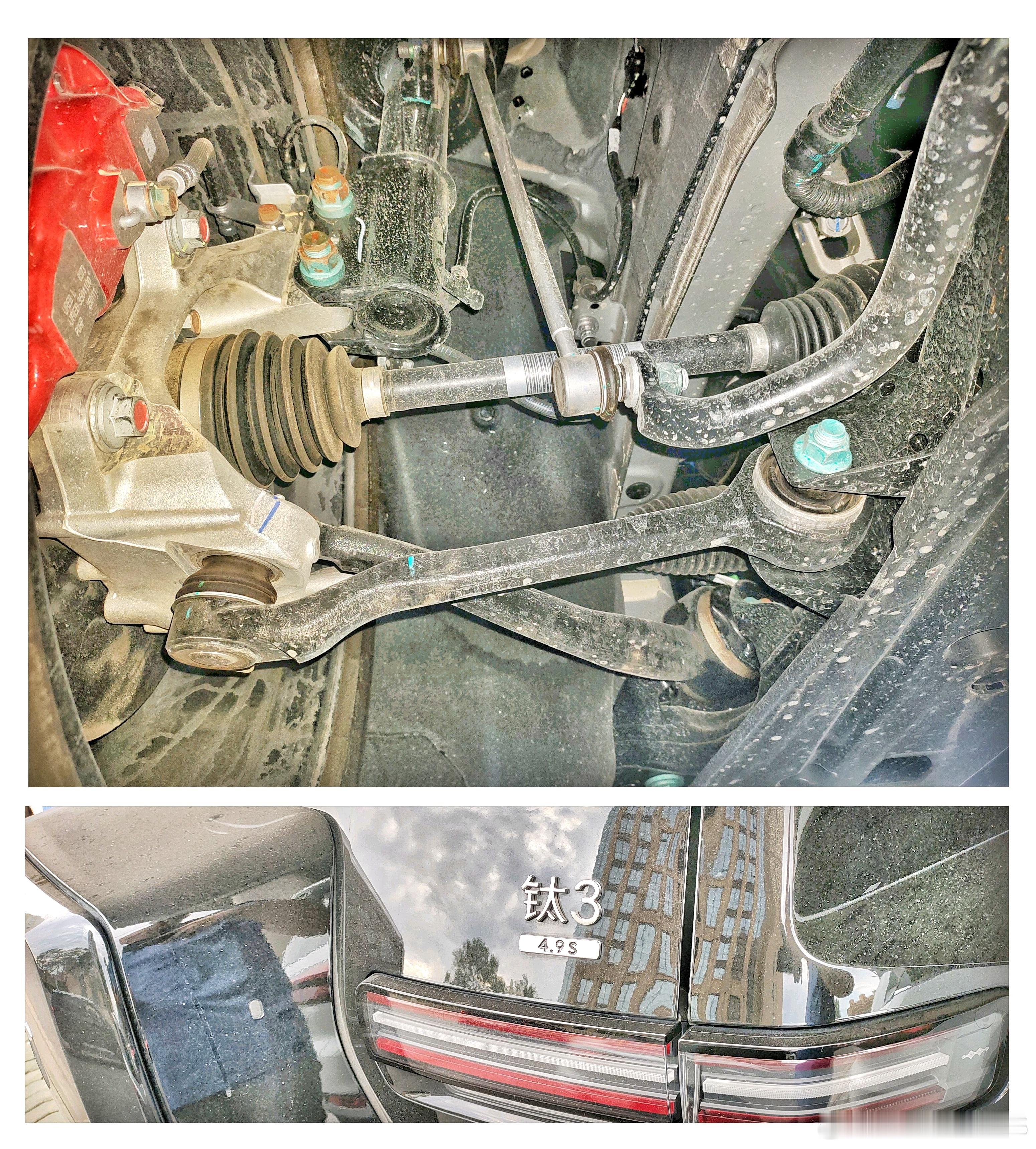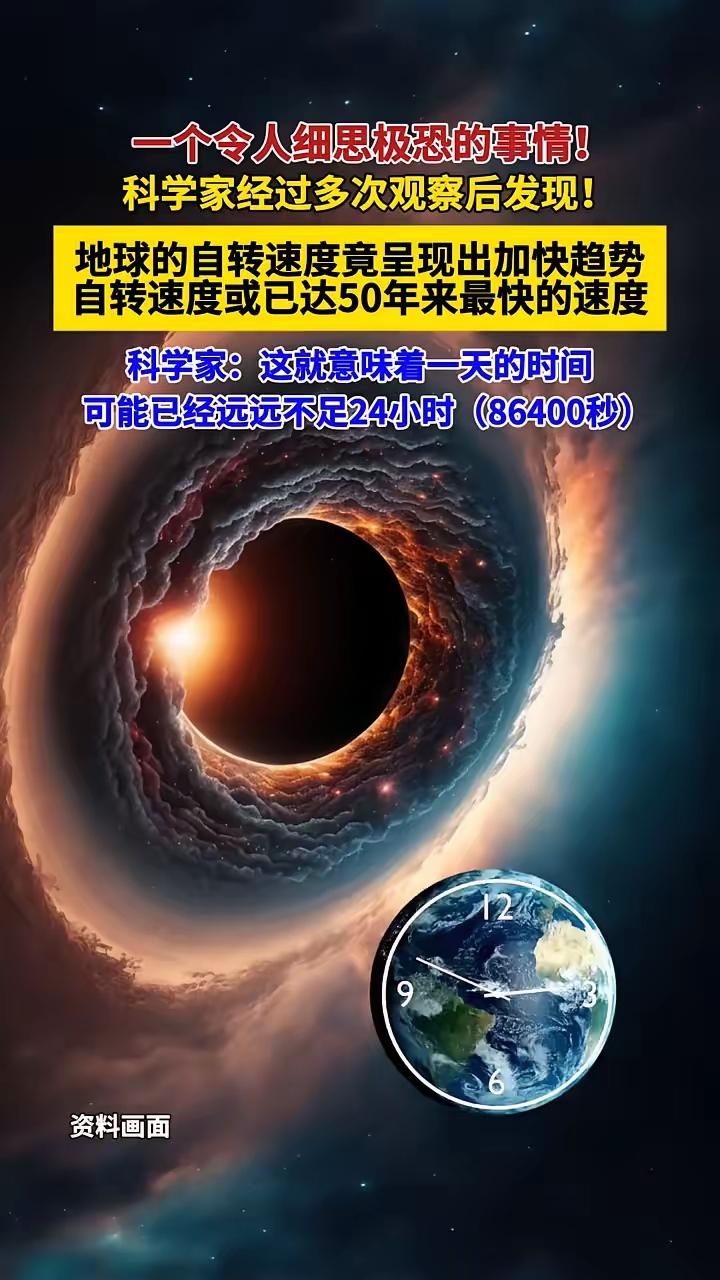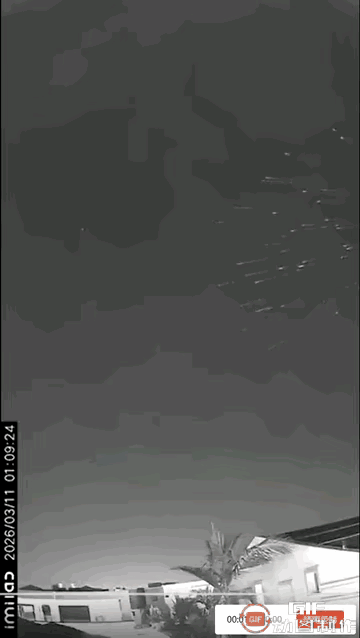全红婵逃不过基因!可能真的是基因太强大了,你说发育吧,哪个女孩不发育呢?之前很
全红婵逃不过基因!可能真的是基因太强大了,你说发育吧,哪个女孩不发育呢?之前很多跳水的女孩也没有这么夸张,她的教练现在身材也不错。不过也无所谓了,跳水本来就是吃青春饭的,她和很多女孩子比运气已经很好了,参加两次奥运并且都得冠军了,已经很圆满了。把两届奥运冠军轻描淡写归成运气,这话听着就很刺耳。全红婵的金牌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靠所谓“没发育”的身材占便宜。东京到巴黎,她每天天不亮就进馆,晚上练到熄灯,一天几百次起跳入水,脚踝缠着肌贴、腰带着劳损,这些苦没人替她扛。网友早就看不惯这种论调,有人直接留言,拿运气否定一个少年的拼命,既不懂体育,也不懂尊重。发育这件事被拿出来反复说,本身就带着偏见。女运动员到了年纪长身高、长体重,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规律,偏偏到了全红婵身上,就成了被围观、被评判的话题。最近她公开亮相,只是身形比以前结实一点,就被揪着身材吐槽,甚至拿造型和体态挑刺。键盘侠盯着镜头里的一厘米一公斤,却看不见她为了适配新身体,把每个动作拆了重练,把核心力量从头打磨。更离谱的是,有人把跳水的青春属性,当成贬低运动员的理由。青春饭不假,但能把青春饭吃到两届奥运登顶,本身就是顶级实力。陈若琳当年也闯过发育关,照样成为传奇,全红婵也在走同样艰难的路。国家队没有放弃她,教练组一直在帮她调整技术、管理身体,她自己也没躺平,该减重减重、该加练加练,这样的态度,配得上所有掌声。网友的态度分得很清。心疼她的人占大多数,大家反感的是用网红审美绑架为国争光的孩子,反感把生理变化当成攻击点。也有理性声音说,竞技体育有残酷,但不该把残酷变成对运动员的恶意。她才十几岁,已经站到过世界之巅,就算未来有一天离开跳台,她的名字也会留在跳水历史里。用“基因”“运气”概括全红婵,是对努力最廉价的消解。她的传奇不是靠身材,是靠每一次咬牙坚持,靠每一次不认输。我们更该关注她的热爱与坚韧,而不是盯着青春期的正常变化说三道四。全红婵打分争议全红婵奶茶挑战你觉得外界对全红婵的身材讨论,是不是太苛刻了?你心里她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