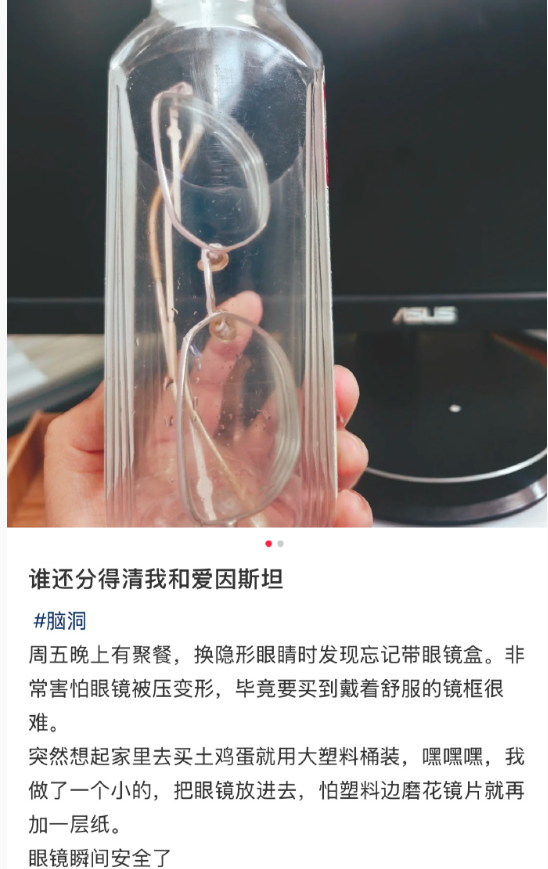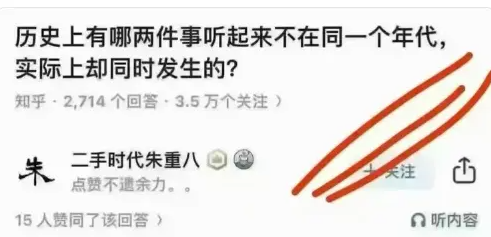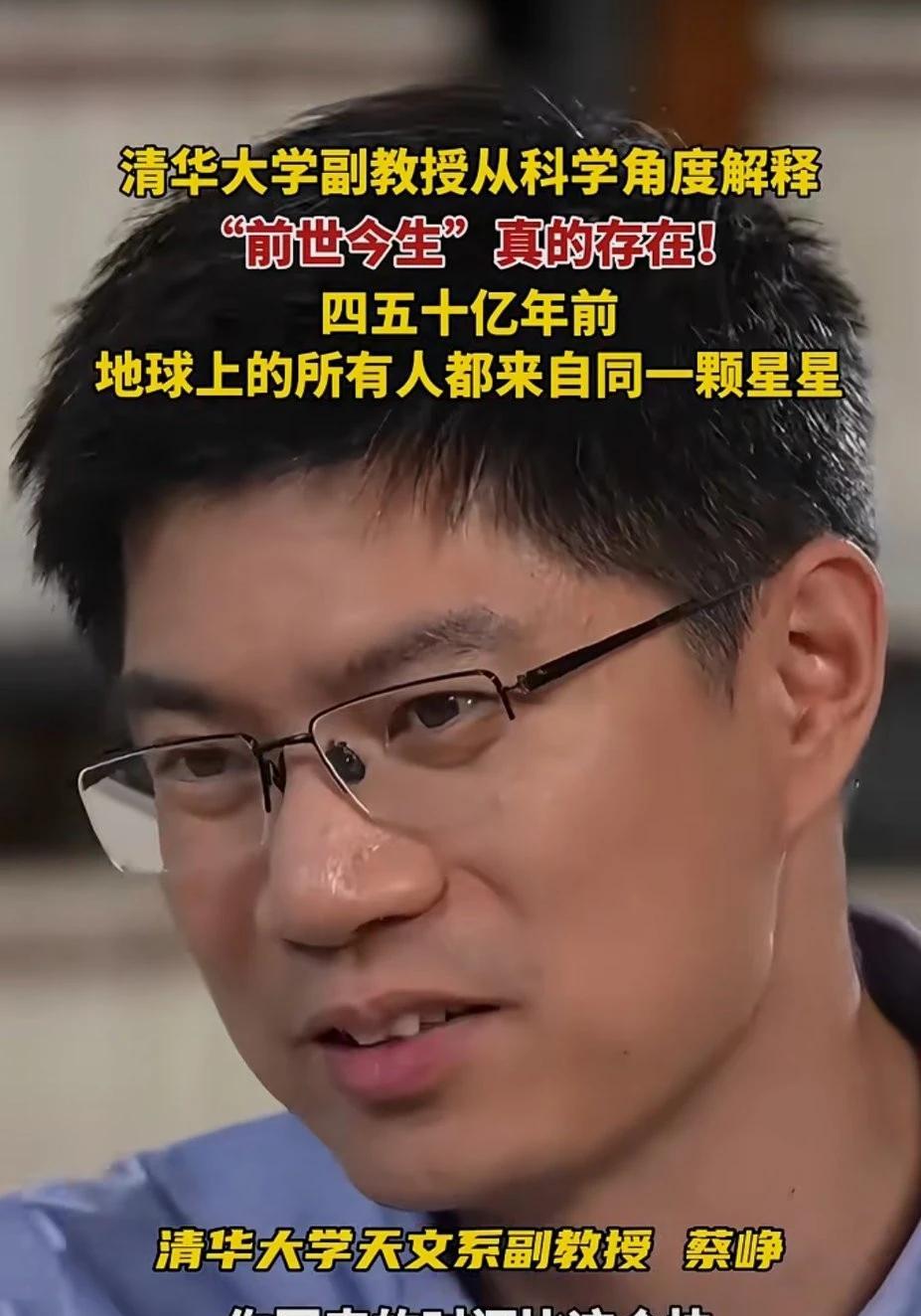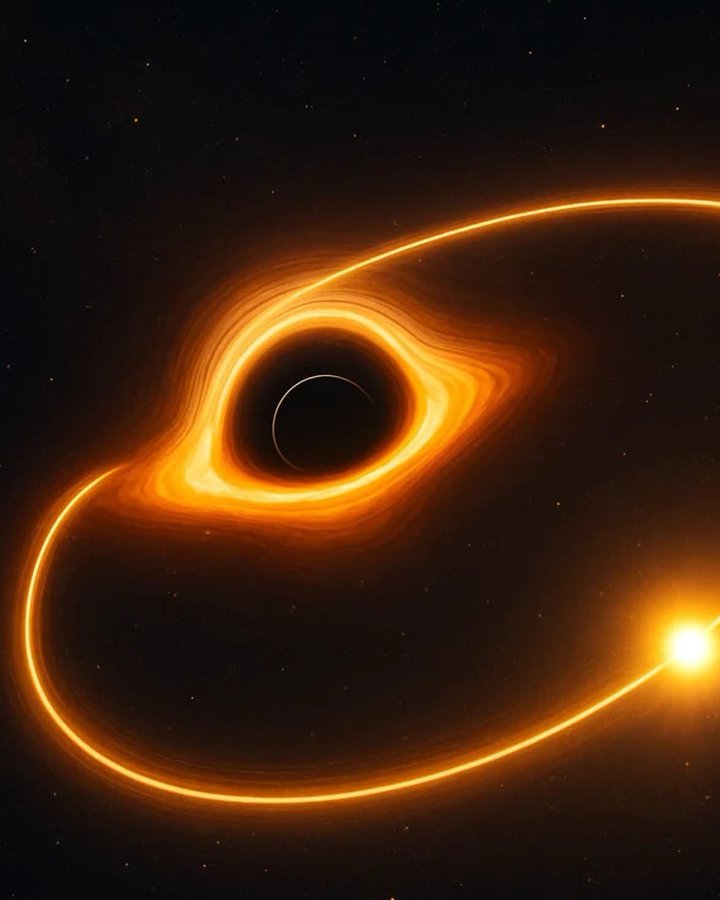2012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阻止建造2000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这也惹怒了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气的他不顾形象大声道:一定要建!不建中国落后30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12年初夏,北京香山的一场科学会议让整个物理学界都记住了一个瞬间,会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一度红着眼眶,拍着桌子喊出一句话:“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就要落后三十年!”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静得出奇,许多人手里的笔都停在了纸面上,这场争论的另一方,是坐在不远处、手拄拐杖的杨振宁,他的声音不大,却每一个字都像石子投进湖面:“这件事不该现在做,太急了,也太贵了。” 这场对峙的背景是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成功发现“希格斯粒子”,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兴奋不已。 那台位于瑞士和法国交界处的大机器让人类第一次直接看到理论上存在的“上帝粒子”,消息传到中国,国内物理学界沸腾起来,很多人都觉得这是追赶世界前沿的好机会。 王贻芳带领的团队提出,要在中国建造一台更大、更先进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周长100公里,比欧洲那台要大出不少,预计一年能产生更多的数据,也能更精确研究粒子特性。 他们写下了厚厚的方案,预算是两千亿人民币,方案一提出,争议立刻爆发,杨振宁的反对格外引人注意。 他曾经在美国亲历过一个规模类似的项目——超导超级对撞机,投入了几十亿美元,最后因为资金紧张、技术困难被美国国会叫停,留下大片荒地和报废的隧道。 他清楚记得那场科学界的失望与反思,他算了一笔账,两千亿意味着全国每个人都要分摊一笔不小的钱,而中国当时还有上亿农民年收入不足一万元,他担心的不只是钱,还包括人才储备。 当时国内高能物理领域年轻科研人员流失严重,博士生大量去了国外做研究,就算机器建成,真正能独立开展顶尖实验的队伍也不够强大,可能还是要依赖国外专家来主导。 王贻芳则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带领团队在大亚湾做过中微子实验,发现了新的振荡模式,让中国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国际物理学教科书里。 他深知没有顶尖实验设备,中国科学家总要用别人建的机器,科研方向受制于人,如果错过这次窗口期,等欧洲和日本完成下一代对撞机,中国再想追赶就要落后很久。 会议上,他的语气一次比一次坚定,手都在发抖,说国家不能一直跟在别人后面跑,那几天,支持和反对的人在会议室里争得面红耳赤。 有人列举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带动的国际人才流动和产业升级,说这不仅是科学,更是未来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反对的人则搬出美国失败的案例,说这个项目可能成为财政黑洞,科学界外部的声音也很嘈杂,普通网友、经济学家、数学家都加入讨论,有人说要敢于梦想,有人说要先把地基打牢。 争论一直持续,没有结论,国家后来没有立即批准对撞机项目,科研经费被投入到多个领域,中国接下来的十年里,在量子通信、深空探测、人工智能、核聚变等方向接连取得突破。 贵州的“中国天眼”探测到深空脉冲星,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刷新核聚变纪录,航天工程里“天宫”和“嫦娥”也先后亮相,基础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加,科研队伍也逐渐壮大。 王贻芳没有放弃,团队继续改进方案,控制成本,把进口依赖降到最低,他们建起新的中微子实验站,积累经验,希望未来有机会再推动大型对撞机立项。 杨振宁在后来的演讲中仍然强调,真正的科研实力要靠长期的人才培养和厚实的基础,他希望年轻人能安心坐在实验室里沉下心做研究。 十多年过去,人们再回看那场争论,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情绪对立,杨振宁的担忧避免了当时可能的巨大资源浪费,王贻芳的坚持推动了中国科学界去思考如何更快追上世界。 那一次交锋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却让科学项目的决策不再只停留在少数专家手中,社会公众也开始关注科研投入和优先级。 科学发展不是一场百米冲刺,需要有人探路,也需要人稳扎稳打,那一天香山会议室里的两种声音,成了中国科技道路上最真实的一道印记。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中国青年网——杨振宁反对建超大对撞机 中科院专家反驳:机遇难得 央广网——中科院专家反驳杨振宁:建造大型对撞机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