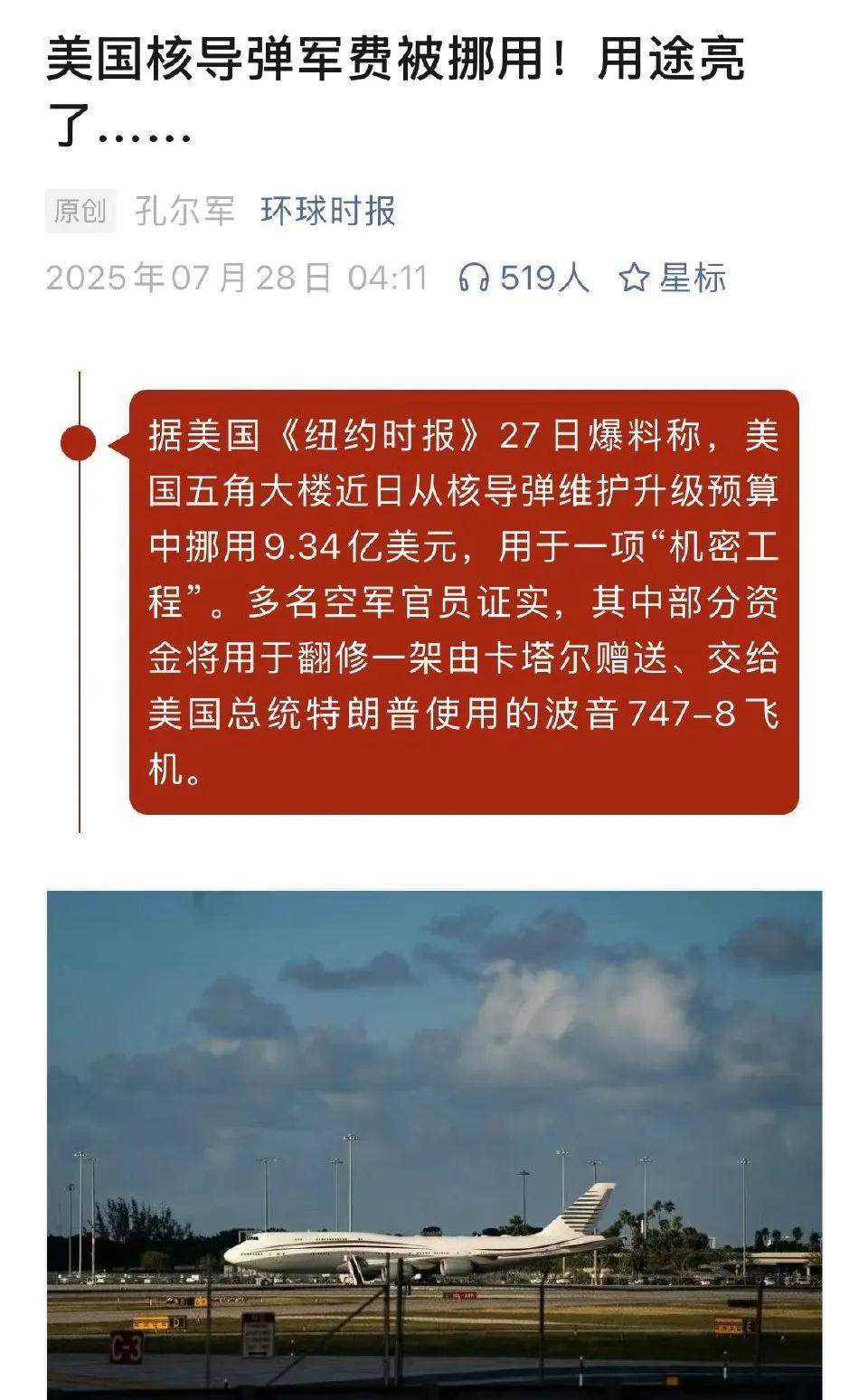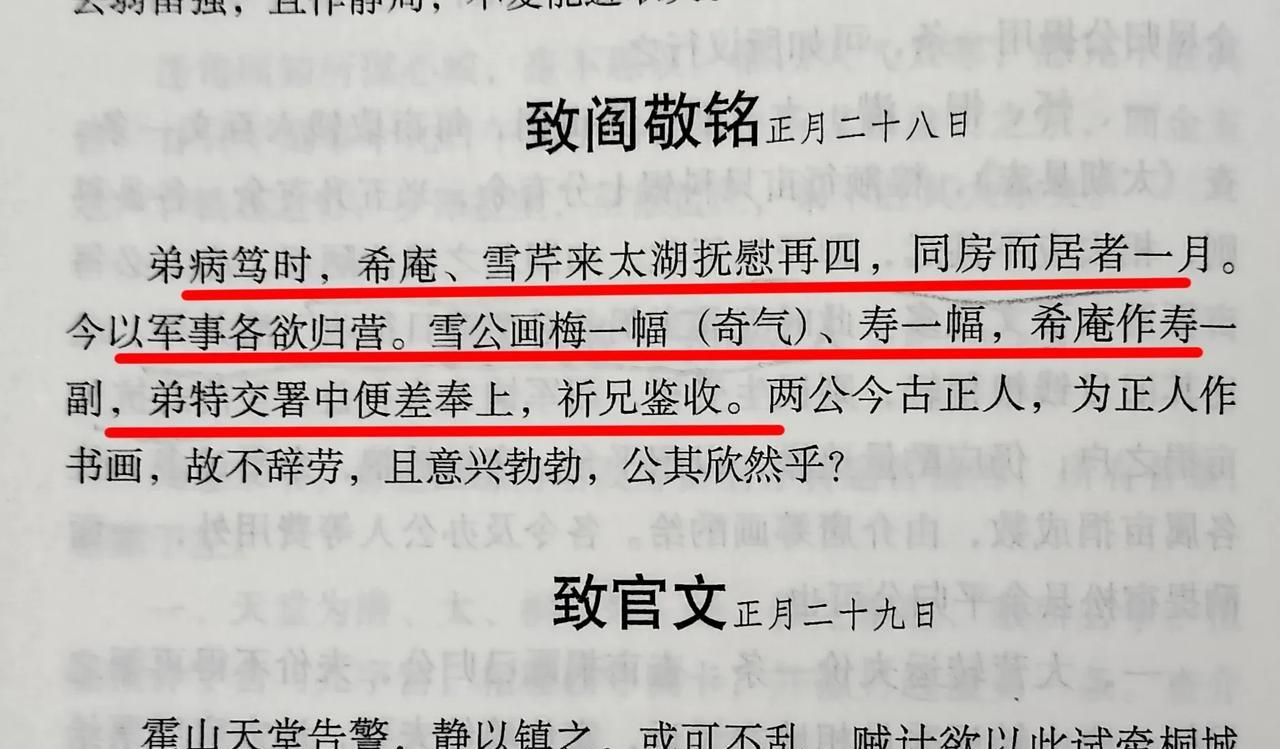李鸿章的侄子李秋升欺行霸市,女子的丈夫将他告到了彭玉麟那里,没想到彭玉麟丝毫不顾李鸿章面子,下令斩首,顺便还修书一封告知李鸿章,我替你杀了这个败坏门风的侄子,不用谢!
1872年深秋的安庆城,江雾裹着压抑的市井,连石板路上的马蹄声都透着小心翼翼,李鸿章的侄子李秋升,正把这座长江重镇变成自家的猎场。
街边米铺老板缩在柜台后,眼见李秋升的家丁踹开铁匠铺的门,拖出个挣扎的少女。
铁匠的儿子扑上去阻拦,被棍棒砸得蜷缩在地,血水渗进青砖缝里。
围观者死死攥着拳头,却无人出声。
知府衙门的鼓早已蒙尘,上一次有人击鼓鸣冤,状纸刚递就被撕得粉碎。
而当彭玉麟的官船泊在安庆码头时,刻意卸了钦差旗号。
这个以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闻名的湘军老将,裹着青布衫混入人群。
突然城隍庙前的哭嚎引他驻足,只见一个老妇跪在衙役脚边,额头磕出血痕。
原来就在三天前,她十六岁的孙女翠儿被掳进李宅,未婚夫上门讨人,被打得呕血丢在门外。
门外的百姓的窃语针般刺进彭玉麟耳中,去年打死王屠户的儿子,尸首都沉了江,李中堂的侄儿,知府大人也只敢装聋!
他顺着青石板踱到李府朱门外,佯装撞翻挑夫的水桶。
门缝里的一瞥让他浑身血冷,庭院深处绣楼上,穿湖蓝缎袍的李秋升捏着少女下巴灌酒,地上蜷缩的少年正是集市上奄奄一息的铁匠之子。
雕花廊柱映着暮色,像一张吃人的巨口。
不大一会之后女子的丈夫看到码头上钦差的旗号于是一路跟随至此,向彭玉麟告状,求他做主。
要说这彭玉麟可是被评价为晚清重臣中兼具军事才能与清廉品格的代表人物。
以铁腕反腐、刚正不阿的作风闻名,被民间称为“活阎王”,同时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民本思想。
可以说就算是皇帝犯错了他都会上去参一本,他就是这么勇,就是这样的刚正不阿。
就在次日卯时,城隍庙临时公堂烛火通明。
彭玉麟的尚方宝剑横置案头,当他的亲兵拖来李秋升时,此人缎袍松散,醉眼斜睨。
此时的李秋升以为只要像往常一样搬出他叔父的名号就会和往常一样乖乖的放了他。
我叔父在上海谈洋务,你这老头,话还没说完,惊堂木震得梁上灰簌簌落下。
翠儿掀起衣襟,背上蜈蚣般的鞭痕引来满堂抽气,之后铁匠之子被抬上堂,胸膛纱布渗着黑血。
人证物证具在,刚准备判刑,此时安徽巡抚跌撞闯入。
扑到案前嘶声,大局为重啊!李中堂若动怒,彭玉麟笔尖悬在《大清律例》上,墨迹凝成寒星,你顾的是官场大局,我顾的是人命关天。
只能说李秋升碰到彭玉麟那算是踢到铁板了。
彭玉麟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一切都以法律为准,依法办事,不搞人情事故那一套。
当“绞监候”三字掷地,李秋升终于瘫软如泥,涕泪横流地喊着叔父。
钢刀挥落时,江风卷着鸦群掠过城隍庙飞檐。
百姓从最初的死寂中惊醒,爆竹声突然炸响全城,米铺老板搬出囤了半年的炮仗,铁匠撑着断腿往江边磕头,满街呼喊“彭青天”的声浪,几乎掀翻李府门楣的鎏金牌匾。
官舱内,彭玉麟展开李鸿章半月前的私信。
这位老友笔迹依旧从容,谈论着水师炮舰的改良。
他提笔蘸墨,在素绢上勾勒江涛孤舟,远帆题写“律法如江,至公至平”。
信使疾驰而去时,他摩挲着尚方宝剑的吞口,那里还留着斩首时的余温。
李鸿章的复信在秋雨中抵达。
素笺上不见雷霆震怒,反是清峻小楷,雪琴公治皖,雷厉风行,某深以为幸。
末尾四行诗更让幕僚瞠目,三尺青锋斩佞臣,半幅水墨见冰心。
江淮百姓同声赞,不负当年结拜心。
安庆城的故事随江风流传。
有眼尖者发现,之后李府朱门悄悄换成了黑漆,知府连夜清理积压三年的冤案卷宗。
茶肆说书人拍响醒木,把“彭公斩侄”编成段子,唱词里一句“匪想靠绑架邀功,军民团结把他踹”,惹得满堂喝彩。
而此刻彭玉麟的官船已驶向九江,桅杆上“巡阅长江”的旗帜猎猎作响,他要去斩下一个该斩之人。
这场看似个人恩怨的斩首,实则是腐朽帝国肌体上的一场刮骨疗毒。
当李秋升的头颅滚落,砸碎的是“刑不上大夫”的千年潜规则,李鸿章那封隐忍的道谢信,默认了乱世中比血脉更重的铁律,民心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彭玉麟的钢刀从未妄想劈开晚清夜幕,只求在至暗时刻擦亮一点星火,让缩在米铺后的百姓相信,世上仍有敢对权贵动刀的傻子,愿为草芥争命的疯子。



![慈禧:天道好轮回啊[并不简单]](http://image.uczzd.cn/1582391736871800497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