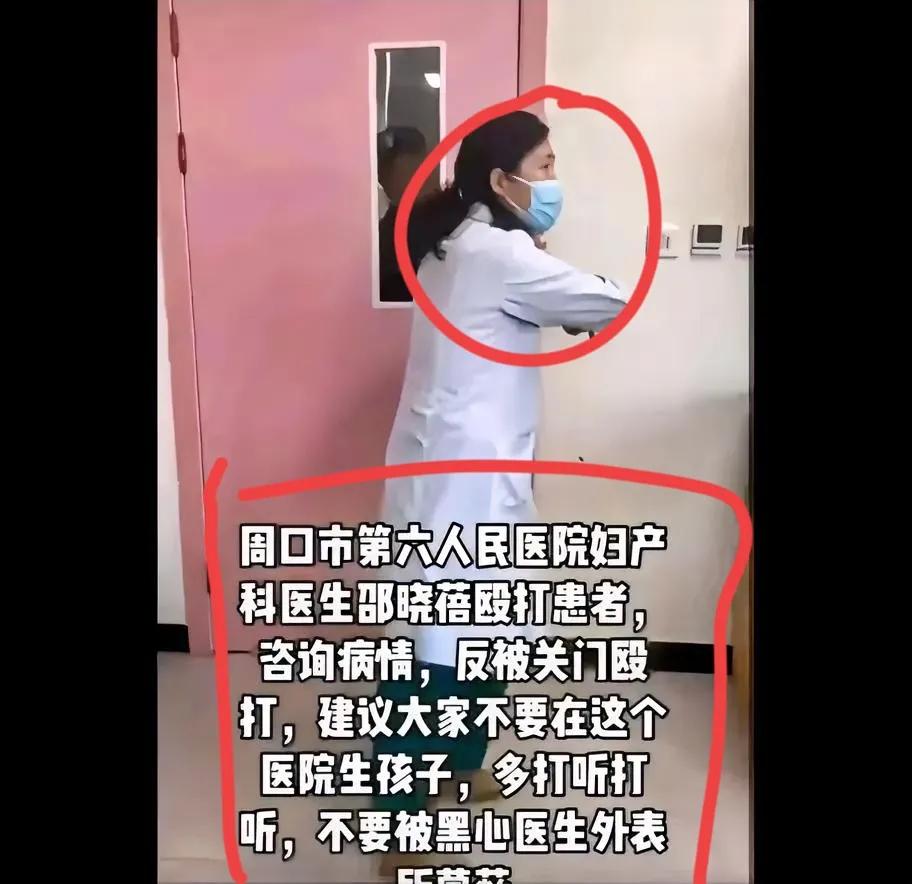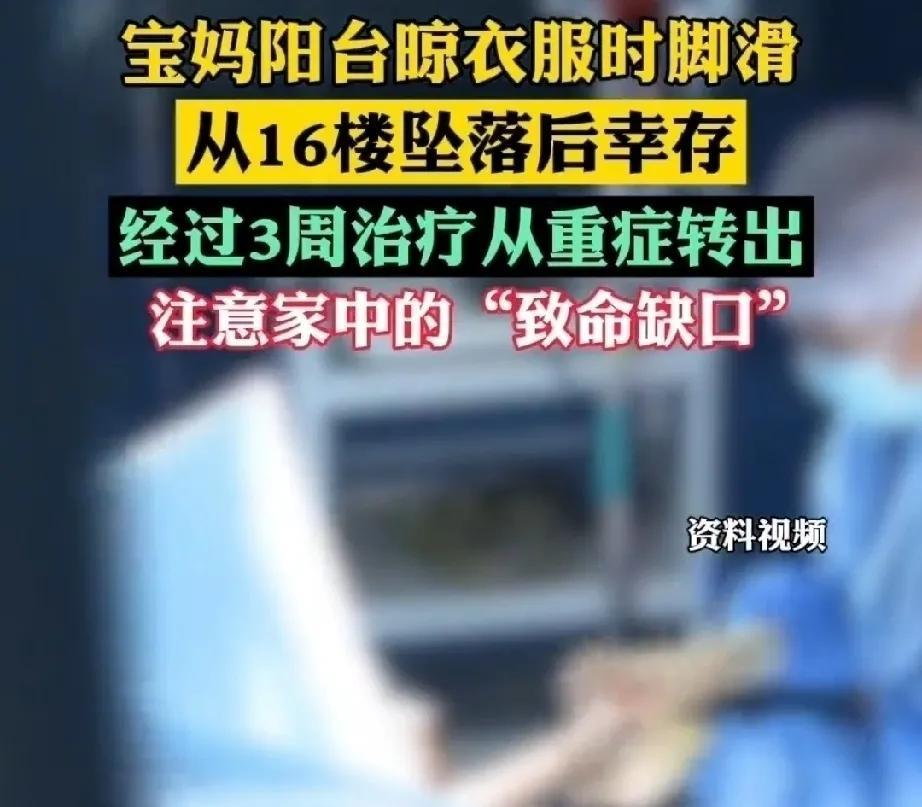1980 年,广州军区保卫部抓了总医院护士长,护士长蛮横地说:“你们怎么敢抓我?” 一个干部冷笑道:“你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军区通信站的电波监测仪上,那段异常信号已经跳动了三天。凌晨三点的值班室里,技术员反复比对频谱,指尖在坐标纸上画出的轨迹,像条毒蛇般缠绕着 “军区总医院” 的方位。 信号很弱,却带着规律的摩尔斯电码特征,每次出现都在深夜,恰好是护士交接班的空档。保卫部的干事捏着刚打印出的定位报告,窗外的木棉树影在月光下摇晃,像极了潜伏者躲在暗处的眼睛。 周晓琳的宿舍窗台上,那盆文竹修剪得格外整齐。保卫干部蹲在对面的楼顶观察了两天,发现这扇窗总在凌晨四点亮起微光,比其他宿舍早半个钟头。 更可疑的是,上周三的物资清单里,这个高干子女突然多领了两卷电池,而她的收音机明明是插电式的。 搜查令批下来那天,干事们在宿舍楼下等她夜班回来,看着她穿着白大褂走过玉兰树,口袋里露出半截金表链 —— 那款式在当时的广州,绝不是普通护士长能买得起的。 审讯室的白炽灯有点晃眼。周晓琳攥着衣角,指甲掐进的确良布料里,却仍扬着下巴:“我父亲是副军长,你们这样做是要负责任的!” 对面的干部推过来一叠照片,是她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华侨饭店门口的合影,男人手里拎着的皮箱,经鉴定装过电台零件。 照片里的周晓琳笑得灿烂,手腕上的表正是那只金表。她的瞳孔猛地收缩,像被戳破的气球,刚才的嚣张气泄得一干二净。 三个月前的深圳火车站,李俊敏就坐在周晓琳对面。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谈吐间全是 “中央部委” 的新鲜词,递过来的巧克力包装上印着英文,是她只在进口商店见过的牌子。 “我在执行保密任务,需要个可靠的落脚点。” 他说这话时,眼神诚恳得像她父亲的老部下。 周晓琳没多想,把他带回了医院闲置的值班房,对外只说是乡下投奔来的表弟 —— 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个 “表弟” 行李箱的夹层里,藏着微型电台和密写药水。 第一次收金条时,周晓琳失眠了整宿。金条被李俊敏包在丝巾里,压在她枕头下,冰凉的触感像块烙铁。 但第二天,他带她去白天鹅宾馆吃西餐,刀叉碰撞的清脆声里,她把顾虑咽了回去。 直到那个雨夜,李俊敏抱着她,突然说 “其实我是台湾来的”,她才吓得浑身发抖。 可事到如今,退无可退 —— 他手里有她的照片,知道她父亲的职务,更清楚她未婚夫是军区作战科的参谋。 护士站的值班记录本成了最好的情报来源。周晓琳值夜班时,总会趁同事打瞌睡,偷偷抄下住院军官的姓名、职务和病情,尤其是那些从广西前线转来的伤员。 有次抄到一个团长的名字,她手都在抖 —— 那是她未婚夫常提起的老领导。 但李俊敏在宿舍等着,电台的指示灯已经亮起,她咬咬牙,把纸折成小方块塞进了白大褂口袋。 那些密码电报发出时,窗外的木棉花开得正艳,像极了战场上溅落的血。 保卫部的车队在东莞的出租屋周围布控时,李俊敏正在教周晓琳发最后一份电报。 电文是广州军区近期的调防计划,周晓琳抄在药瓶标签背面,字写得歪歪扭扭。 门被撞开的瞬间,李俊敏一把将电台扔到床底,周晓琳却僵在原地,手里还攥着没发完的电稿。 后来她才知道,那间出租屋的房东早就报了警 —— 这个 “出手阔绰的北方人”,总在凌晨拉窗帘发电报,实在太反常。 法庭上,周晓琳的父亲拄着拐杖来旁听,军装的领章被泪水打湿。 她被判八年的那天,广州下起了小雨,押送车经过军区总医院门口,她看见曾经的同事正在给伤员换药,白大褂在阳光下晃得刺眼。 而李俊敏的无期徒刑判决,后来减到了二十六年,2006 年被遣返台湾时,他在罗湖桥头回头望了一眼,对岸的木棉花又开了,只是再也与他无关。 军区档案室的卷宗里,这段往事被锁在铁皮柜里。泛黄的照片上,周晓琳穿着护士服站在医院门口,笑容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 没人知道,如果那个火车上的 “表弟” 没有出现,她会不会如期嫁给参谋,在军属大院里生儿育女,看着木棉花一年年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