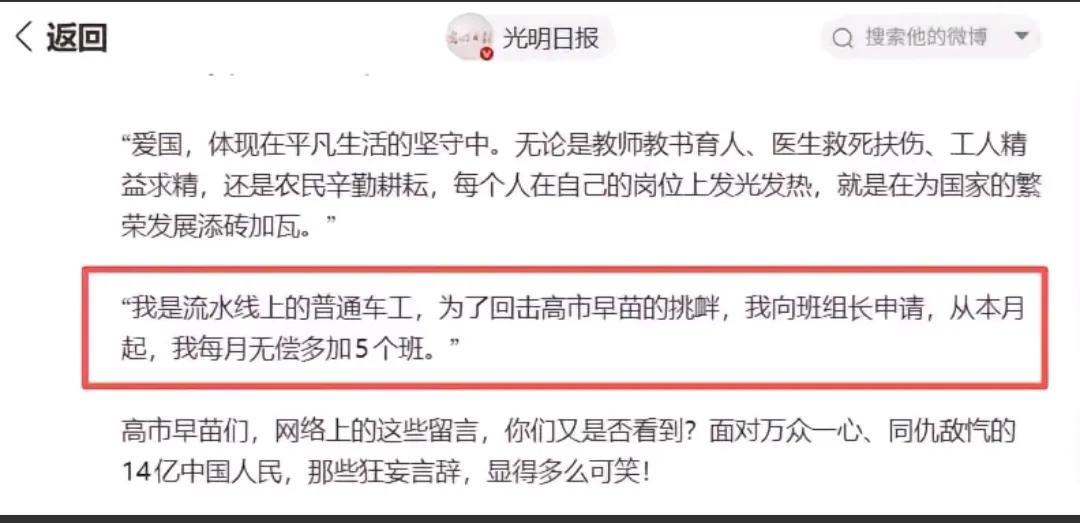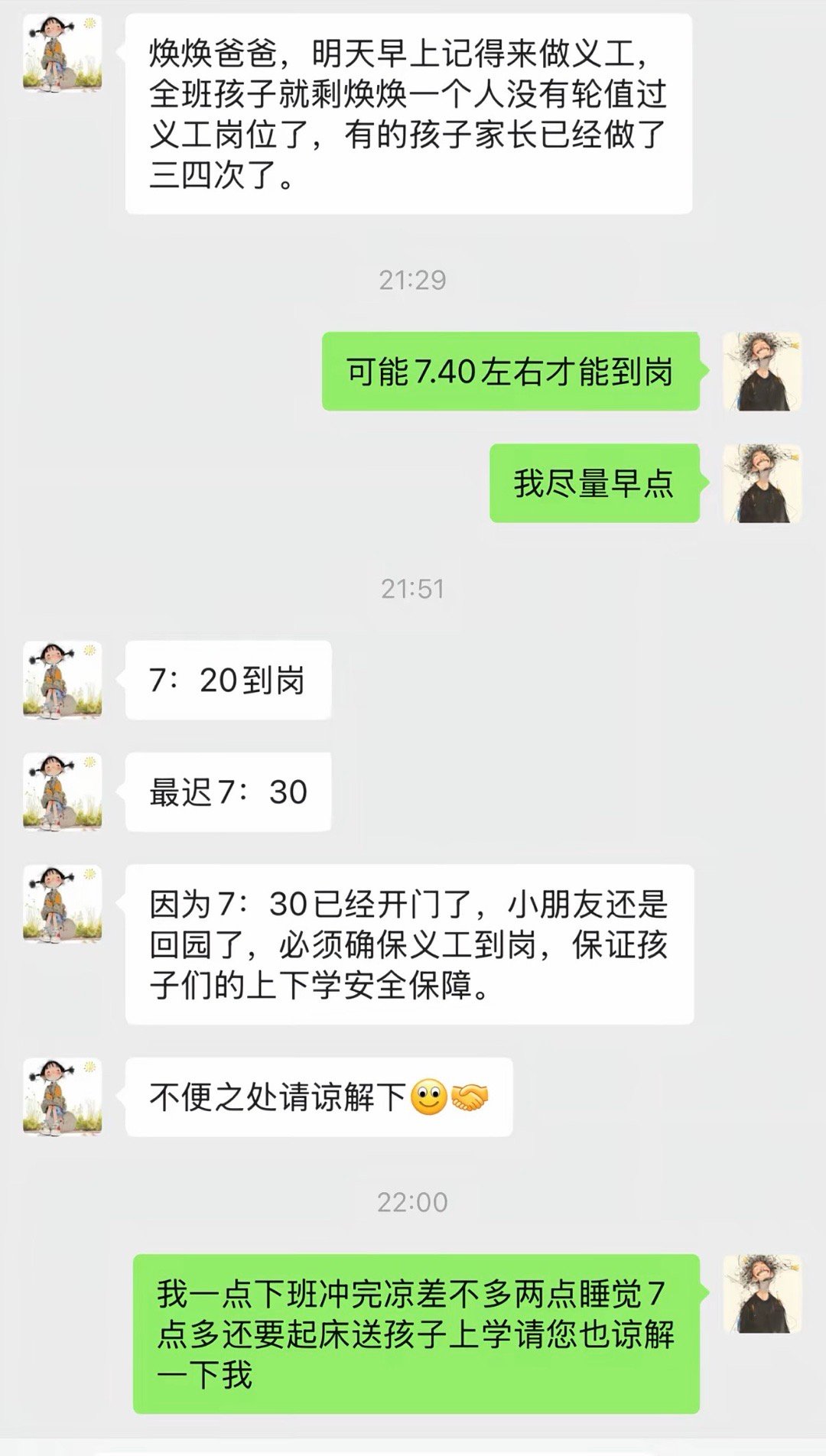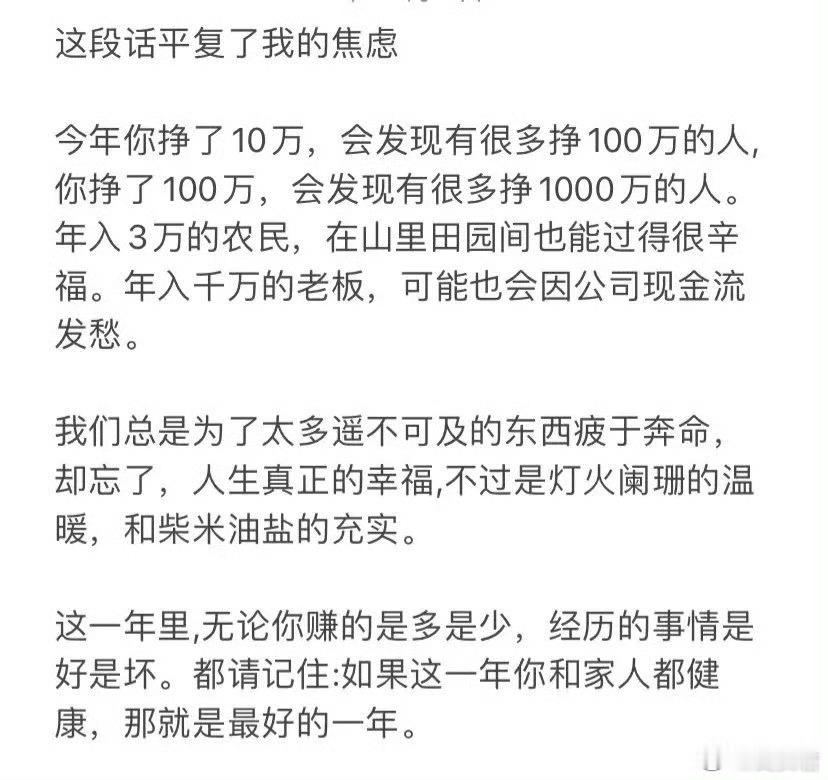“吃鱼不说话”,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也是一个人生教训。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清晰记得,如同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当时我住在广州市同福路的七楼,那天,妻子兴冲冲的在菜市场买了一条鲤鱼,说回来给全家做一顿红烧鱼晚餐;我下班回来,见厨房里有一条已㓥好待做的金黄色鲤鱼,便脱口说道:“这么漂亮的‘鲤鱼精’,吃了好可惜呀!”妻子瞟了我一眼,撅嘴说:“别瞎说!再瞎说,‘鲤鱼精’会缠住你不放的。”鲤鱼烧好后,端到桌上又鲜又香,我忍不住边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边与妻子开着玩笑,说“我与‘鲤鱼精’亲吻了;”只是没想到,妻子和我自己一语成谶,“鲤鱼精”顿时真的缠上我了。
说着与吃着间,糟糕了,我囫囵吞枣把一根鱼刺吞下去了,鱼刺并没有顺着蠕道下滑,而是卡在了喉咙哽上,不上不下,就像一根细竹签插在一根胶管中间一样,两头死死插在喉咙壁上,似有非有,似在非在,似痒又似痛,令人非常难受。我担心家人笑话我吃菜“狼狈”,不动声色地悄悄的大嚼青菜,企图用粗枝大叶的青菜把鱼刺“卷落”下去,谁知青菜吃了不少,鱼刺依然紧紧的“钳制”在喉咙里,越发痒酥酥的,大有不吐不快的迫切感;既然青菜“卷”不下去,我就起身,去大口喝水,并用力干咳,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奏效,把鱼刺顺带冲落下去;可是水喝了不少,咳嗽了若干,依然不见效。“鲤鱼精”依然把我缠绵得紧紧的,丝毫没有分开和“放手”的意思。
妻子见我满脸通红,知道是鱼刺卡住在喉咙上,便拿来手电筒,叫我张开嘴巴,希望手电筒能够像“照妖镜”那样,照得见“鲤鱼精”“兴风作浪”的样子和“狞笑”的神情,可是照了半天,依然毫无所获,不见踪迹,也没有吓跑“鲤鱼精”。
接下来我按父母亲提供的老办法喝醋、用手倒勾、弯腰低头猛摇头……诸多办法尝试了一遍,但是“鲤鱼精”依然没有放弃与我“亲热”的打算,反而似乎贴的更紧了、绷得更直了,弄得我满头大汗,浑身难受,瘫坐在沙发上,无计可施,愁眉紧锁。
还是父母亲见多识广,提醒我马上去医院“虎口拔刺”,我一时昏聩迷惘,失了分寸,听父母亲这样一说,马上醒悟过来,红会医院就在家的旁边,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去医院灭掉这个兴风作浪的、害人的“鲤鱼精”呢?我喜出望外,精神一振,迅速地步行下楼了。

楼房是老式居民楼,没有电梯,楼梯宽敞,阶梯较多,我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说:你这个“鲤鱼精”妖孽,害我不浅,看我到了医院,定叫你现出“原形”,不灭了你不解气……说着说着,下到了一楼平地,突然感觉喉咙哽的异样没有了。起初,我还不敢相信,便反复咽了几口口水,发现并无“梗塞”的感觉,口水顺畅下咽,绊不到鱼刺,这才彻底确认“鲤鱼精”的确是害怕见到医生、自己先逃之夭夭了。
复转身,又上楼,我又自言自语道:你这个“鲤鱼精”啊,再捣蛋再邪门,还是怕医生的手术刀呀!早知道这样,我就直奔医院,不用受这么多的折腾了。
家人们见我这么快回来,以为是我忘了带钱,是回来取钱的;我爽快的告诉他们:“鲤鱼精”吓跑啦!
鱼刺去哪儿了?事后我一想,应该是下楼梯的大踏步和大口喘气所带来的振动,绺顺了鱼刺的方位,让它顺利地滑落到肠胃里了;当然,前期所做的一切努力也有可能起了一定的助力作用。
中国有个成语叫“如鲠在喉”,说的是鱼刺卡在了喉咙里难受的感觉;有时候也形容人们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非常难受的感觉;不过我通过自己的这次“如鲠在喉”的亲身经历,我还觉得在生活中如果碰到类似如鲠在喉的困境、窘境、棘手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让时间去过滤、淘漉、冲刷、检验、溶解、回答、解决;尤其是碰到问题或一些矛盾、事故时,千万不能手忙脚乱,失了分寸,失了理智,更不能利令智昏,做出饮鸠止渴的判断和错上加错、以错对错的举动,如果是那样,可真会“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如鲠在喉”尴尬体验便有些警示和昭示的意味和作用了:一是事急则缓,事缓则圆;打败自己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势力和某些不利因素,而是自己的心智与性格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二是吃鱼不说话,说话不吃鱼;延伸到工作和生活中,就是做事心无旁鹜,聚精会神,就不会出丑、出错。


☆ 本文作者简介:杨德振,男,65年出生,祖籍湖北麻城,客居广州。工商硕士,中共党员,复转军人,企业高管(刚退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者》《意林》《思维与智慧》《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出版文艺著作八部、企业管理论著二部;大部分著作被国家图书馆、各省图书馆、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和高等学府收藏。。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