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的浓雾
1791年3月2日上午,克劳德·夏普(Claude Chappe)站在巴黎的一处屋顶上,手里拿着一只高倍望远镜。他的视线穿过烟囱和煤烟,聚焦在15公里外的另一座塔楼上。
那里竖立着一根木杆,顶端横架着一根可以旋转的横梁,横梁两端各有一根更短的活动臂。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十字架,涂成了黑色。夏普低头看了看怀表,秒针归零。远处的机械臂动了。横梁旋转了45度,右侧短臂垂直向下,左侧短臂水平向左。

夏普查阅手中的密码本。
这个动作代表“Si”(如果)。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以光速传输信息——虽然它的载体是木头。法国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巴黎需要知道前线的消息。夏普设计的这套“光学电报”系统(Semaphore),由一系列建在山顶和塔楼上的信号站组成,每隔10到15公里一座。操作员不需要理解信息的含义,他们只需要盯着上一站的机械臂,模仿它的动作,然后通过望远镜确认下一站的操作员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1794年8月,这一系统迎来了高光时刻。北方战线的孔代城被法军收复。消息从里尔出发,经过15个中继站的机械臂挥舞,仅用了20分钟就抵达了巴黎。而在过去,骑马的信使跑死两匹马也需要整整一天。
但物理学很快给夏普上了一课。
1799年11月,雾月政变前夕,拿破仑急需南部的军情。信号从土伦发出,一路顺畅地跳过了普罗旺斯的山丘。然而,当信号传递到里昂以北时,一阵冷空气遭遇了暖湿气流。
浓雾遮住了第42号信号塔。
第41号塔的操作员疯狂地挥舞着巨大的木制手臂,试图引起注意。第43号塔的操作员把眼睛贴在望远镜上,但他看到的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信息中断了。在那个没有风的下午,整个法国的情报网络瘫痪了。拿破仑在巴黎焦躁地踱步,而那条关于军队调动的关键指令,就这样悬停在里昂北部的半空中,消失在水蒸气里。
夏普的系统有一个致命缺陷:它依赖视线。它怕雾,怕雨,怕黑夜。为了让它在夜间工作,夏普尝试过在木臂上挂灯笼,但微弱的烛光在几公里外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光斑,根本无法分辨角度。
就在夏普为了如何穿透迷雾而焦虑致死(他在1805年跳井自杀)的几十年后,在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间地下室里,查尔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e)正盯着一根铜线发呆。他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威廉·库克(William Cooke)带来的奇怪装置。

只要接通电流,远处的磁针就会偏转。不需要望远镜,也不受黑夜限制。
唯一的问题是,没人相信这东西有用。直到那个穿贵格会大衣的男人买了那瓶毒药。
穿着贵格会大衣的杀人犯
1845年1月1日,星期三。约翰·塔威尔(John Tawell)走进斯劳的一家药店,买了一瓶氢氰酸。他对药剂师说这是为了治疗静脉曲张。
下午,他前往萨拉·哈特(Sarah Hart)的小屋。哈特是他的情妇,还要养育他和她的两个孩子。塔威尔给她倒了一杯啤酒,把氢氰酸倒了进去。邻居透过栅栏,听到了一声短促的尖叫,接着是一阵呻吟。
几分钟后,塔威尔推开门走了出来。他穿着标志性的贵格会教徒长款大衣,神色慌张。他快步走向斯劳火车站,跳上了一辆开往伦敦帕丁顿的火车。那是晚上7点左右。
塔威尔坐在头等车厢里。火车时速40英里。在这个速度下,没有人能追上他。在这个时代,只要你离开了犯罪现场,你就暂时安全了。警察不可能比火车跑得更快。当尸体被发现并确认死因时,他早就融入了伦敦拥挤的人潮中。
但他错了。因为在斯劳火车站的站台上,除了铁轨,还有几根沿着路基延伸的电线。
一位名叫威廉姆斯的神职人员目击了塔威尔离开受害者家的全过程,并跟踪他到了车站。威廉姆斯找不到警察,但他看到了电报室。他冲进去,对着操作员大喊:“哪怕花这辈子所有的钱,我也要发电报到伦敦。”
操作员启动了五针电报机。这台机器通过五根磁针的偏转指向不同的字母。它并不完美——为了简化电路,表盘上没有字母C、J、Q、U、X和Z。
信号开始传输:
M-U-R-D-E-R (谋杀)
C-O-M-M-I-T-T-E-D (发生)
A-T (在)
S-A-L-T-H-I-L-L (索尔特希尔)
接下来的描述成了问题。塔威尔穿着贵格会(Quaker)的大衣。操作员无法拼出“Q”。
帕丁顿端的接收员看着针头乱跳,无法理解。斯劳端的操作员不得不重新拼写:
K-W-A-K-E-R
帕丁顿端回传:“明白。”
此时,塔威尔的火车还在半路上。电子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铜线中飞驰,越过正在喷吐黑烟的蒸汽机车。
当火车缓缓驶入帕丁顿车站时,塔威尔提着包,混杂在下车的乘客中。他回头看了一眼,确认没有警察追上来。他轻松地走出站台,叫了一辆公共马车。

他没注意到,一个穿着便衣的警长正站在阴影里,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抄写下来的纸条。
警长没有立刻动手。他像个幽灵一样跟着塔威尔穿过伦敦的街道,直到第二天早上,在一家咖啡馆里,警长走到塔威尔面前。
“我想你刚才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吧?”警长问。
塔威尔愣住了:“你怎么可能这么快?”
第二天,《泰晤士报》刊登了这条新闻。人们不再谈论谋杀案本身的血腥细节,所有人都在谈论那几根铜线。这不仅仅是一次逮捕,这是物理学对地理学的第一次公开羞辱。罪犯的逃逸速度在电流面前变得毫无意义。
电报局的生意一夜之间暴涨。但英国只是一个岛。当电报线延伸到多佛尔的悬崖边时,它停下了。
前面是30公里的海水。
连接英国和法国的铜线
如果要把电线扔进海里,空气绝缘就不管用了。海水是良导体。如果你把裸露的铜线丢进大西洋,电流会瞬间散逸到浩瀚的盐水里,接收端什么也收不到。
你需要一种东西,能包裹铜线,既不导电,又能经受住深海的压力、寒冷和腐蚀。橡胶在冷水中会变脆开裂。沥青会碎。
答案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医生,威廉·蒙哥马利。1843年,他给皇家艺术学会寄来了一种他在马来西亚发现的树胶样本:古塔波胶(Gutta-percha)。这是一种热塑性材料,加热时变软,冷却后变硬,最重要的是,它绝缘且防水。
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把玩了这种材料,点了点头。

1850年,约翰·布雷特(John Brett)和雅各布·布雷特(Jacob Brett)兄弟决定干一票大的。他们要连接英国和法国。
这对兄弟没有工程背景,全是商业赌徒的狂热。他们筹集资金,制造了一条25海里长的电缆。这条电缆极其简陋:一根1/16英寸粗的铜线,裹上一层古塔波胶。没有外层铠装,没有钢丝保护。它细得像根跳绳。
1850年8月28日,一艘名叫“歌利亚号”(Goliath)的小拖船载着这卷电缆离开了多佛尔。为了让这根会漂浮的细线沉下去,工人们每隔100码就在上面绑一块铅块。
船缓慢地向加来驶去。电缆像一根脆弱的面条被放入英吉利海峡。

晚上,电缆铺设完毕。多佛尔的操作员按下了电键。
在法国格里内角,检流计的指针动了。
“Hurrah”(万岁)。
第一条跨海信息发送成功。布雷特兄弟开了香槟。拿破仑三世发来了贺电。这一刻,英吉利海峡似乎消失了。
但庆祝活动只持续了不到24小时。
第二天早上,信号突然中断。无论多佛尔端如何调试电压,检流计都死气沉沉。
原因在几小时后被查明,但这极其荒谬。
一名法国布洛涅的渔民那天运气不好,网住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他用力拉拽,发现是一根长长的、黑色的、像海藻一样的绳子,但中心闪着金红色的光泽(铜)。
渔民认定这是某种未知的新型海怪,或者是含金的海草。他掏出刀,截断了那段“含金”的部分,高兴地把剩下的扔回海里,准备带去布洛涅的市场展示他的战利品。
人类第一条跨海电缆,就这样被一把杀鱼刀终结了。
布雷特兄弟看着那截断裂的线头,意识到了一件事:海洋不是平静的实验室。它是充满锚链、岩石和愚蠢渔民的敌对环境。
1851年,他们卷土重来。这次,电缆重达200吨。古塔波胶外面包裹了麻绳,最外层缠绕了十根镀锌铁丝。这是一条真正的铠装电缆,任何渔民的刀都切不动它。
这一年11月13日,电缆再次接通。这次,它没有断。伦敦和巴黎的股市行情开始实时同步。仅仅在第一天,这条线路就传送了开盘价和收盘价。
既然跨过了30公里的海峡,那个叫做赛勒斯·菲尔德(Cyrus Field)的美国造纸商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为什么不试试3000公里外的大西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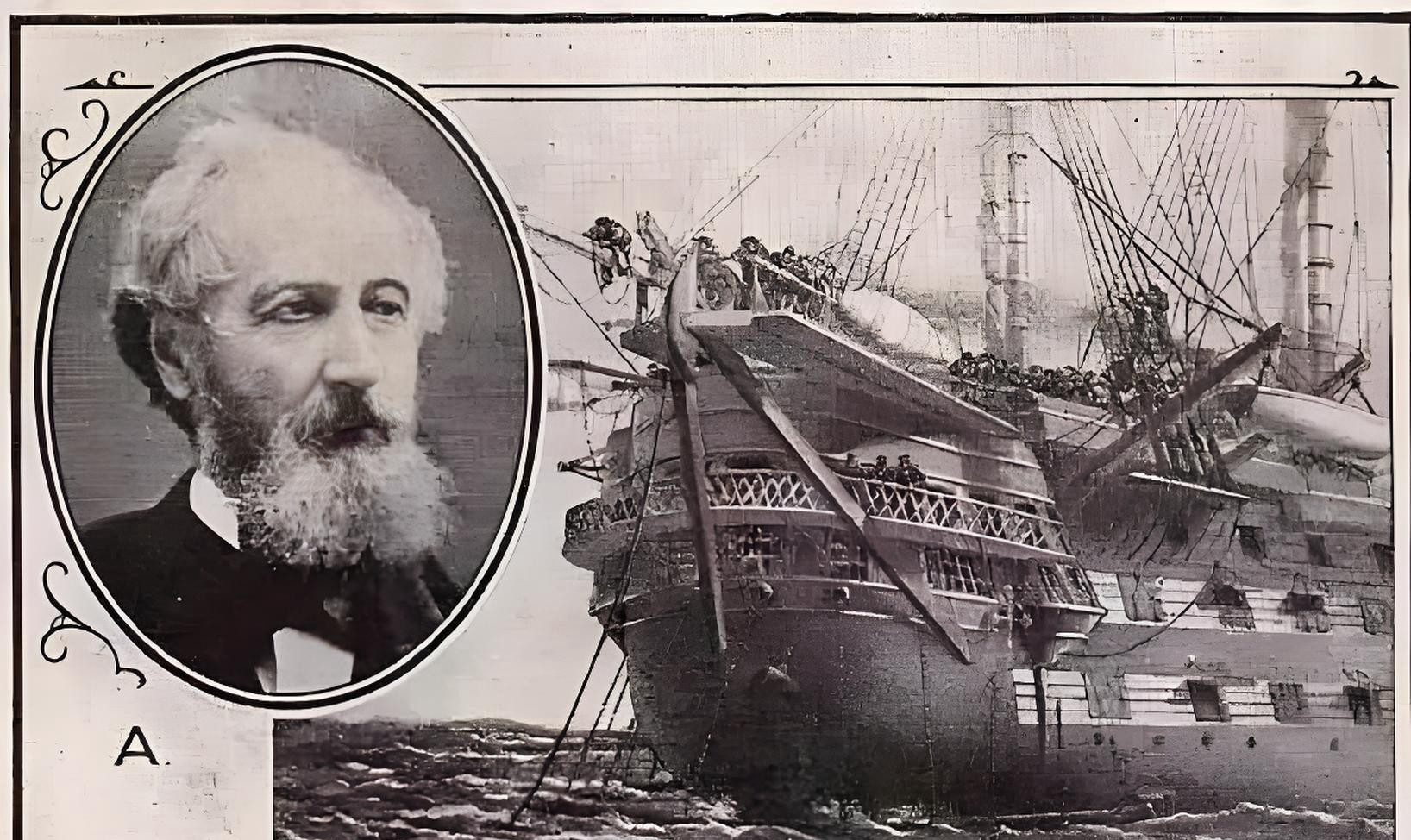
他在地球仪上画了一条线,连接爱尔兰的瓦伦西亚和纽芬兰的三一湾。他不知道那是两英里深的深渊,也不知道那是足以让所有投资者破产的黑洞。
百万富翁的赌局
1854年的一天晚上,赛勒斯·菲尔德在他的纽约豪宅里接待了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吉斯伯恩(Frederick Gisborne)的客人。
菲尔德34岁,刚从造纸业退休,身价几十万美元,正处于一种富有的无聊状态中。吉斯伯恩则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投机客——破产,负债,手里攥着一个烂尾工程。吉斯伯恩的想法是在纽芬兰岛铺设电报线,这样当欧洲的邮轮经过纽芬兰时,可以把消息传回纽约,比船只本身早到一天。
菲尔德听完,盯着地图上北大西洋的那片蓝色区域问:“既然能连到纽芬兰,为什么不直接连到爱尔兰?”
这就是那个价值百万美元、同时也可能让他身败名裂的问题。
菲尔德对电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欧姆定律,分不清伏特和安培。但他有两个关键优势:钱,以及一种对困难缺乏想象力的盲目乐观。
他给莫尔斯(Samuel Morse)写信,询问电信号是否能传输这么远;他给海洋学家马修·莫里(Matthew Maury)写信,询问海底地形。莫里的回复出人意料地令人振奋:大西洋底部并不是崎岖的山脉,在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有一片平坦的高原,莫里称之为“电报高原”(Telegraph Plateau)。海底铺满了柔软的贝壳尸体,就像羽绒被一样等待着电缆落下。
菲尔德在第二天早上5点起床,决定把余生和全部财产都扔进这片水域。
他成立了纽约、纽芬兰和伦敦电报公司。这不是一家科技公司,而是一台融资机器。菲尔德穿梭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之间,向那些甚至还没见过电报机的银行家兜售未来。他说服了英国政府提供船只,说服了美国国会提供资金——尽管仅以一票优势通过。
1857年,电缆制造完成。2500海里。这根线需要两家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了6个月。因为没有一艘船能装下这么重的东西(2500吨),任务被分派给了两艘战舰:英国的“阿伽门农号”和美国的“尼亚加拉号”。
菲尔德站在码头上看着这两艘巨舰。他以为他战胜了自然,但他甚至还没搞定他的总工程师。
50万美元的电缆断裂
在大西洋电报公司的董事会里,坐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一个是怀尔德曼·怀特豪斯(Wildman Whitehouse)。他原本是个外科医生,半路出家玩起了电学。他不懂微积分,蔑视理论,信奉“大力出奇迹”。他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信号传不过去,那就加大电压。他是公司的首席电工,因为他擅长用华丽的演示忽悠外行董事。
另一个是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后来的开尔文勋爵)。格拉斯哥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22岁就发表了关于热力学的论文。他走路有些跛,手里总是拿着笔记本计算。

汤姆森提出了一个让他不受欢迎的理论:“平方定律”(Law of Squares)。他计算出,电流在长距离海底电缆中的传输速度会急剧下降。电缆不仅仅是导线,它还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古塔波胶把铜线和海水隔开,形成了一个电容,会吞噬电流,导致信号在另一端变得模糊不清,就像在隧道里喊话产生的回声。
汤姆森的结论是:不能用高压暴力传输,必须用极低电压和极高灵敏度的接收仪器。
怀特豪斯对此嗤之以鼻。他在董事会上嘲笑汤姆森是“象牙塔里的理论家”,并向董事们保证,只要电压足够高,电子就会像子弹一样穿过去。
董事会选择了听起来更像商人的怀特豪斯。汤姆森被边缘化,仅仅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顾问随船出征。
1857年8月5日,船队从爱尔兰出发。
前三天一切顺利。电缆缓缓滑入海底。但在8月11日,海水深度达到2000英寻(约3600米)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船尾随浪颠簸,负责控制电缆释放速度的制动员操作失误,刹车闸卡死。巨大的拉力瞬间作用在电缆上。
“啪”的一声。
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是一声清脆的断裂声。船尾的张力计归零。价值50万美元的电缆像一条死蛇一样滑入深渊,永远消失了。
菲尔德站在甲板上,脸色苍白。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怀特豪斯立即宣称这是机械故障,与他的电气理论无关。汤姆森一言不发,只是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断裂点的坐标。
两千伏特的结局
1858年夏天,他们又试了一次。
这次策略变了。两艘船开到大西洋正中间,先把电缆头接好,然后背向航行,一艘往英国开,一艘往美国开。
6月,遭遇风暴,“阿伽门农号”差点翻船,电缆断裂。
7月,再次尝试,两船驶出不到200英里,信号中断。
菲尔德回到伦敦时,董事会主席建议卖掉剩下的电缆止损。菲尔德拒绝了。他说服董事会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
1858年7月29日,两艘船在洋中汇合。接头完成。8月5日,两艘船分别抵达爱尔兰和纽芬兰。电缆没有断。
大西洋两岸接通了。
消息传出,举世狂欢。纽约街头鸣放了100响礼炮,市政厅被烟火点燃(字面意义上的点燃,圆顶被烧坏了)。蒂芙尼公司买下了没用完的电缆,截成4英寸长的小段作为纪念品出售,大赚一笔。
8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向美国总统布坎南发送贺电。
这段只有98个单词的信息,传输了整整16个半小时。
这验证了汤姆森的预言:信号严重延迟。在爱尔兰端的接收室里,汤姆森架设了他发明的“镜面检流计”。这是一种精妙的仪器——将一面只有硬币大小的镜子粘在磁针上,反射一束光到墙上。哪怕电流微弱到只能让磁针偏转极小的角度,墙上的光斑也会移动很大的距离。
靠着汤姆森的仪器,操作员勉强能读出模糊的信号。
但在另一端,怀特豪斯愤怒了。他此时因为身体原因没能上船,但他仍然控制着爱尔兰的基站。他觉得汤姆森的镜面检流计是“玩具”,认为传输慢是因为电压不够。
就在公众还在庆祝“人类团结”的时候,怀特豪斯在瓦伦西亚岛的机房里实施了一场谋杀。
他拆掉了汤姆森的仪器,搬出了他引以为傲的巨型感应线圈。这是一个长达5英尺的怪物。怀特豪斯下令将这个装置接上刚刚铺好的大西洋电缆。
他向那根脆弱的铜线注入了2000伏特的高压电。
如果是陆地上的架空线,这或许没问题。但在深海,高压意味着巨大的电应力。古塔波胶绝缘层并不是完美的,它上面有微小的气泡和裂纹。
2000伏特的电流像高压水枪一样冲击着薄弱的绝缘层。绝缘层被击穿了。
信号强度瞬间跳水。起初还能勉强辨认单词,随后变成无意义的乱码。到了9月,信号彻底消失。
这条耗资250万英镑、动用两国海军、牺牲了无数水手的电缆,仅仅工作了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一根横跨大西洋的废铜烂铁。
公众的反应从狂热瞬间转向暴怒。报纸指控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股市骗局,甚至有人声称电缆根本没通过电,女王的贺电是伪造的。赛勒斯·菲尔德成了过街老鼠,他在纽约不得不避开人群。
大西洋电报公司实际上破产了。怀特豪斯被调查委员会传唤,最终被解雇并钉在科学史的耻辱柱上。
这似乎就是结局:海洋赢了,物理学赢了,人类输了。
但在伦敦的一间仓库里,有一个巨大的生锈怪物正在沉睡。而在格拉斯哥,汤姆森正在擦拭他的镜面检流计。他们只需要一个机会。
大东方号启航
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1859年去世时,带着一个巨大的耻辱:大东方号。

这艘船是个怪物。它长211米,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船只的五倍大。它有两个明轮、一个螺旋桨、六根桅杆和五个烟囱。布鲁内尔设计它的初衷是直航澳大利亚而无需加煤,但它太大,下水时就把绞盘崩飞了,还没出港就让运营公司破产。它就像一条搁浅的鲸鱼,在港口生锈,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过度膨胀的工业野心的墓碑。
但这头白象是能装下整条大西洋电缆的容器。
1865年,赛勒斯·菲尔德收购了大东方号。工人们拆除了船上华丽的头等舱沙龙,挖空了船腹,建造了三个巨大的圆形水箱来存放2300海里的新电缆。
这一次,威廉·汤姆森亲自跟船。电缆也进行了升级:核心铜线加粗,绝缘层加厚,外层包裹了更强韧的钢丝。
7月23日,大东方号起航。这艘曾经被视为诅咒的巨舰在海浪中出奇地平稳。铺设过程枯燥而顺利。电报室里,汤姆森盯着光点,每一秒都有信号传回爱尔兰。
但大西洋不打算这么轻易认输。
8月2日,行程过半。船员发现电缆绝缘层出现了一个微小的针孔,导致漏电。这看起来像是人为蓄意破坏(有人怀疑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工贼刺穿了电缆),船长下令把电缆拉回来切除坏点。
这是个危险的动作。大东方号虽然大,但在大西洋中心调头并回收电缆依然极其困难。就在电缆被拉出水面时,船身颠簸了一下。
电缆在距离船头几米的地方崩断了。
没人说话。所有人眼睁睁看着那条黑色的线头滑入水中,像一条逃跑的鳗鱼,消失在波涛里。这里的水深是2.5英里(约4000米)。
菲尔德没有哭,也没有发疯。他下令:“拿抓钩来。”
接下来的9天,船员们在大西洋中心盲目地抛下巨大的铁钩,试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底钩住一根直径只有2.5厘米的绳子。
甚至比这更荒谬的是:他们钩住了。
8月10日,绞盘的张力剧增。他们钩住了一条线。绞盘呻吟着把电缆往上拉了1200米,然后绳索断了。
8月15日,又钩住一次,拉上来一半,绳索又断了。
8月17日,第三次钩住,再次断裂。
他们用光了所有的绳索。大东方号不得不返航。但这次失败不同于以往。他们知道电缆就在那里。汤姆森记下了精准的坐标,并在海面上抛下了一个浮标。
菲尔德回到伦敦,成立了新的公司。这次没有人嘲笑他。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电缆不是不能铺,只是绳子不够结实。
海底的复活
1866年7月13日,一个星期五。大东方号再次出征。
这次没有任何戏剧性。机器运转完美,天气晴朗。14天后,7月27日,大东方号驶入纽芬兰的三一湾。船员把电缆拖上岸。
电报员接通了仪器。几秒钟后,来自爱尔兰的信号清晰地出现在检流计上。
欧洲和美洲连接了。这一次,是永久的。
但菲尔德和汤姆森没有开香槟庆祝。大东方号加满煤,掉头驶回大西洋中心。他们要去干一件物理学上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打捞一年前丢失的那根电缆。
他们在海上搜索了三个星期。这是一场巨大的盲人摸象。船长必须修正风向、洋流和经纬度的误差,把抓钩准确地拖过海底的某一条线。
9月2日,抓钩钩住了一个沉重的东西。
绞盘极其缓慢地转动。经过30个小时的提拉,一根覆盖着灰色淤泥和海洋生物的电缆破水而出。它已经在冰冷的高压海底躺了整整一年。
船上的电报室里,所有人屏住呼吸。技术员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刚出水的烂线剥开,接上检流计,然后按下了电键,试图呼叫爱尔兰的瓦伦西亚站。
在那边,一位孤独的值班员正百无聊赖地守着一台死了一年的仪器。突然,光点动了。
值班员以为自己眼花了。看着光点跳出了清晰的莫尔斯码:“Ship to Shore”(船呼叫岸站)。
他在记录本上写下了回复。
大东方号的电报室里爆发出了欢呼声。
这一刻比铺设新电缆更具震撼力。它证明了海底电缆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赌博,而是一种可维护、可修复的工业资产。现在,大西洋底有两条工作的电缆。
菲尔德发给伦敦的第一条消息不是贺电,而是商业报价。他列出了新的收费标准:每20个单词,1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0000美元)。
红海的泥浆
大西洋被征服后,世界的其余部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英国不能只靠轮船来统治印度。1857年的印度兵变消息花了40天才传到伦敦,等援军赶到时,局势已经失控。伦敦需要一条直通孟买的神经。
但向东方铺设电缆比横跨大西洋更麻烦。大西洋虽然深,但底质是柔软的泥沙。红海和印度洋底层则是珊瑚礁、岩石和生物。
早期的红海电缆是一场灾难。并没有人告诉工程师,热带海域里有一种叫做船蛆的软体动物。这种东西虽然微小,但也是一种不知疲倦的钻孔机。它们嗜好古塔波胶的味道。
第一条红海电缆铺设后几个月,信号就变得断断续续。拉上来一看,绝缘层被啃得像蜂窝煤一样。
工程师们学会了在古塔波胶外面包裹黄铜带。这被称为“防蛀层”。
1870年,连接伦敦和孟买的电缆终于全线贯通。以前需要6周的消息,现在只需要4分钟。
在此之前,伦敦和孟买的棉花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暴利。如果你知道欧洲棉花收成不好的消息比你的竞争对手早一周,你就能买空市场。现在,这根细线抹平了时间差。
一位老派的棉花商人在回忆录中抱怨:“电报毁了生意。现在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知道价格。那种凭直觉和速度赚钱的日子结束了。”
世界变小了,也变快了。1883年,印尼的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爆炸声还没传到几百公里外,关于海啸的电报已经传到了伦敦。波士顿的报纸在火山灰还没落下时就刊登了头条。

到19世纪末,地球被十几万海里的铜线缠绕着。这些线路大部分汇集到伦敦。英国通过这些铜线监听世界,调度舰队,控制价格。
康沃尔的幽灵信号
1901年,有线电报公司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科技巨头。它们拥有海底的铜线,拥有沿岸的登陆权,拥有政府的特许经营。
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只有27岁,没上过大学,是个半吊子物理学家。他有一个荒谬的想法:不需要电线,电磁波可以跨越海洋。

所有的正统物理学家,包括爱迪生和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都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电磁波像光一样沿直线传播。地球是圆的。如果你从英国发射电波,它会直射向太空,根本不可能绕过地球的曲率到达美国。
马可尼不听。他只懂实验,不懂数学。
1901年12月,他带着两个助手来到纽芬兰的信号山。他在一座废弃的传染病医院里安顿下来,试图用风筝把一根天线拉到400英尺的高空。
在3500公里外的英国康沃尔郡波尔杜,他的团队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发射台。那是一个狂暴的机器,利用高压电容器产生巨大的火花,释放出大约25千瓦的能量。
12月12日中午12点30分,马可尼坐在冰冷的房间里,把听筒压在耳朵上。风很大,风筝在天上剧烈晃动,导致天线长度不断变化。
按照约定,波尔杜电台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连续发射摩尔斯电码“S”(三短点:· · ·)。
除了风声和静电噪音,什么都没有。
物理学家们是对的。地球的曲率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墙。
突然,在噪音的间隙中,出现了三个清晰的、有节奏的点击声。
滴,滴,滴。
滴,滴,滴。
马可尼把听筒递给助手坎普:“你听到了吗?”
坎普点了点头。
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科学家才发现地球大气层外有一层电离层,它可以像镜子一样反射无线电波。马可尼实际上是把信号射向了天空,天空把它弹回了地面。他运气好,选对了频率。
那天晚上,电缆公司的董事们还在享用晚餐。他们的股票依然坚挺,垄断依然看似牢不可破。但实际上,他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在那间漏风的木屋里,那个只有27岁的年轻人刚刚证明了,连接这个世界不需要昂贵的铜线,不需要古塔波胶,也不需要跟大西洋的鲨鱼搏斗。
信息是可以自由飞翔的。
铜线落潮,电波升空
从里尔屋顶的浓雾到康沃尔的幽灵信号,人类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对抗物理枷锁的远征。克劳德·夏普的木制臂膀在迷雾中失效,布雷特兄弟的跨海电缆被渔刀斩断,怀特豪斯的高压电流击穿了深海的绝缘层——每一次失败,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信息能否挣脱空间、天气与地形的束缚?
汤姆森的镜面检流计捕捉到了微弱的电流信号,马可尼的风筝天线接住了来自电离层的反射电波,答案逐渐清晰:信息的本质从不依赖载体的厚重。当铜线在海底铺成牢笼,电磁波便化作飞鸟;当视觉信号被迷雾阻隔,电流便沿着铜线潜行。人类对“连接”的认知突破——从依赖视线到驾驭电流,从缠绕地球的铜线到跨越天际的电波,始终在打破“不可能”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