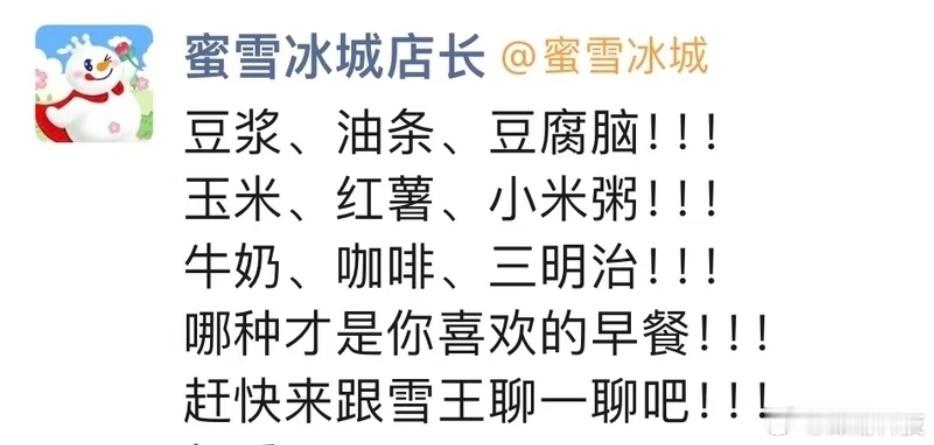全球十大面条,就算有钱也未必全吃过

四千年前的喇家遗址,一碗被地震封存在陶碗里的粟米面条,
干硬得像块土疙瘩,却藏着最早的烟火气。
那时的人还没有精细的磨盘,把粟米捣成碎粒,掺水揉成筋道的团,
再用手扯成条下锅,粗粝的口感里全是活下去的实诚。
后来有了石磨,麦粉替代了粟米,面条也从“煮饼”变成了真正的模样。

汉代人吃汤饼,得用筷子挑着热乎的往嘴里送,溅得衣襟上全是油星;
唐代长安的夏天,街头卖的冷淘过了冰,咬起来凉丝丝的,是穷人和富人都爱的滋味。
灾年里,一碗杂面能救一条命;
丰年时,它又成了待客的礼数。
北方人过年要吃压面,说是“压走晦气”;南方人做寿得下挂面,盼着“福寿绵长”。

我爷爷说,民国时逃荒,他揣着半块干面走了三天,饿极了就掰一点嚼,渣子都舍不得吐。
如今锅里的面条煮得软烂,浇上番茄鸡蛋卤,小孩捧着碗呼噜呼噜吃。
这根从远古拉到现在的面,裹着汗珠子和眼泪,也藏着最实在的日子,从来没变过。
今天,跟您聊聊全球最好吃的十碗面!

诞生于19世纪,中国、日本、菲律宾、葡萄牙移民涌入夏威夷种植园时。
劳工们拮据,凑锅煮面,
中国汤面打底,日式鲣鱼汤提鲜,菲律宾炒粉条增韧,葡式香肠切片,再撒夏威夷土鸡蛋和朝鲜辣白菜。
这锅“大杂烩”成了多元文化的活化石,被州政府列为历史景点,
像欧胡岛Like Like Drive Inn的墙面还留着百年前的煤烟痕迹,透着沧桑味儿。
细面软滑似云,吸饱汤头后卷成小弯,咬下是柔中带弹的口感。
汤底清冽如海风,掺着虾汤的鲜、酱油的咸,配菜堆成小山:
叉烧薄如蝉翼,午餐肉煎得微焦,海苔片脆生生,再来点日式蒸鱼饼和青葱,
嗦一口直喊“Aloha”!
夏威夷人管这叫“海岛版的拉面”,连麦当劳都卖它,是真正的“平民美味”。

这口面,得从元朝“禁刀令”说开。
那时蒙古人怕汉人造反,十户才配一把菜刀。
有回平遥老汉取刀扑空,回家路上捡块薄铁皮,老婆子急得直咂嘴:“这软塌塌的能切面?”
老汉一拍腿:“切不动就‘砍’!”说着便抄起铁皮,站在滚水锅边“咔咔”削面,面叶如柳叶翻飞,老汉边吃边喊:“美咧,美咧!”
这“砍”法一传十,十传百,成了晋中人的面魂。
如今这面,讲究个“刀不离面,面不离刀”。
面团要“一斤面三两水”,揉得筋道滑溜,削时手腕一抖,面叶中厚边薄,入锅滚三滚,浇上肉臊子、番茄卤,再就瓣蒜,“圪蹴”在门口吃,那叫一个“耐嚼”!
2008年它还成了国家级非遗,全球人都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
这口面,吃的是烟火气,嚼的是千年时光,你说是不是?

两百年光阴里从平壤街头小摊走进朝鲜族节日餐桌的味觉纽带。
据《东国岁时记》载,它诞生于19世纪中叶平壤、咸兴,分“水冷面”和“拌冷面”两种。
农历正月初四吃冷面是“长寿面”,寓意健康长寿,
民间还叫它“盒勒面”,用木盒压制得名。
传说唐朝时从中国传入朝鲜,后更名“水冷凉面”,如今已成为朝鲜族的文化符号,连汤带面吃个精光,浑身透着“敞亮”劲儿。
这冷面,劲道得跟东北冰溜子似的,吸溜一口,
酸甜辣咸在嘴里“打架”,却打出夏天的清凉。
面条是荞麦、小麦混着淀粉压的,汤是牛骨、鸡肉熬的,配上黄瓜丝、鸡蛋片、泡菜,撒把芝麻,浇勺辣酱,那叫一个“得劲”!
冷面不只是食物,更是朝鲜族的“魂儿”。
夏天解暑,冬天暖胃,吃进嘴里,凉丝丝的,直窜心窝子,让人直呼“真中”!

这抹源自绳文时代的粗粝烟火,在江户街头熬成了千年食魂。
它诞生于镰仓僧侣的磨盘,唐风东渡时裹着荞麦香,江户百姓把荞麦粒揉成面,切得细如发丝,蘸着柴鱼酱油汁,嗦一口,便咬碎了旧年的灾厄。
这“年越荞麦”的规矩,从平安时代传到如今,除夕夜必吃,图个“断灾”的吉利,
连搬家都要送邻居一碗,道声“そばを食べて(嗦碗面吧)”,像极了咱老辈人说的“远亲不如近邻”。
冷吃时,面过冰水,弹牙得像咬住春天的尾梢,蘸汁里浮着山葵的辛、葱花的鲜,一口下去,凉丝丝直窜天灵盖;
热吃则泡在暖呼呼的汤里,吸溜吸溜,暖意从胃里漫到指尖,连汤底都要喝得精光。

传说唐时高僧空海从长安带回制面术,在香川县赞岐落地生根。
那时濑户内海缺米,空海以麦面救民,成就“赞岐乌冬”的传奇。
江户时代,这面从僧院走进市井,成为平民的“热汤暖食”,街头摊贩飘着酱油香,连大名都爱这口筋道。
如今四国香川的乌冬仍是日本第一,
当地人管它叫“うどん”,咬着“咔嚓”响,像嚼着阳光晒过的麦浪。
这面粗得实在,直径两三毫米,热汤配出汁鲜得掉眉,冷面蘸芥末酱油爽到心尖。
秋田稻庭的细乌冬滑溜溜似泥鳅钻泥,长崎五岛的加了山茶油,细而不烂。
日本人吃它不分四季,
这碗面,是刻在日本人骨子里的烟火气,连除夕夜都要来一碗“跨年乌冬”,
图个长寿安康,比啥补药都实在!

地道京味儿,源自清朝。
传说努尔哈赤行军时“以酱代菜”,清军入关后百姓效仿,将黄酱与甜面酱按3:1调和,
五花肉丁煸至金黄,慢火熬出“油酱分离”的酱香。
慈禧西逃时在西安尝此面,赞“再来一碗”,回宫后带入宫廷,后经民间改良,
成“小碗干炸”技法。
酱需文火慢熬三遍,每遍加葱碎提香,最终浓稠如琥珀,挂面不坨,油亮不腻。
面条讲究“手擀筋道”,
和面加盐碱,醒透后擀薄切条,过凉水“拔丝”,冬吃“锅挑儿”热乎,夏吃“过水面”爽滑。
菜码随四季变换:
春有香椿芽,夏配黄瓜丝,秋用心里美萝卜,冬加腊八蒜,再淋点腊八醋,酸香解腻。
一口下去,酱香裹着肉丁,菜码脆生生,跟吃“七碟八碗”似的,
满口都是胡同里的烟火气,
连梁实秋都念叨:“没听说过用切面做炸酱面的,手擀才够味儿!”

源自中国却在日本扎根成魂。
明朝遗臣朱舜水流亡日本时,以面条款待水户藩主德川光圀,
这碗面藏着“以食会友”的东方智慧。
江户末期,横滨中华街的“来来轩”让拉面从贵族私享变为市井烟火。
1910年尾崎贯一招来中国厨师,一碗拉面配烧麦,让东京人排起长队。
二战后,美国廉价面粉与归国士兵的“中国胃”,让拉面从流动摊贩走进千家万户,成了“战后复兴”的味觉符号。
这碗面,汤头是魂。
博多豚骨拉面乳白浓汤,得熬足十二小时,猪骨胶原蛋白融得像化不开的亲情;
札幌味噌拉面咸辣浓稠,配卷面筋道得“咻”一声就滑进喉;
关西盐味拉面清透如山泉,撒把九条葱,香得直咂摸嘴儿。
面条有粗细,配菜有讲究,
叉烧得用猪肩肉,溏心蛋得腌成“味玉”,笋干得脆生生。

是四川自贡的“盐味传奇”,
道光二十三年(1841年),挑卤水工陈包包因伤转行,用扁担挑着铜锅走街串巷。
一头煮面,一头炖鸡,盐场工人端起这碗“热乎劲儿”,喊一声“老板,汤宽油大!”
便觉寒气退散。
这碗面,藏着盐帮菜的魂,
自贡矿盐提味,汉源花椒酥麻,宜宾芽菜脆香,辣得“巴适得板”,却不燥不呛,像极了川人骨子里的韧劲。
如今这碗面,面条细如银丝,筋道滑溜,臊子肉末酥香如“酥麻”入口,红油辣子亮得能照见人影,配一撮豌豆尖,鲜得人直咂嘴。
汪曾祺曾赞其“面细无汤,麻辣味鲜”。
它从盐场挑担到成都街头,又漂洋过海火到香港米其林,可那口“盐都老味道”始终没变,
这碗面,不讲排场,只讲实在;不追时髦,只守本味。

是意大利的“命根子”,可这口面咋来的?
说法多着嘞!
古罗马人为了存粮,把面揉成团、切条晒干,硬生生“憋”出这法子。
后来阿拉伯人带着硬质杜兰小麦和晒面技术来西西里,那叫一个“天作之合”!
12世纪西西里岛就有了《烹饪意大利面和通心粉的艺术》食谱,比马可·波罗回欧洲还早百来年。
咱可别被“马可·波罗带面”的传说“带沟里”了!
这面筋道得很!
杜兰小麦做的,耐煮不坨,咬着“咯吱咯吱”带劲。
配上番茄肉酱,酸香裹着肉末,滋溜一吸,“美滴很”!
中世纪人用手抓面,吃完舔手指头,后来贵族嫌“埋汰”,发明了餐叉,这叉子比耶路撒冷还金贵!

清朝嘉庆年间的“中华第一面”。
据甘肃文旅局资料,其根在河南怀庆府,
东乡族马六七从陈维精处学得“小车牛肉老汤面”技艺,带入兰州后,经陈和声、马保子等人提炼出“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绝活。
汤清如镜、萝卜白、辣油红、香菜绿、面黄亮,这标准一立,便是二百多年。
马保子1915年创制的“热锅子面”,更添“进店一碗汤”的规矩,热汤入口,直教人“攒劲”得发梢冒汗。
如今这碗面,早已不是街巷里的“穷鬼饭”。
面条分毛细、二细、韭叶等九种型,师傅拉面时“溜条”如舞,面团在指尖翻飞,拉出劲道弹牙的口感;
汤底用牛骨、鸡骨慢熬八小时,鲜得人直咂嘴。

这根面还在沸水里翻滚。
从四千年前那只陶碗出发,穿过汉唐的油星与冰渣,挨过灾年的饥馑与丰年的期盼,如今躺在你的碗里。
筷子挑起时,挂着番茄鸡蛋的暖光,也挂着爷爷那辈人舍不得吐的渣。
它见过地震的尘土,尝过移民的乡愁,熬过战火与禁令。
可它什么都没说,只是继续在锅里软下去,在齿间弹起来。
吃吧,吃下去的不是面,是时间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