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潮汕文化区,囊括了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市,这里的人们说着闽南语支系下独具特色的潮州话,也曾在近代史上书写过一段经济繁荣的辉煌篇章。然而,一场始于1943年的大饥荒,却将这片土地拖入了绝望的深渊,成为潮汕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痛。
若回溯至20世纪初,该地区的核心城市汕头,曾是全国瞩目的经济重镇。根据《广东省志》记载,自1907年起,汕头的经济步入全面繁荣期,其在全国的地位,堪比今日的深圳——商贸云集,财富汇聚,甚至有“随便在安平路、淮安街、万安街拉一个人,都能包下整栋茶楼”的说法,足见当时的富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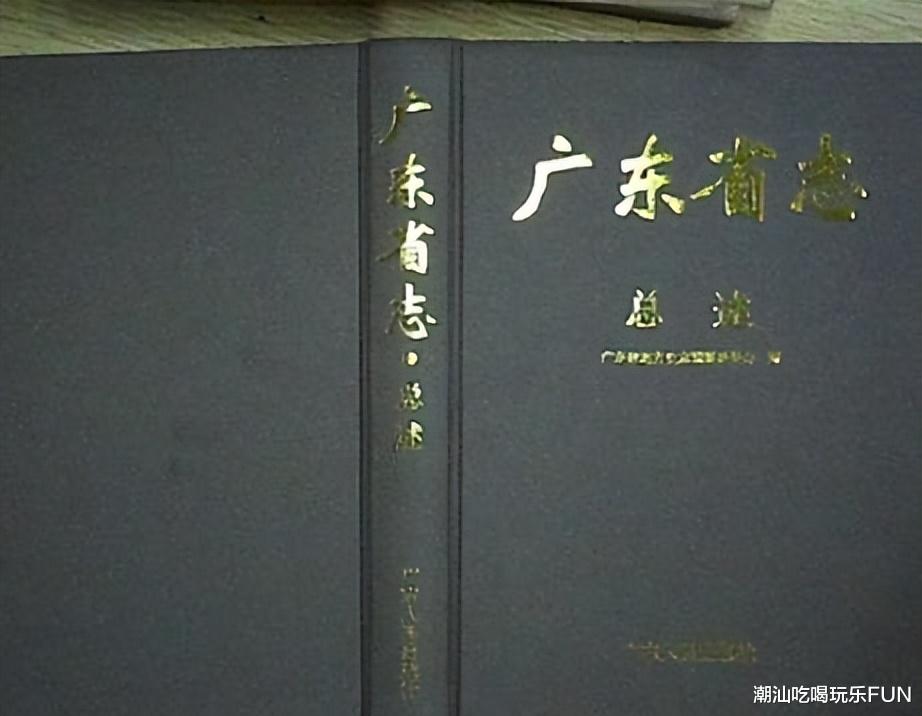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将汕头与广州一同划为省辖区,这意味着汕头正式跻身广东顶尖城市行列,其繁荣不仅滋养了自身,更带动了整个潮汕地区的发展。彼时的潮汕,虽已隐现“地少人多”的隐患,但依托汕头的商贸优势,各地官府每年从外地乃至外国购入粮食,尚能维系民众生计,民国时期的汕头更是每年需外购350万担大米,方能填补本地粮食缺口。
但谁也未曾料到,这份繁荣会在战火与天灾的叠加下,迅速崩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汕头连同整个潮汕地区的经济首当其冲,遭到毁灭性打击。而1943年的大饥荒,更是一场由“日军封锁、持续大旱、粮食断供”三重劫难交织而成的人间悲剧。
1939年6月21日,日本第23军攻占汕头,自此,潮汕地区的命运被彻底改写。日军为切断中国政府与海外的联系,实施“以战养战”策略:,三菱、三井、横山三家日本洋行掌控了汕头市的粮食供应,所有输入潮汕的粮食需先经日本洋行转手,再层层加价卖给本地商人、零售商,最终粮价暴涨至少4倍。

同时在潮汕沿海,渔民本以出海捕捞为生,但日军控制出海口,不准渔民出海,甚至凿沉绝大部分民用渔船,怕渔民与中国政府或抗日游击队联络。
1942年,当河南大饥荒的阴霾尚未散去,潮汕地区也迎来了致命的干旱。据幸存者回忆,这年冬天,潮汕大地滴雨未下,土壤干裂得能塞进拳头,长安县更是连续4个多月无雨,1000多亩稻田中,350亩彻底绝收。
到了1943年,灾情愈发严重,每亩稻田的收成不足60斤,这样的产量,别说养活一家人,就连两个人的温饱都无法维系。本就依赖外购粮食的潮汕,在日军封锁与大旱的双重夹击下,粮食危机瞬间爆发。

1943年1月,大饥荒席卷广东全省,97个县中有80个县受灾,而潮汕地区的灾情最为惨烈。 起初,灾民的饮食从一日三餐减至两餐,再到一餐,最终彻底断粮。他们被迫挖掘野菜、啃食树皮、煮食海草,可这些食物难以消化,吃多了便会丧命。
很快,街头开始出现饿死的灾民,而更令人绝望的场景接踵而至:有人抢食日本军马的粪便,有人吞咽观音土充饥;在流沙镇、藏龙镇等地,甚至出现“饥民围等同胞断气后分食”“人价贱过鸡狗,七八元一斤售卖”的惨剧。
粮食价格的疯涨更让普通民众绝望:汕头米价翻了6倍;揭阳县的白米,1942年每斗仅83元,1943年飙升至990元;普宁县的米价更是“一小时一个价”,5月5日每斗500元,11天后便涨至700元。这样的价格,早已超出了寻常百姓的承受能力。

政府曾在1943年5月先后拨付500万元、1000万元赈济款,可彼时抗日战争已到关键阶段,全国资源优先投入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等前线战事,这些赈济款终究是“空头支票”,未能落到实处。
广东省政府的表现更令人心寒,当时的省政府已失去对广州的控制,仅能管辖粤西及潮汕部分飞地,却仍未放弃敛财,计划将72万担粮食分“成本价售卖、免费发放、抚养孤儿”三类使用,可以一些官员却囤积粮食,迟迟不送往粤东灾区;本应“成本价”售卖的粮食,竟按市场价的75%出售,而彼时的粮价早已让灾民望而却步。更遑论日军的阻挠,让仅存的救济粮难以送抵沦陷区。
江西、湖南、广西等邻省,彼时也深陷困境:江西、湖南因支援长沙会战耗尽资源,连养活自身都成问题;广西作为抗战后方,需支援前线与远征军,无力再援助广东。最终,仅有湖南省在广东以海盐交换的条件下,拨付3000石粮食;不与广东接壤的湖北省,勉强拨出7万担粮食并借出2000袋军粮,但是这点物资,面对潮汕的饥荒,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绝境中,潮汕本地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努力,成为了黑暗中微弱的光。普宁县政府紧急派发200担稻谷,虽未能救尽灾民,却让部分人得以存活;揭阳县为防止霍乱爆发,成立中医师工会,推行饮水消毒、静脉注射等措施,降低了疫病传播率。 民间善堂更是扛起了救援重担,其中延寿堂每逢双日救济灾民,单日便能帮助2万多人,还接收了大量因饥荒被父母寄养的孩子。
海外侨胞也未曾放弃家乡,潮州联名厂厂长林之德捐款1.5万粤币,西贡巨富郭耀泰捐出6000粤币,柬埔寨华侨陈之芳更是冒险开辟“东新贿赂”秘密路线,成功将15万斤大米送回潮汕。 可这些努力终究有限:善堂在沦陷区缺粮的困境下难以长期支撑,侨胞的救济物资常因日军封锁滞后,等送到时,不少灾民早已离世。
为了活下去,潮汕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600公里外的江西、福建等地。在战火与饥饿的夹击下,逃荒之路布满荆棘。从汕头出发需步行半个月,途中要躲避日军,还要忍受饥寒,“中途填沟壑者有之”。即便抵达江西,当地也无足够物资救济,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江西再遭战火,不少逃荒者再度丧生。

据统计,1944年7月,登记到江西省的潮汕移民有7万多人,逃往福建的有10万人。直到2016年,当年的幸存者才陆续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而这场饥荒,最终导致汕头至海陆丰地区约50万人饿死,汕头市达濠镇更是失去了1/3的人口。
回望这场悲剧,潮汕“地少人多、极度依赖外购粮食”的短板,在日军封锁与天灾的叠加下被无限放大——这也是潮汕饥荒远比同期粤西、珠三角惨烈的核心原因。
而这段历史,也让我们深刻理解了国家设立“耕地红线”的意义:当一个地区的生存必需品过度依赖外界,一旦遭遇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1943年的潮汕大饥荒,是一段浸透血泪的历史。它不仅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天灾的无情,更警醒着后人:粮食安全,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安身立命的根本。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