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 许述工作室
李庄(6)
宜宾李庄作为抗战时期“四大文化抗战重镇”的重要支点,同济大学在此承担起核心枢纽的历史使命。如今探访李庄同济医学院旧址,穿过苍苔点染的砖红色门廊,仿佛走入时光的大门,墙面上泛黄的图画与室内一隅的解剖室复原模型仍在讲述西迁办学的故事——



李庄百姓对同济大学“吃人”义愤填膺
这组影像背后承载着一个轰动性历史记忆——“同济大学吃人”,此事在当年闹得沸沸扬扬。同济大学历经千辛万苦,从上海滩一路西迁来到川南小镇李庄,才把行李归置妥当,还没站稳脚跟,就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李庄的老百姓既怕又恨,想方设法要将同济师生轰出门外。
同济大学当时下辖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其中医学院入驻祖师殿。作为医学必修核心课程的“人体解剖学”在此特殊时期仍坚持开设。一天,师生们在祖师殿的花坛上搭起一块木板,并把一具尸体抬出来放在木板上,准备操刀解剖。好巧不巧,一个当地的泥瓦匠正好在祖师殿的屋顶上修缮房屋,看到一具尸体被一圈人围着,这帮人拿着刀子把尸体“大卸八块”……当地工匠哪见过此等“恐怖”场景,他以为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师生杀了人要分尸啃食尸体!自己如果被发现了,肯定也会被捉去吃掉,吓得要死,从楼梯上滚了下去,逃之夭夭。随后,泥瓦匠逢人便把亲眼所见的恐怖情景以及自己“虎口脱险”的经历添油加醋大讲特讲。

当年,同济大学医学院浸泡解剖用尸体的花坛和池子
越是闭塞落后的地方,流言传播得越快,往往传着传着还会更加夸张变形。一夜间,“同济大学吃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李庄镇。镇上人明里不敢撵客,暗地里却默契地筑起无形高墙——百姓有事要路过医学院,宁可多绕半里路也不打从其墙角过;当地商贩见同济大学的人来买东西,不管对方出多少钱都不卖。
李庄本地人对“外来户”同济大学充满敌意,虽然近在咫尺,却老死不相往来,还千方百计想让同济大学“滚蛋”。怎么办?
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周均时憋出个绝招,三下五除二就解开了李庄人的心结。他让医学院敞开大门,把平日里藏着掖着的“开膛课”大大方方亮出来,让百姓们都来参观,展览时间长达7天,让大家都看个够看个明白。这样的活动在李庄简直是破天荒,大家既害怕又好奇。等到白天开展时,十里八乡的人全都聚了过来看“稀奇”,祖师殿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

“人体解剖展览”
一进展厅,两边分别摆放的骨架映入眼帘;往里走,玻璃缸里琥珀色液体中泡着五脏六腑;待到最里间,灯光下泡着环抱膝盖的老者、少女、婴童,空气中弥漫着福尔马林的气味。现场不仅有讲解员解疑释惑,医学院的师生们还拿着手术刀划开皮肤肌理,一边解剖一边解释:这个部位叫什么,容易得什么病;并叮嘱大家染病了要去同济大学医院医治。还有老人当场问诊,说自己哪里不舒服,问得了什么病,医学院师生们开启了现场诊疗。不少老人很感慨: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知道咋回事,这回是长了见识了!当然,也有胆小的,有的跌坐在青石板上干呕,有的每晚噩梦连连。
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连有些身份的人也未曾见过这种“人体解剖展”。南溪县团练局局长洪汉中之子洪恩德后来回忆说:“展览过后,群众对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由误解变为理解,全部拥护了。做生意的说‘下江人’不吃人,他们买什么就给他们送去。有的说‘下江人’有钱,没有当地人抠门,不太跟生意人计较。农民们听了就很乐意卖东西给他们。镇上有人生了病,也找他们看,关系好得很。”(作家岳南于2003年10月3日在李庄采访洪恩德记录,见岳南:《那时的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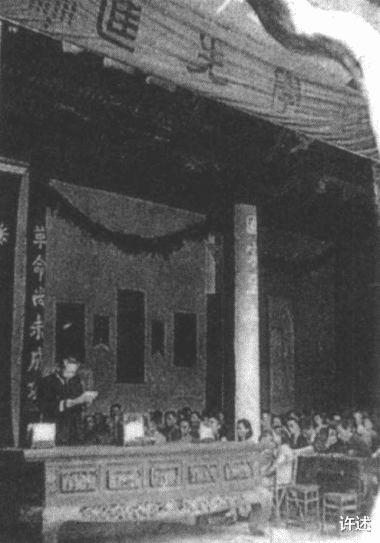
同济大学35周年校庆
这场特殊的医学展览彻底解开了同济大学与李庄百姓之间的误会,而同济为李庄办的另一件大事,则真正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当时,李庄等川南地区流行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疾病,当地人称之为“耙病”(耙音pa,是四川方言发音,意思是“软瘫”)、“痹病”、“麻脚瘟”。染上这种病,轻则全身乏力,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则肚子痛,上吐下泻,先是脚麻,然后扩散到四肢,再发展到胸部基本就没救了。这种怪病自清代就有了,一直找不到病根儿,也就未能根治,长期危害百姓。方圆百里的郎中大夫都摇头,省里的名医也束手无策。所以,川南的老百姓对“耙病”十分恐惧,到医院看医生也没用,只能通过击鼓、放鞭炮等“迷信”的方式,意图吓跑病魔。
同济大学迁到李庄不久,当地就发生了一起集体感染“耙病”的大事件——宜宾中学的37名师生在一次聚餐后突然发病。人命关天,宜宾中学的领导紧急求助于同济大学,既然当地医院对这病没招,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同济大学或许有办法。这一次,宜宾中学算是找对人了。
同济大学最初是靠医学起家的,而且和德国有很深的关系。“同济”这个名字其实是上海话里德语“Deutsch”(意为德国)的谐音,取同舟共济之意。早在一百年前的1920年代,上海同济医院就已经和北京协和医院齐名,号称“南同济北协和”。如果说现在的同济大学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同济大学医学院就是当初这棵大树的根儿。

接到宜宾中学的求救,同济大学立即派出了医学院的唐哲教授(1905-1993),这位四川广安籍的医生可谓是不二人选。他1930年从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就留校当校医,医术精湛,经验丰富。当年上海沦陷前,有人拉他合伙开私人医院过安稳日子,但他宁愿跟着学校跋山涉水迁到李庄,既不愿在日军占领区过仰人鼻息的生活,也有心回乡帮助老乡。唐教授诊断认为是钡或磷中毒,对症治疗后果然药到病除。

老年唐哲

同济医学院(搬到宜宾县城)
毒解了,人救过来了,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同济医学院的教授们喜欢刨根问题,从源头和根本上解决医学难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毒?同济医学院的杜公振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用动物多次试验,终于查到了“罪魁祸首”——宜宾中学的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这种食用盐是四川乐山五通桥生产的,是很多单位和家庭的生活必需品,长期使用可能导致慢性中毒——这就是为什么“耙病”在川南频发的原因。

杜公振
同济大学医院这一发现轰动一时。专家团队再接再厉,对“耙病”提出了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对此,川南老百姓十分感激,大家舞龙舞狮纷纷前往同济大学表示祝贺和感谢,并颁发了旌表,上书:“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声誉日隆。”(江鸿波等编著:《烽火同济:在李庄的日子里》,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9页)这段医民情深的佳话,成为抗战时期同济大学西迁李庄的重要历史见证。
唐哲精于临床诊疗,杜公振则长于医学理论研究。杜公振是山东高密人,微生物学专家,193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后赴德国杜根大学医学院深造并获博士学位,1939年归国后任教于母校,担任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其与助教邓瑞麟合写的学术论文《痹病之研究》获得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创下抗战时期医学研究领域重要突破。杜教授常常对学生说:“一个伟大的医生,是以造福人类为其终生工作目标,而不以医学为个人图利的工具。”(江鸿波等编著:《烽火同济:在李庄的日子里》,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