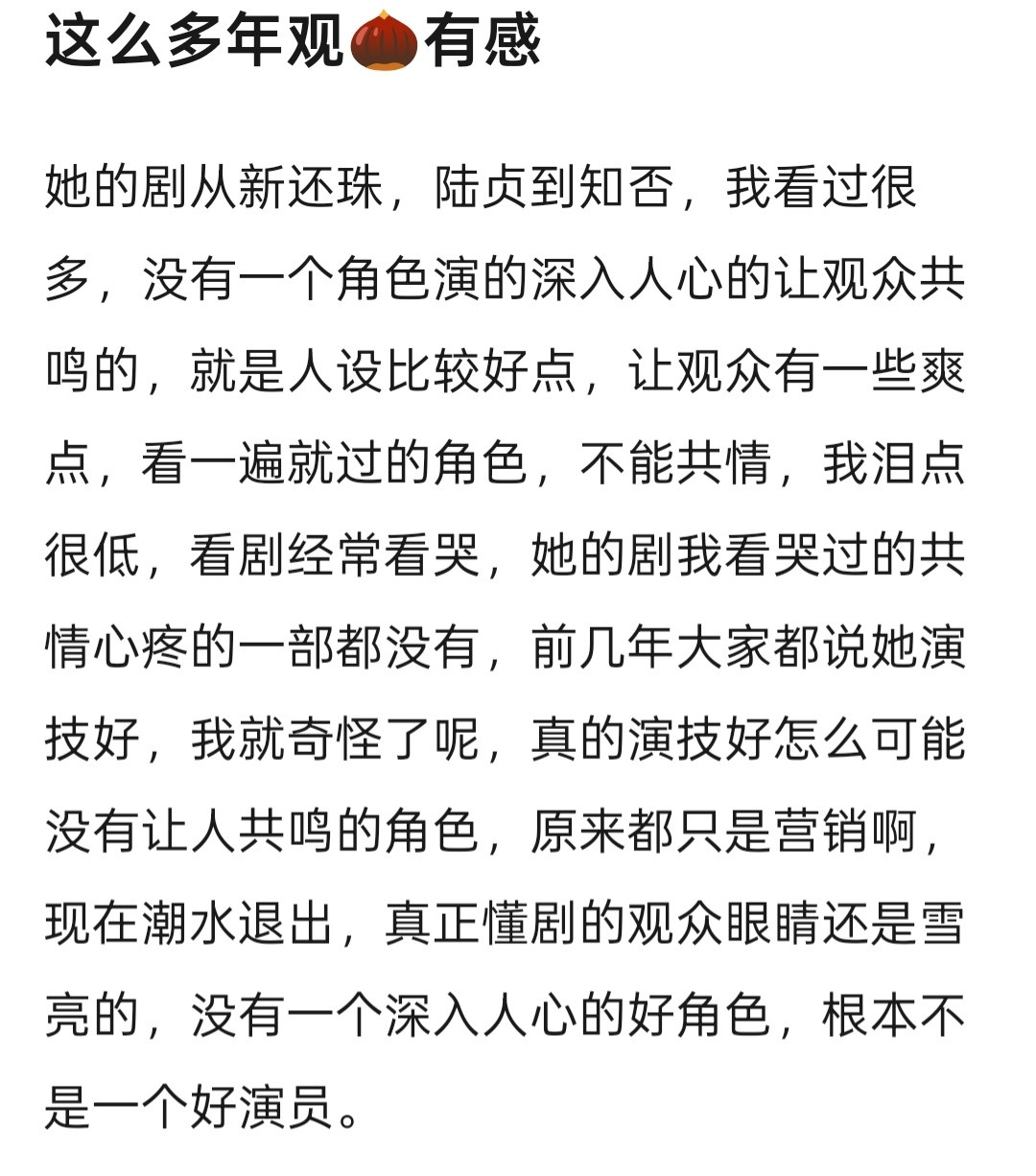第七章 断层线
陆川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车开回老房子楼下的。王韬绝望的声音还在耳边嗡嗡作响,混合着沈静愤怒的哭喊和胃部那顽固的、逐渐加剧的绞痛。世界像一张被水浸透又晒干的宣纸,布满了扭曲脆弱的褶皱,每一次呼吸都扯得生疼。
他把车歪歪扭扭地停进车位,熄了火,却连拔下钥匙的力气都没有。额头抵在冰凉的方向盘上,金属的寒意渗进皮肤,稍微缓解了一下颅内的胀痛。药效彻底过去了,疼痛不再是尖锐的绞拧,而是一种深沉的、弥漫性的钝痛,从胃部辐射到整个胸腔,沉甸甸地坠着,每一次心跳都带来沉闷的回响。
不能倒在这里。他对自己说。至少,不能倒在车里。
他几乎是爬出驾驶座的,扶着车门,稳住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傍晚的风带着凉意,吹在汗湿的背上,激起一阵寒颤。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一片昏暗。他摸索着墙壁,一级一级往上挪,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钥匙对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推开门,屋子里一片漆黑,寂静无声,只有窗外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透过没拉严的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条冰冷的光带。
他踉跄着走到沙发边,瘫倒下去。身体陷进破旧的弹簧里,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黑暗和寂静包裹上来,像一层粘稠的、不透气的茧。王韬的求救,沈静的危机,李蔓阴毒的笑脸,林薇审视的目光,还有悠悠那双盛满不安和困惑的眼睛……无数画面和声音在脑海里冲撞、爆炸,最后都沉淀为胃部那持续不断的、几乎要将他吞噬的痛楚。
他需要药。医生开的药,或者更猛的止痛片。他挣扎着想坐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猛地袭來,他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眼前金星乱冒,喉咙里泛起腥甜的铁锈味。咳完,他瘫在沙发上,像一条脱水的鱼,只剩下胸腔剧烈的起伏。
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敲响了。
笃,笃笃。不重,但很清晰,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陆川不想动,也不想应。他希望门外的人以为没人,自己离开。
但敲门声又响起了,这次更坚定了一些。“陆川?你在里面吗?”是苏柠的声音,隔着门板,有些模糊,但能听出关切。
陆川闭上眼,没有回应。他现在这副样子,不想被任何人看见,尤其是苏柠。她那过于明亮的、充满生活气息的眼神,会照出他此刻的狼狈不堪,像阳光照进堆满污垢的角落。
门外安静了片刻。就在陆川以为她已经离开时,钥匙插入锁孔、轻轻转动的声音传来。门,被推开了。
走廊的光线泻进来一道,勾勒出苏柠站在门口的轮廓。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逆着光,看不清表情。
“你果然在。”苏柠的声音平静,没有惊讶,也没有责备。她走进来,顺手打开了墙上的开关。老旧的日光灯管闪烁了几下,惨白的光线瞬间充满了狭小的空间。
陆川下意识地抬手遮了一下眼睛,然后才放下手,看向苏柠。她穿着家居服,头发松松挽着,手里端着一个小砂锅,正看着他,眉头微微蹙起。
“我听到你咳嗽,还有上楼的声音……不太对劲。”苏柠把砂锅放在旁边那张摇摇晃晃的小桌上,目光落在他惨白的脸、汗湿的头发和微微痉挛的手指上。“你脸色很差。病了?”
陆川偏过头,避开她的视线,声音沙哑:“没事。有点累。”
“这叫有点累?”苏柠走近两步,蹲下身,平视着他。她的眼神直接,带着一种不容敷衍的认真,“你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手在抖。是胃疼?还是别的?去医院看了吗?”
“看了。”陆川简短回答,不想多说。
“药呢?吃了没?”
陆川指了指散落在沙发另一头的药袋。
苏柠过去,拿起药袋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空着的水杯。“吃饭了吗?”
陆川摇头。从早上那片止痛药之后,他什么都没吃,也吃不下。
苏柠没再问,转身去了他那简陋的厨房。很快,传来烧水的声音,还有碗碟轻碰的脆响。她端着一杯温水和一小碗熬得稀烂的白粥过来,粥里飘着几粒切得碎碎的青菜末,几乎看不到油星。
“先喝点水,把该吃的药吃了。”她把水杯递给他,语气是不容置疑的,“然后,把这碗粥喝了。我熬的,很烂,不伤胃。”
陆川看着她,没有接。这种被照顾的感觉,在此刻不仅没有带来慰藉,反而像一根刺,扎破了他竭力维持的、最后一点体面的伪装。他不需要同情,尤其是来自一个几乎算陌生人的邻居。
“我自己来。”他生硬地说,伸手去接水杯,手指却不听使唤地颤抖,差点把水洒出来。
苏柠没松手,稳稳地托着杯子,另一只手扶住他的手腕,帮助他把水杯送到唇边。“别逞强。”她的声音低了一些,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先把药吃了。身体垮了,什么都做不了。”
也许是太虚弱,也许是那杯温水的诱惑,陆川最终放弃了抵抗。就着苏柠的手,吞下了医生开的几种药片。苦涩的味道在口腔里蔓延,但温热的水流顺着食道滑下,暂时抚平了一些胃部的焦灼。
然后,苏柠又把那碗温热的青菜粥递过来。粥熬得极好,米粒几乎化开,青菜的清香很淡。陆川机械地一口口吃着。温热的食物进入空荡荡、备受折磨的胃里,带来一种近乎疼痛的舒适感。他吃得很慢,额头上又渗出细密的汗,但这一次,似乎不只是因为疼痛。
苏柠没有离开,就坐在旁边一张小凳子上,安静地看着他吃,没有说话。屋子里只有他喝粥时轻微的吞咽声,和日光灯管发出的细微嗡鸣。
一碗粥见了底。陆川放下碗,感觉那股冰冷的、坠胀的痛楚似乎被这碗温热的粥暂时逼退了一些,困意和更深沉的疲惫席卷而来。
“谢谢。”他终于开口,声音依然沙哑,但比刚才多了一丝人气。
“不客气。”苏柠站起来,收拾碗筷,“你睡会儿吧。我看你这样子,得好好休息。”她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着他,“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事,但病成这样一个人硬扛,不是办法。”
陆川靠在沙发里,没有回应,只是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苏柠轻轻带上了门。
黑暗重新降临,但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绝对,没有那么冰冷。胃里残留着粥的暖意,喉咙里还残留着温水的滋润。身体依旧沉重疼痛,但意识却像一艘颠簸太久的小船,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强可以停靠的、浅滩般的睡眠。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是被手机持续的震动吵醒的。天已经黑透了,屋子里只有手机屏幕幽蓝的光在闪烁。是张律师。
陆川费力地摸过手机,接通。
“陆先生,”张律师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专业,但语速比平时快了一些,“有两件事需要立刻向您汇报。”
“说。”
“第一,关于李蔓女士。她通过她的代理律师,正式向法院提交了申请,要求以‘您近期不稳定的精神及生活状态可能对子女成长不利’为由,重新评估并争取对陆悠悠的部分探视权,乃至可能提出变更抚养权的动议。沈静女士已经收到相关通知。”
陆川的心脏猛地一缩,睡意全无。李蔓……她果然不肯罢休。从打击沈静的事业,到直接争夺悠悠。她要把他身边的一切都撕碎。
“第二,”张律师继续道,声音里多了一丝凝重,“是关于‘启明资本’。情况比预想的更糟。王韬先生……未能稳住局面。银行抽贷引发连锁反应,几家主要投资方也萌生退意,要求提前赎回份额。竞争对手趁机压价收购散落股权,市场谣言四起。现在公司股价已经……跌破了安全线。王韬先生本人,可能面临董事会的集体诉讼,指控他管理不善,导致公司资产重大损失。”
陆川听着,感觉身体里的温度在迅速流失。王韬顶不住了。他留下的帝国,正在他眼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那些他曾经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一切,那些数字,那些关系,那些荣耀……都成了压在王韬身上、最终也将反噬他自己的巨石。
“陆先生,”张律师顿了顿,“虽然您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但您毕竟是创始人,持有过大量股份,这场风暴……恐怕很难完全将您撇清。尤其是,如果王韬先生那边撑不住,一些法律责任和债务追索……”
“我知道了。”陆川打断他,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密切关注。有任何新进展,第一时间告诉我。”
挂了电话,他在黑暗里坐了很久。胃痛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李蔓的法律攻势,王韬和公司的绝境,像两条狰狞的断层线,在他试图重建的生活地基下骤然裂开,深不见底,酝酿着足以吞噬一切的崩塌。
他想起苏柠端来的那碗温粥。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暖意,在这巨大的、冰冷的危机面前,像一个苍白的玩笑。
他慢慢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城市的灯火依旧璀璨如星河,冰冷而遥远。他看到了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影子,模糊,扭曲,像一个随时会消散的幽灵。
清单早已不知被丢到了哪个角落。那些“学会做菜”、“接送上学”、“弄懂女儿喜好”的条目,在“前妻破产危机”、“女儿抚养权争夺”、“昔日帝国崩塌”、“自身健康告急”这些沉重如山的现实面前,轻飘得像一声叹息。
断层已经出现。生活的板块正在剧烈碰撞、错位。而他,站在震中,脚下是不断扩大的裂隙,头顶是摇摇欲坠的天空。下一步该迈向哪里,才能不至坠落?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碗粥带来的短暂暖意,正在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浸入骨髓的寒意,和一种近乎麻木的清醒。风暴并未过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从四面八方,将他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