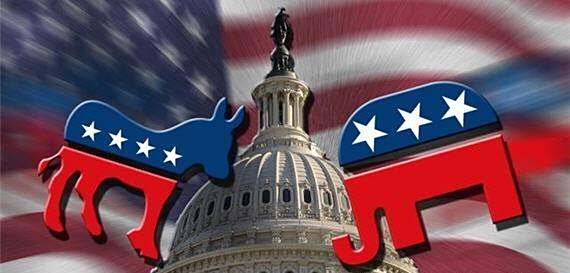
话说公元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初立,江山乍定,百废待兴。开国太祖华盛顿陛下,连同他手下的几位能臣——比如笔杆子犀利的詹姆斯·麦迪逊,正为新制定的联邦宪法能否通过而操心。麦迪逊同志熬夜写下雄文《联邦党人文集》,其中苦口婆心地告诫百姓:拉帮结派搞“党争”,乃是祸国殃民之首恶,不利于团结,有害于大局!华盛顿陛下在告老还乡(退休)的告别演说中,更是语重心长,把“党派意识”批得跟明朝的阉党似的,提醒大家要万分警惕。这场景,像极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立下“内臣不得干政”的铁牌,生怕后世子孙被朋党所误。然而,历史最爱开的就是这种玩笑。话音未落,麦迪逊和另一位大佬托马斯·杰斐逊就坐不住了。他们眼睁睁看着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据说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就是他代笔的)权力越来越大,政策全是偏向北方做生意的大商人。这还了得?咱美利坚明明是农业立国,南方种烟草的庄园主和西部开荒的农民才是根本啊!于是,一幕经典的“真香”定律上演了。曾经最反对党派的人,亲手搞起了第一个现代党派——民主共和党。麦迪逊和杰斐逊这二位,好比是明朝里一开始反对设立内阁,后来自己却成了内阁首辅的官员,为了对抗他们认为的“错误路线”,不得不“以身试法”。这其中的讽刺意味,足以让人捧腹。
一、朝廷初立,两派相争
其实,这最初的党争,倒不像后来为了争权夺利那般污糟,更像是一场关于国家道路的“路线大辩论”。汉密尔顿一派,自称“联邦党”,认为新生的美国弱不禁风,必须有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搞经济、办大事、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这好比明朝的“集权派”,主张中央要手握重权。而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民主共和党”,则坚信美国的前途在广阔的田野,应该让各州自己管好自己的事,中央权力不能太大,免得成了欺压百姓的恶龙。这活脱就是明朝的“乡绅自治派”。两边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但说到底,都觉得自己是为国为民,是正义的一方。这种情形,像极了明朝朝堂上清流与浊流、浙党与东林党的辩论,起初也都是怀着理想,只是立场不同。就连德高望重的华盛顿陛下,虽然努力摆出超然姿态,但内心还是更偏向老部下汉密尔顿的主张。这就好比皇帝虽然不说,但心里自有倾向,让下面的派系斗争更加微妙。
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1796年,华盛顿陛下坚决不肯连任第三届,开了个和平交权的好头(这点比很多封建王朝强多了)。第一届真正的“皇位”争夺战,就在联邦党的约翰·亚当斯和民主共和党的杰斐逊之间展开。结果亚当斯以微弱优势胜出。按当时的规矩,输家杰斐逊得去给赢家当副手,也就是“副皇帝”。这局面别提多尴尬了,好比太子争位失败,还得天天在胜利者身边站着。但杰斐逊居然认了!这在美国“国史”上可是关键一步,意味着大家开始按规矩办事,输了认栽,不搞武力政变。到了1800年大选,好戏又来了。这次杰斐逊卷土重来,和搭档阿龙·伯尔票数一模一样,都比亚当斯高。这下糟了,龙椅有两个人抢,而且决定权落到了被对手联邦党控制的众议院手里。朝廷内外谣言四起,说是有阴谋交易。众议院一连投了35次票,才终于把杰斐逊推上宝座。经此一役,虽然过程惊险,但亚当斯愿赌服输,和平交出了权力。这在美国可是破天荒头一遭,确立了“皇帝”也能通过投票换人的规矩,而政党,就是组织这场“夺嫡大战”的核心力量。从此,政党这玩意儿,就算是在美利坚的土壤里扎下了根。有趣的是,最初的失败者联邦党,因为政策太精英化,又不屑于讨好老百姓,没过几年就自己凋零了,成了历史书里的一个名词。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江湖上混,群众基础很重要,光有高层支持,迟早要完蛋。
三、乱世出枭雄,分肥成惯例
联邦党一没,天下成了民主共和党一家的。但党内没了对手,自己人就掐起来了。1824年大选,四位候选人同出一门,活像一场激烈的“党内初选”。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票最多,但没超过半数,结果众议院把宝座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老亚当斯的儿子)。杰克逊阵营大骂这是“腐败交易”,憋着一股劲要在下次夺回来。1828年,杰克逊果然成功“逆袭”。这位老兄是行伍出身,脾气火爆,信奉“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一上台,就把朝廷里前任的官儿们大规模撤换,安插自己人,美其名曰“轮流做官,防止腐败”,实则开启了“分肥制”的先河——选举获胜的一方,有权瓜分胜利果实(官职)。这好比新皇登基,大肆封赏自己的从龙功臣,把前朝旧臣清扫出门。这个时期,政党开始像模像样地组建“班子”,从地方到中央,层层都有组织,负责拉票、动员、甚至给新移民提供帮助来换取选票,形成了所谓的“政党核心团体”,就像一个个地方上的“小朝廷”或“帮会”。
四、奴隶制惹风波,旧党裂新党出
好景不长,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奴隶制,像幽灵一样缠上了美国政坛。原来的两党(此时民主共和党已演变成民主党,而反对杰克逊的人组成了辉格党)都对此含糊其辞,想和稀泥。但民意如火,压是压不住的。一些有良知的人成立了反对奴隶制的第三党,如同明末的民间结社,不断呐喊。终于,在1854年,一个全新的、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政党——共和党——横空出世。它迅速崛起,取代了软弱的辉格党,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对手。1860年,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皇帝”。南方蓄奴州认为这日子没法过了,纷纷宣布独立,最终引发了南北战争。这场大战,从根本上说,就是政党路线斗争无法在朝堂上解决后,最激烈的表现形式。
五、新政定乾坤,联盟大洗牌
内战之后,民主党在南方势力稳固(因为南方人恨林肯的共和党),但在全国层面,共和党优势明显。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场空前的大萧条改变了一切。当时的共和党总统胡佛,信奉“无为而治”,觉得政府不该过多干预经济。但老百姓饿着肚子,哪听得进这个大道理?于是,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DR)横空出世,他推行“新政”,大意就是:政府要大手大脚花钱,搞建设、发救济、管这管那,带大家渡过难关。这一下,选民联盟彻底重组。民主党不再是那个主要代表南方农民的党了,它变成了城市工人、穷人、少数族裔、工会和知识分子的“大帐篷”。而共和党,则更坚定地成为了商业、富人和保守派的代表。这次“政治地震”的影响,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随后的几十年,两党阵营又经历了不少微调。比如,原本支持民主党的南方白人,因为受不了民主党在民权问题上的进步立场,逐渐转向共和党;而一些原本倾向共和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则加入了民主党。这分分合合,像极了江湖门派的势力消长,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全看“武功秘籍”(政策主张)是否对口。
六、技术焕新颜,本质犹未改
到了现代,政党的玩法又变了。不再是靠大佬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内定候选人,而是搞全民参与的“初选”;拉票也不再只是火炬游行和群众集会,而是上了电视、通了网络、用上了大数据。募捐可以在网上瞬间完成,攻击对手的广告可以精准投放到你家电视上。但无论形式怎么变,美国党争的核心没变:依然是两派人马,为了不同的理念和利益,在既定的规则下,争抢领导这个国家的权力。它有时吵吵嚷嚷,有时甚至有些丑陋,但两百多年来,这套机制大体上维持了国家的运转和权力的和平更迭。所以,回顾这段历史,就像看一本厚厚的演义小说。开头是几位理想主义者的担忧,中间是无数枭雄、政客、理想家和投机客的轮番登场,有高尚的辩论,也有肮脏的交易。但归根结底,这出名为“美国政党”的大戏,还在继续上演着。而看戏的我们,或许也能从中咂摸出一点关于权力、民意和历史的滋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