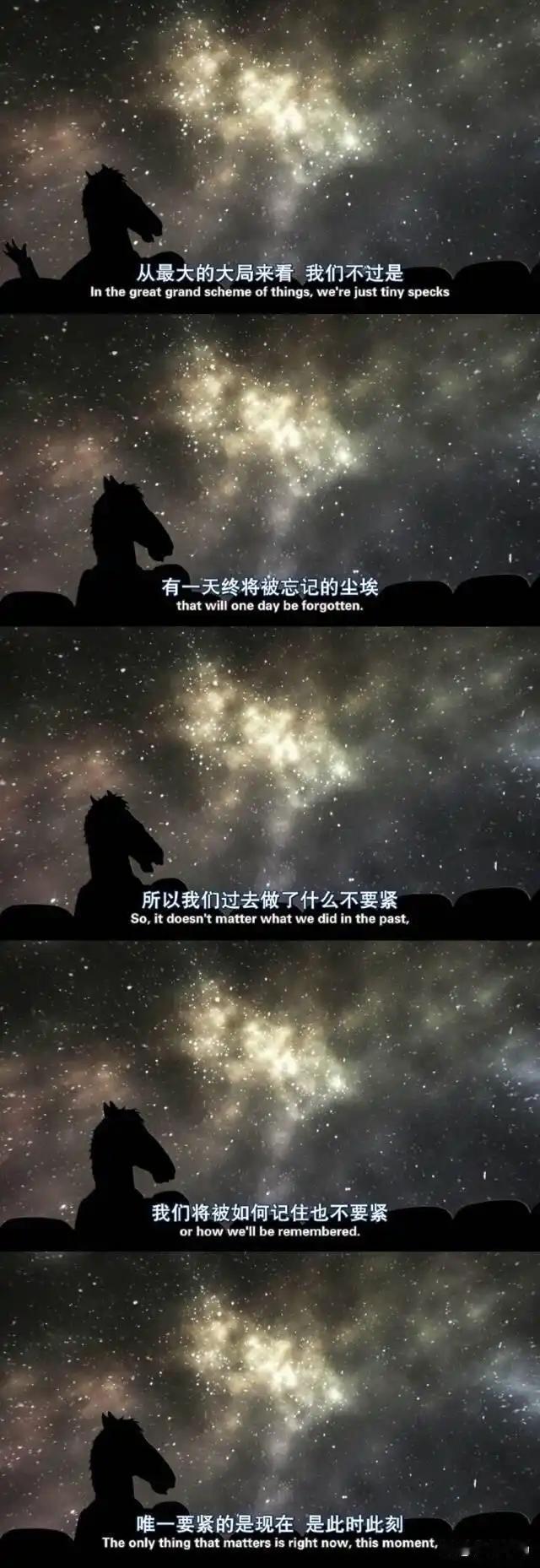性学专家李银河说:“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什么都不为,我们和一只蚂蚁,一棵树,一只甲壳虫,一粒灰尘,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一些物质,然后就这样死去了。” 2023年深秋,我在巷口修鞋摊遇见陈师傅。他正用锥子纳着一双翻毛皮鞋,桂花落在工具箱上,像撒了把碎金子。 "李银河那话,我在晚报上读过。"他突然开口,让我想起三天前写的那篇关于生命意义的采访提纲,"她说人跟蚂蚁没区别,可您看这鞋——"他举起半成品,针脚在阳光下闪着细光,"每双鞋都带着主人的故事,蚂蚁能留下啥?" 陈师傅的修鞋箱是1982年结婚时打的木箱,箱盖内侧用红漆画着囍字。 他说年轻时在国营鞋厂,觉得一辈子就该钉好每颗鞋钉;下岗后摆修鞋摊,发现每个顾客都是一本书:穿破芭蕾舞鞋的退休教师、鞋跟磨偏的出租车司机、总穿新球鞋却永远开胶的快递员。 "上个月有个戴助听器的大爷,说修鞋是为了多看看巷口的老桂树。"他用砂纸打磨着鞋底,木屑混着桂花香飘起来。 2019年冬,我在肿瘤病房遇见林阿姨,她正对着窗台上的多肉植物说话,化疗后的头皮泛着青茬。 "小李啊,"她指着叶片上的白霜,"李银河说人是消耗物质,可你看这肉乎乎的叶子,去年还是片枯叶,现在长出三个新芽。" 她床头柜上摆着褪色的笔记本,记着30年前当语文老师时学生的作文,最新一页写着:"今天教会护工小刘写'爱'字,她的孙子叫我'识字奶奶'。" 林阿姨总说自己像棵老桂树,年轮里刻着别人的故事:带过的三届毕业生、收养的流浪猫、甚至帮隔壁床病友写的家书。 "前几天小刘说,她学会写'爱'后,给老家的闺女寄了封信。"她摸着多肉新生的叶片,眼里映着窗外的阳光,"你说这算消耗物质,还是留下点啥?" 李银河的生命观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世俗的意义幻象,却让陈师傅和林阿姨这样的普通人,在修鞋钉、教写字、侍弄植物中,无意中反驳了存在的虚无。 这让我想起20世纪初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在《实用主义》里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经验链。" 就像陈师傅的修鞋箱、林阿姨的笔记本,都是普通人对抗虚无的温柔武器。 同类的生命叙事总在暗处闪烁:敦煌的壁画修复师在颜料里看见千年风沙,乡村教师在粉笔灰中播撒文明星火,甚至街角的早餐摊主,也在蒸腾的热气里记住每个熟客的口味。 这些"消耗物质"的过程,何尝不是在编织意义的网络?正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说:"意义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照亮。" 今年秋天再访巷口,陈师傅的修鞋箱旁多了盆多肉,是林阿姨临终前送的。 他正给一个穿汉服的姑娘修绣花鞋,针尖不小心刺破手指,血珠落在鞋面上。 "您看,"他笑着贴上创可贴,"连伤口都能变成鞋上的花。"老桂树的影子落在他佝偻的背上,像幅会呼吸的画。 我们总在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却忘了意义本身就在寻找的过程中。 陈师傅纳鞋时的专注、林阿姨教字时的耐心、甚至此刻桂花落在修鞋箱上的声响,都是存在的明证。 李银河的话像面镜子,照见生命的本质是空,却也让我们更珍惜每个"填空"的瞬间——那些被记住的笑脸、被修复的物件、被传递的温度,都是对抗虚无的最好答案。 陈师傅用了三十年磨秃二十把锥子,林阿姨在病房教会二十七个护工写字,他们都在"消耗物质",却也在创造着比物质更长久的东西。 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高悬的哲学命题,而是藏在修鞋时的一针一线、教字时的一横一竖、侍弄植物时的一呼一吸中。 当我们不再追问"活着为了什么",转而认真对待每个"如何活着"的瞬间,虚无便有了形状,存在便有了重量。 就像巷口的老桂树,春抽芽、夏成荫、秋开花、冬落叶,每个季节都在回答:生命的意义,就在这循环往复的照亮与被照亮中,在每个认真活着的当下,悄然生长。 或许,这就是普通人对存在主义最温柔的反叛——用具体的生活,给抽象的哲学,缝上一针带着体温的线。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文章为真实事件整理评述,无不良引导,文中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