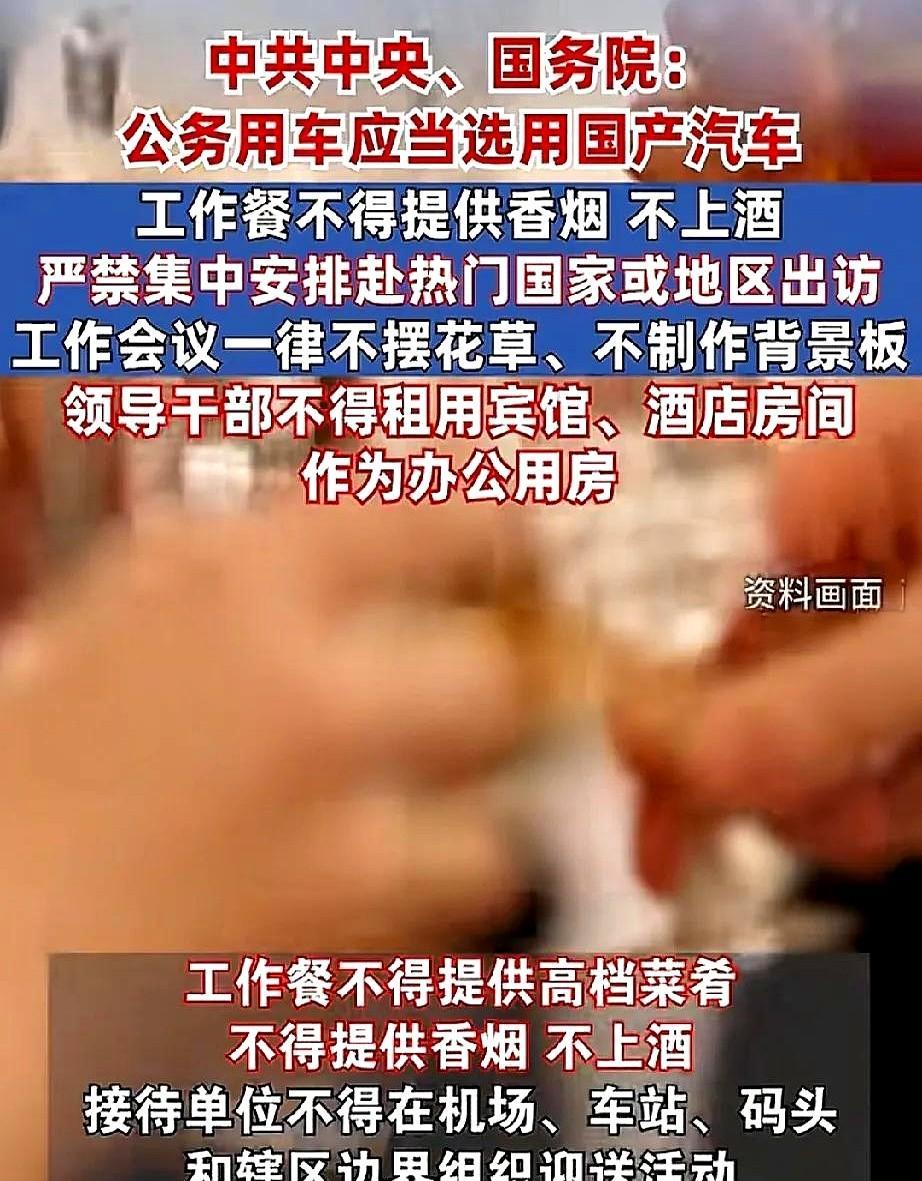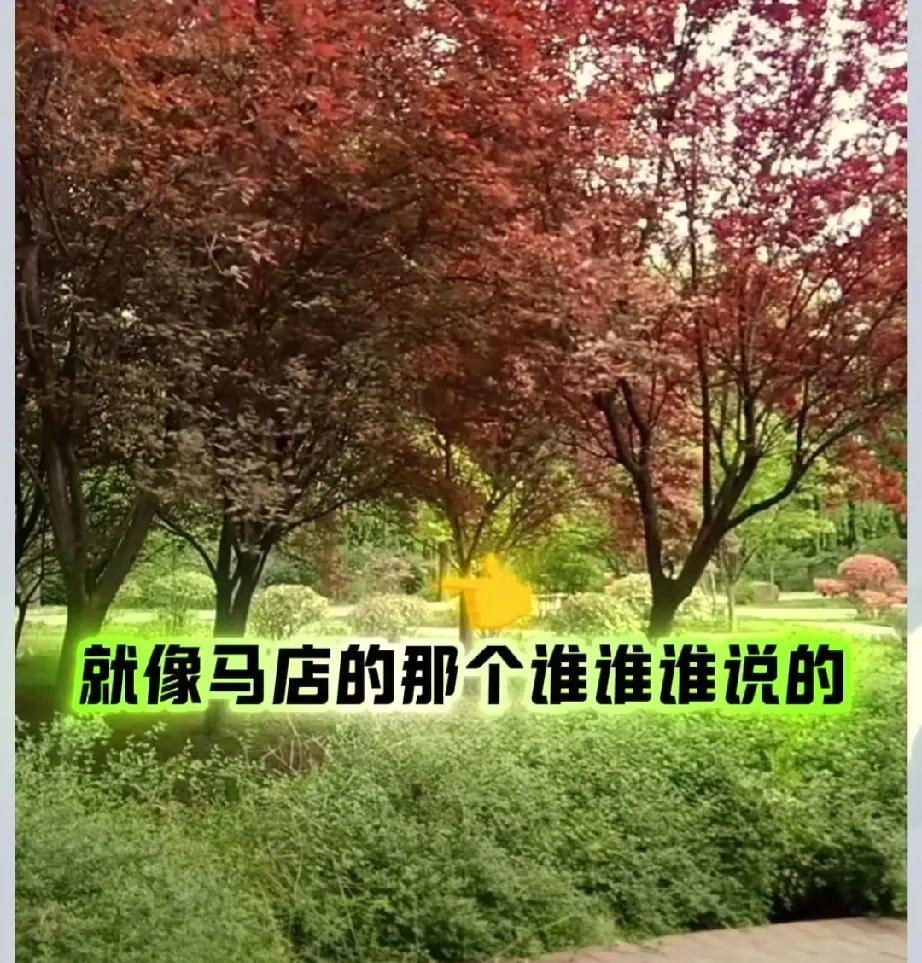在“杭州林”三期所在的四方墩,那些遥远的地表隆起,在几千年前曾是湖中的小岛。现在,人们发愿,要再用10到15年时间,用梭梭将它们串连。

飞机、高铁、汽车,换乘了三种交通工具后,杭州日报记者和读者代表一行人,抵达2600公里之外的甘肃民勤,实地了解、参与2025年的民勤春种,亲手播下绿色希望,见证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杭州力量。
5月,杭州花事正浓,民勤却在前些天经历了沙尘暴。“小马哥”马俊河(青梭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带领我们前往梭梭农庄。2025年的春种接近尾声,最后一批志愿者就要离开了。小马哥说,今天要在农庄宰一只羊感谢他们。
2025年为期81天的春种,从全国各地前后赶来了8000多名志愿者,这个数字创下新高,是往年的两倍多。他们和当地村民一起,种植梭梭、红柳、花棒、柠条、沙拐枣等沙生植物268.8万株,共9600亩,远超最初预计的5000亩。这让小马哥和他的治沙伙伴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这9600亩中,有1433亩梭梭来自杭州市民去年的捐种。而今年是杭州日报“党报记者绿色传递”公益治沙活动的第15年,杭州市民的捐款可种梭梭1464亩,这意味着明年春天“杭州林”的种植总面积将扩大到16700余亩,为民勤防沙治沙再添一抹西湖绿。
在“杭州林”第一期国栋村,沙漠已经开始泥化,兔子、蛇、老鼠、鹰、蜥蜴、狐狸等小动物栖居其间,林子里还有骆驼在游荡:啃食过于茂盛的枝条,踩踏老鼠洞。
在“杭州林”第三期四方墩,我们看到老鹰在空中盘旋,野生梭梭迎风生长。因为栽植了梭梭,就有了种子落下,当温度、水分同时合适的时候,就长出了野生的小梭梭,纵然风沙肆虐,仍然分外挺拔。
而寄生于梭梭根部的名贵药材肉苁蓉,在这些年也稳定产出,旱植给村民们带来收入,利润又能继续投入到梭梭种植中。
在这里,没有征服自然的豪言壮语,只有植物、动物、人类与风沙的长久对话——用耐心代替急躁,用协同代替对抗,每一个生命都是生态链的参与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年恰逢“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两山’启新程,治沙续华章”,这片广袤沙漠,人与自然正以生命之力,奏出和谐共生的交响曲。
昌盛村四迁
车行驶在村道上,寂静无声,门上崭新的“家和万事兴”横批,提示我们这里是有人居住的,他们一直对美好生活充满着向往。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去昌盛村。
2019年4月,我第一次和读者代表走入民勤,“小马哥”马俊河就带我们来过一次。
是不远的沙漠深处,种满梭梭,那是“杭州林”的第二期。
彼时对于昌盛村的印象,只记得村里的人家,门都紧闭。西北民居的墙很高,门密实得紧,看不出里面是不是住着人,流沙吞没了半堵墙——后来,在民勤防沙治沙纪念馆里,我看到了昌盛村的照片,一头驴正沿着沙堆走到了墙顶。
配图文字是,“沙上墙,驴上房”。
那人呢?
我翻出那天下午用无人机记录下的昌盛村视频,无人机从沙地上起飞,四周只有桨叶带来的风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镜头往梭梭林飞去,拉高俯瞰,林子里只有梭梭,以及打着旋儿的沙砾在空中细密地飞……
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六年后,老丁讲给我听了。
老丁叫丁有余,住在昌盛村六社八号。我们遇到他时,戴着口罩的他和围着纱巾的老伴正往农用三轮车上搬家具。
老丁子女双全,还有四个孙辈,都在内蒙古打工,一年只有春节回家,平时就是老两口过日子。
老丁的家是标准的西北小院布局,单人沙发、小茶几、四方餐桌上堆着杂物,一块绣着喜字的毛巾盖着收音机。三门衣柜的镜子已经裂开,露出银色的镀层。老丁说,这些都不打算带走了。
堂屋边上有一个月洞门,外墙已经被黄沙漫过。月洞门旁有一处建筑,一看就是后添置的,老丁说这是政府给修的卫生间,当年修好后就不用去村里上公厕了。
左手边是卧室,推门进去,地上一层薄薄的黄沙。门上写着“丁丰阳”三字,笔迹幼稚,是老丁的孙子的练字涂鸦,他当成宝贝也舍不得擦掉。
他说在这里已经住了31年。过不了多久房子就要拆了,他和老伴合计着把家里一些还用得上的家具运去新家——说是新家,也不新了,也已经住了五六年了,只不过他心里放不下老屋,定期回来打扫一下。
原来如此。难怪我们上次来时,昌盛村里了无人烟。
32年前,1993年5月5日,一场罕见的特大沙尘暴侵袭民勤。民勤治沙纪念馆里的描述是“风沙过处,掀砖揭瓦,阻路埋田,倒杆断线,折树摧苗”,这和后来2010年民勤遭遇的黑沙尘暴并列为沙尘暴典型案例。
老丁一家就是在1993年沙尘暴之后,在政府的帮助下重修新家,养儿育女,过上了“有余”的生活。
老丁家后面,寂寥一片。小马哥指着“杭州林”二期的腹地,说昌盛村以前在那儿,后来沙子来了,人和村庄就退了,盖了昌盛村二期,已经被沙漠吞噬得只剩残躯。
沙子不懂退让,和时间一样只管向前,于是昌盛村又搬了一次。第三次的村落沿着县道路边而建。为了防沙,当地人将房子转了个方向,用结实的后墙迎着沙尘。于是每刮一次沙尘暴,院子里的沙得用四轮拖拉机清理好几次。
每一次搬迁折损的成本,耗费的心力,都是一肚子的艰辛。
老丁家门口的墙上有历年来留下的提示,层层叠叠,很像敦煌石窟里一层层被各朝工匠覆盖的壁画。最浅一层依稀可见六个字:“生态避险搬迁”,颜色最深、最清晰处写着五个字:“有安全住房”。
安全住房就是四迁后的昌盛村。
这次昌盛村采用了当下新农村建设的普遍布局,农舍聚居而建,一个个小院横平竖直地分布,有六七十平方米,也有更大点的,但和以前的占地相比,都不算大,于是不少村民选择在小院内再加建房屋。
“造房子的钱政府出一点,我们自己出一点。这旧房子拆了政府还给了10万块钱哩。”老丁絮絮地说。
村口还修了篮球场,村里有文化礼堂,不远处还有警务站和医务所,村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车行驶在村道上,寂静无声,很多人都在上工或是歇晌。门上崭新的“家和万事兴”横批,提示我们这里是有人居住的,他们一直对美好生活充满着向往。
离开昌盛村,往民勤县城赶路,一路上,这样的集聚化村落还有不少,有的房子外墙涂成了鹅黄色,有的保持本白色。坐落在平原上,像一座座小城堡,守护着家人,当灯光亮起时,一定特别好看。
“孟母三迁”和“昌盛村四迁”都有相同的目的:寻找更好的环境。只不过孟母追寻的是求学的环境,昌盛村则面对更严酷的选择——物理意义的生存环境。
在民勤,随处可见那句话:“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杭州人民也跨越山海地为此努力着,让昌盛村不再“五迁”。
15年的努力,“杭州林”有了四期的规模,当年种下的梭梭早已抽枝发芽,茁壮得比一个成年人还高。我们在种下它时,只是小手臂长的几束“枯枝”。
2019年,我们来时,在腾格里沙漠最西端种梭梭;2025年的今天,我们在巴丹吉林沙漠最南缘种梭梭。从“西”到“南”,一片片荒漠已经被“锁定”。当年的湖泊、现在的盐碱地上,志愿者操作着拖拉机凿开了坑,植上了苗,浇上了水。
“00后”志愿者辉哥说,他一个上午能开装着15吨水的水车来回浇上三车半的水。最忙时,一天种下的梭梭需要用十车水来浇灌。小马哥说,最大、也是用得最多的一辆水车上写着“杭州日报”四个字,正是杭州日报的读者、杭州人民捐赠的。
如果你见过一条河流突然消失,河床干涸龟裂;如果你见过眼前水声潺潺,回头沙丘撞入眼帘,你会深深领悟,为何绿洲是沙漠旅者的希望归属。
人类没有能力抵抗时间,但有能力让绿洲慢慢扩大。
在“杭州林”三期所在的四方墩,小马哥站在立着治沙纪念碑的小丘顶,遥指前方:“要从这个墩种到那个墩,还有那一个……”这些遥远的地表隆起,在几千年前,它们或许曾是湖中的小岛。现在,治沙志愿者们发愿,要用10到15年时间,用梭梭将它们串连。
治沙纪念碑上,一排排来自杭州、深圳、北京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名字,接续排列,一个接着一个,一年接着一年。
昌盛村,多好听的一个名字啊,想必命名者一定对其寄予了生命的厚望。如今,我们对四迁后的昌盛村,对这座沙漠中的县城,同样有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沙漠里的逆行者
陶憬瑛(读者代表)
沙漠里行走的人,大多会顺着沙丘的脊线,借风力之便,省些脚力。偏有那些“逆行者”,顶着风,踏着流动的沙,在荒漠深处种下一片绿色的希望。
“漫天黄沙白日昏”——这是杜牧笔下的沙漠;“大漠风尘日色昏”——这是王昌龄笔下的沙漠。一直以来,我只是在诗句里和文章中领略着沙漠的荒凉和恶劣。这次,有幸跟随杭州日报的记者,跨越2600公里,来到民勤防风固沙的“杭州林”种植梭梭,亲身感受到了那份“漫卷黄沙遮白日,掀天揭地大风狂”,以及梭梭种植志愿者们的不易。
从杭州到民勤,一路的风景从绿色葱郁切换到黄沙莽莽,从“桃红柳绿、微风拂面”的江南转场到了“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
与小马哥汇合后,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坐车一路颠簸着向沙漠深处的梭梭林行进。沙漠中无路,我们走的是志愿者们因种植和灌溉需要蹚出的一条凹凸不平的车辙路。沿着这条地图上找不到的路,我们时而上蹿、时而左摇、时而右晃地来到了“杭州林”。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灰绿的矮树丛,绵延数公里,在沙漠中静默着。梭梭树不甚高大,枝干扭曲,树皮皲裂如老人的手背,叶子退化成鳞片状,灰不溜秋的样子,简直可以用丑陋来形容。随行的师傅告诉我,这其貌不扬的树相当地耐旱,根系能扎十几米深,一年就喝几场雨水,就能在别的树活不成的地方活得好好的,一棵梭梭能固定十平方米沙土。闻言,我不禁钦佩这梭梭暗藏的韧劲,小小的身躯不屈不挠地挺立在风沙中,绽放着生命的奇迹。
随后,在小马哥和志愿者的指导下,我种起了梭梭,挖坑、插苗,笨拙的动作诠释了我的不事稼穑,随行的师傅说我再多铲几锹手上要起水泡。此时,荒漠刮着大风,乱舞的头发不时遮挡我的视线,风裹着细沙往鼻孔、衣领里钻。望着那一片梭梭林,想着师傅的经验之谈,想起在来种梭梭之前参观的种植基地中看到的几个大帐篷(一个大帐篷中安置着若干小帐篷,小帐篷里铺着地垫和床垫,这就是志愿者们的“宿舍”),对那些坚持在这里种梭梭的志愿者油然起敬,他们如梭梭般坚韧,在风沙中种下了对绿色的憧憬。
在这次的活动中认识了一位来自甘肃天水的“00后”志愿者温启辉,他年轻的脸庞被风沙吹成了黝黑色,他在朋友圈里说,“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看到发芽的梭梭仿佛凯恩夺冠一样开心”……这位阳光大男孩让我们看到新一代的治沙人在顽强地成长。
一代代逆行者的努力,在践行着绿进沙退、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承诺,这大约就是逆行者的意义吧——在黄沙漫漫处走出绿意。
爱满观成,绿溢大地
吴婕(杭州观成实验学校教师)
每逢春季,“观成人”有一种情怀就像春草,从冬日冰冻的土地上苏醒过来。从2016年起,“西湖无法复制,绿色可以传递”这句话击中了观成师生的心,于是我们开始捐梭梭、写小诗、画海报、献爱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今年恰逢我们向这片风沙之地捐赠梭梭的第十个春秋,学校开展了以“爱满观成·绿溢大地”为主题的十周年庆典暨微光手账LOGO发布仪式。我也有幸随杭州日报踏上这片被风沙雕刻的土地,在黄沙与绿意的交响中,触摸一个关于坚守与重生的故事,赴一场十年之约。
初至民勤,我们一路颠簸前行,车窗外闪过的是一排排倔强的身影——沙枣树虬曲的枝干刺向苍穹,新疆杨高耸的躯干在风中铮铮作响,恍若戍边将士将千年风沙挡在县城之外。
抵达那夜,对面坐着春种归来的志愿者,烤架上的油脂滴落进火堆,溅起满天星子。有单车骑士从天水跋涉而来,面庞黝黑,笑称自己从“天水白娃娃”成了“民勤黑娃娃”;更有摩托骑手褪去手套,掌心纹路里嵌着洗不净的沙砾。在席间我们听着陌生朋友不同的故事,感受着他们对这片土地同样的热爱。
通往四方墩生态基地的沙土路像条蜿蜒的伤疤,司机师傅猛踩油门,扬起的沙尘扑在车窗上沙沙作响,小马哥向我们介绍:“这条路地图上没有,是我们开拓出来的!”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有一方石碑在风中巍然矗立,“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朱红大字直刺云天。俯身细看,碑阴镌刻的援助名录里,“杭州观成实验学校”的字样映入眼帘,那一刻,十年间跨越千山万水的绿意,忽然有了具体的形状。
在观成中学林,最大那株梭梭已亭亭如盖。十载光阴,近千亩荒漠化作绿洲,当用手指触到它龟裂的树皮时,感受到的是大地深处汩汩流淌的生机。小马哥说:“你走进去感受梭梭的力量。”越往里走,我越感受到肆虐的风沙变得轻柔,梭梭正在保护着这片土地。
往返途中,我们有幸坐上了去年刚开通的武威东至中川机场的列车,在一年前奔赴此地的志愿者们还需要坐很久的大巴车前往武威和民勤。望着窗外的新绿,我内心坚定:西部高铁的建成意味着这片土地会越来越好!愿民勤的春天不再是只是梭梭的春天,当高铁穿云,当绿洲蔓延,这片土地终将如梭梭般,在岁月风沙里站成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