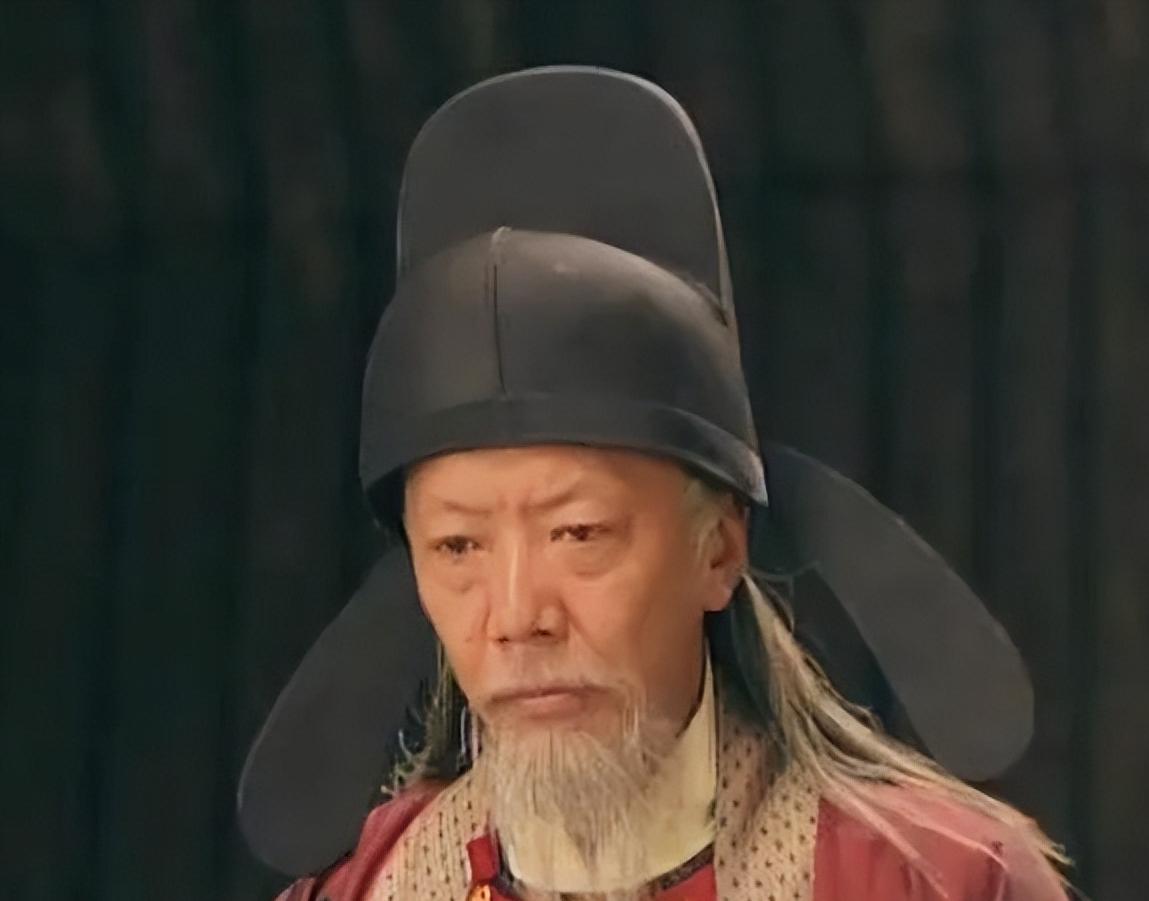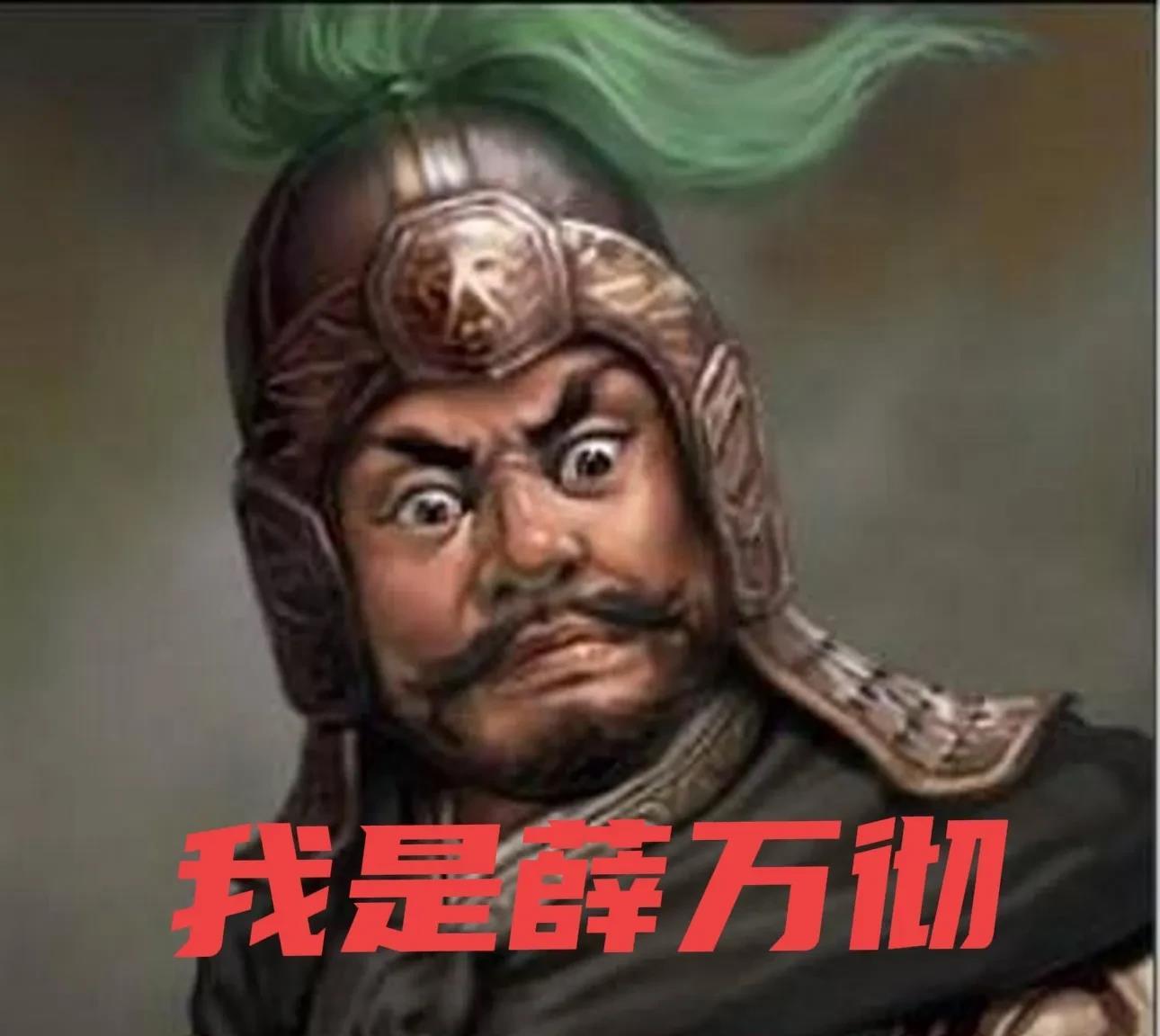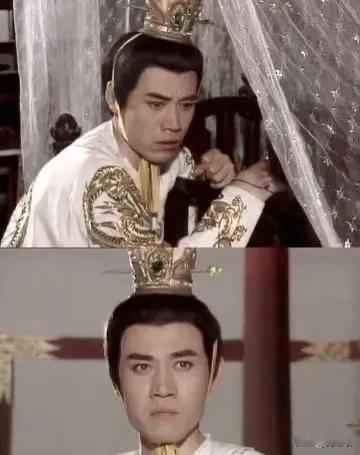612年,大隋帝国百万大军,倾巢出动,跨海东征,目标只有一个——高句丽。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杨广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兵一个难以征服的对手?民间骂他昏君,史书评他暴政,可崇祯却看出了他的另一面。这位隋炀帝,或许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死在时代前头的天才。
杨广不是庸主。他继位之初,励精图治,文武并举,大兴水利,完善科举,整肃吏治,手段一点都不软。他清楚,父亲打下的江山不稳,南北刚统一不久,四夷还不服,边境问题迟早爆雷。
最让他坐卧不安的,就是东北方向的高句丽。
这个老对手,从汉朝打到隋朝,始终桀骜不驯。隋朝刚建时,它就借口内乱出兵骚扰辽东,烧村杀人,明里试探,暗里渗透。朝廷屡次发文安抚,对方却当耳旁风。
杨广看得清楚,这不是边境摩擦,而是地缘战略死结。如果任由高句丽坐大,整个辽东防线迟早塌陷。一旦东北门户被破,草原部族会蜂拥南下,那时整个华北就不保。
崇祯在明朝末年也面对类似处境。辽东失守,女真崛起,最终清军入关,江山改姓。或许正是这种相似命运,让崇祯对杨广多了几分理解。他知道,防守永远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主动出击,提前破局。
杨广就是要赌这一把。赌赢了,天下太平;赌输了,国运断头。
612年,杨广第一次出兵高句丽。他亲自调度,动员全国兵马,集结百万人马,水陆并进,气势逼人。整个东征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可是战局从一开始就跑偏了。
几十万水师在渤海沉船,陆军长驱直入,被高句丽设伏于山川险隘。大将宇文述率领主力攻城未果,惨败撤军,几乎全军覆没。回朝时,尸横遍野,饿殍遍地,兵士连马蹄都啃了下去。
613年,杨广不信邪。他再次起兵,这次带着报复的怒火。刚到战场,国内突发杨玄感叛乱,后方炸锅。他不得不撤军,兵马未动,民心已散。
614年,第三次东征,他不再恋战,只围而不攻,等高句丽投降纳贡后便草草收兵。
三次出征,前后不过三年,却将隋朝百姓拖入深渊。赋税加重,劳役不断,饥荒、叛乱、动荡接踵而至。
可杨广真的错了吗?
他只想解决一个定时炸弹,只想一劳永逸。他没想到,对手韧性太强,地形太险,国内太弱。他高估了胜利的可能,也低估了民意的反噬。
传统印象里的杨广,是个铺张浪费、沉迷声色的昏君。可如果只看他留下的基础设施,会发现他是极其务实的人。
他修大运河,联通南北,打通漕运命脉;他设东都洛阳,稳定中原权力中心;他推科举取士,打破世家门阀垄断。
所有这些,不像是昏庸无能者的胡作非为,反而像是雄才大略者的系统构建。
征高句丽,也是他治理思路的一部分。他想把边疆问题彻底解决,把隋朝的势力延伸到朝鲜半岛,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亚核心”。只是这个“先见之明”,在当时的国家承载力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他太急了,太重视结果,太轻视代价。
百姓不理解,官员不支持,军队不堪重负。于是,这场“战略突围”,成了耗尽国本的灾难。
崇祯说过一句话:“天下大势,非一人之功所能转。”他理解杨广,也看到了这位“千古名君”的悲剧。
618年,隋朝灭亡。杨广在江都被部将所弑,一代帝王落幕。
史书大笔一挥,称他“暴君”、“亡国之主”。他的政绩被掩盖,功劳被抹去,留下的只有“好战、淫逸、残暴”的刻板标签。
可历史从不只是黑白分明。
唐太宗李世民接替隋制,继承运河、科举、行政架构,一步步走向盛世。而这些基础,正是杨广拼命推行的。他看得远,却没走得稳。他想做“千年帝国”的奠基人,却成了“速朽王朝”的葬送者。
而高句丽呢?并没有因为躲过隋军而长治久安。几十年后,被唐与新罗联合击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高句丽不是打不垮,只是隋炀帝选错了时机。
历史对杨广不公,对隋朝苛刻。但如果我们抛开成见,从制度、战略、地缘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位帝王,就会发现,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皇帝”。
他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者,一个“愿赌服输”的战略家。
只可惜,他赌的是国运,输的是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