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后不久,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深夜,上海弄堂里,苏青的笔尖在纸上颤抖,字里行间是她十年的屈辱与觉醒。1934年的上海,租界里的灯红酒绿与弄堂的柴米油盐形成鲜明对比。苏青的新婚之家在法租界一角,窄小的弄堂房子里,摆着她从娘家带来的几本旧书。
那时的她,20岁,满心以为嫁给李钦后是幸福的起点。婚礼上,她穿着旗袍,脸上带着羞涩的笑,亲戚们夸她“知书达理”,婆婆却在席间嘀咕:“希望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第二天,喜悦尚未消散,她推开卧室门,却看见丈夫李钦后与表嫂并肩坐在床边,表嫂的手轻轻搭在他的臂上,低声笑道:“我还以为你娶了媳妇就忘了姐姐呢。”李钦后斜了她一眼,语气轻佻:“娶她不过是给家里个交代,你才是我的心头好。”
苏青僵在门口,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她想冲上去质问,却被婆婆的咳嗽声打断,只好默默退回厨房,眼泪混着洗菜的水流下。 那个年代,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丑闻。苏青的母亲曾告诫她:“女人嫁了人,就得守本分,忍字当头。”她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只要贤惠懂事,丈夫总会回心转意。
她开始埋头家务,烧饭、缝衣、伺候公婆,连喘口气的空闲都没有。接连几年,她生下四个女儿,婆婆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每次她抱着孩子,公婆的目光总是掠过她,直勾勾地盯着襁褓,叹气道:“又是个赔钱货。” 李钦后在外花天酒地,回家却对苏青百般挑剔。
一次,她因产后虚弱,脸色苍白,李钦后与表嫂当着她的面嘲笑:“瞧你这副病怏怏的样子,哪还有点女人味?”苏青低头不语,手指攥紧了衣角,指甲几乎掐进肉里。家里的经济也每况愈下,李钦后挥霍无度,常常一掷千金请客,却连孩子的奶粉钱都不愿出。
1941年,第五个孩子出生,是个儿子。婆婆终于露出一丝笑意,但那笑意只给了孩子。苏青拖着刚生产完的身体,忙着洗尿布、熬粥,婆婆却冷冷地说:“儿子总算有了,你可别拖后腿。”那年冬天,家里米缸见底,孩子饿得哇哇大哭。苏青鼓起勇气,低声向丈夫开口:“能不能给点钱买米?”李钦后醉醺醺地抬起头,斜眼看她,忽地一巴掌甩过来:“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脸上的刺痛让苏青踉跄一步,她捂着脸,泪水在眼眶打转,却硬生生咽了回去。
这一巴掌,像一记惊雷,炸醒了沉睡的她。从那天起,苏青开始偷偷写作。深夜,孩子们睡下后,她点亮油灯,在桌子上铺开纸张。她的笔下,是婚姻的苦涩,是婆家的冷眼,是丈夫的背叛。她回忆起少女时代,父亲留下的书堆里,她曾读过《红楼梦》,贾宝玉的痴情让她向往爱情,可现实却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她的幻想。
她的第一篇作品《产女》在《论语》杂志发表,读者来信称赞她的文字“像刀子般锋利,割开生活的真相”。 写作成了她的救赎。1943年,她将十年婚姻的辛酸写成《结婚十年》,书一出版便席卷上海。书店门口排起长队,读者争相传阅,有女人读完后泪流满面,写信说:“苏青,你写出了我的心声。”张爱玲在私下评价:“她的文字,像一个人坐在你对面,娓娓诉说,却字字刺心。”
但写作带来的光芒并未照亮她的生活。李钦后对她的成功嫉恨交加,公开指责她“抛头露面丢人现眼”,甚至污蔑她与编辑有染,当众对她拳脚相向。苏青终于下定决心,带着五个孩子离开李家。离婚后,李钦后拒绝支付抚养费,她只能靠稿费和编辑工作养家。
上海的冬天,租来的小屋四处漏风,她一边咳嗽一边改稿,孩子们挤在一张床上取暖。
1944年,《结婚十年》再版第20次,苏青的名字传遍上海滩。她受邀参加文人聚会,穿着朴素的布衣,站在一众西装革履的男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有人问她:“苏女士,写书这么赚钱,为何还过得这么清苦?”她笑而不答,低头抿了一口茶。
那一刻,她想起离婚那天,收拾行李时,婆婆冷冷地说:“带着这么多孩子,你走得出这门,可走不到明天。”她也想起李钦后最后一次打她时,邻居的窃窃私语:“这女人疯了吧,敢跟男人对着干?” 她挺直了背,目光穿过人群,望向窗外的黄浦江。江水滔滔,像是她的心,翻涌着不甘与希望。
苏青的笔从未停下。她用文字为无数女性发声,揭开婚姻的伪装,撕碎父权社会的遮羞布。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人的抗争史,更是1940年代中国女性觉醒的缩影。晚年,她住在上海一间逼仄的小屋,身边只有小女儿相伴。1982年,她在病痛中去世,但她的文字,依然在读者心中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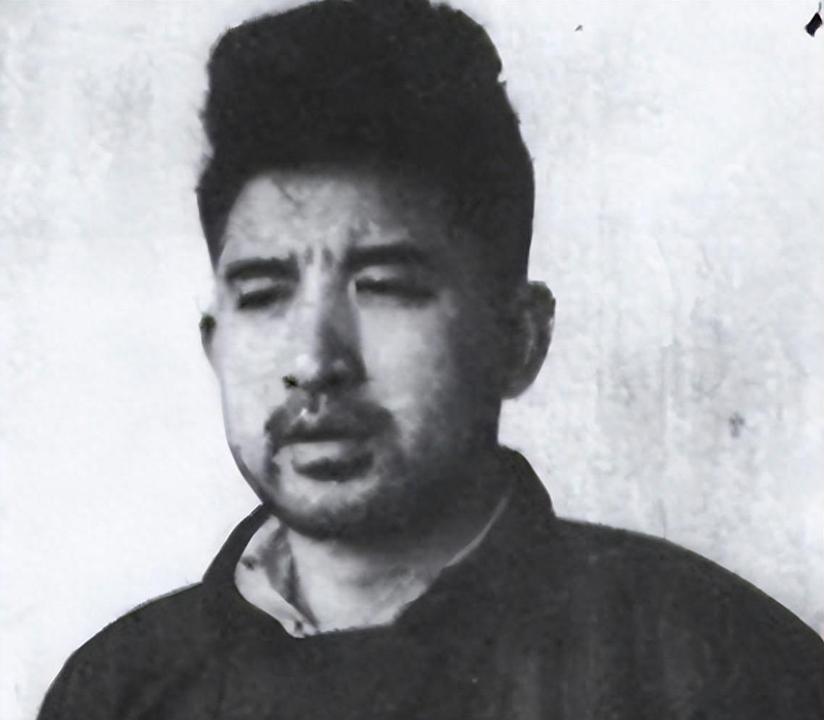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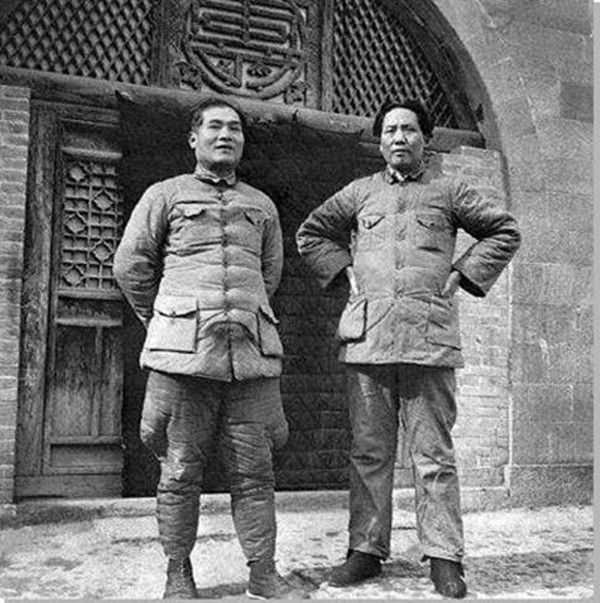


用户10xxx67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