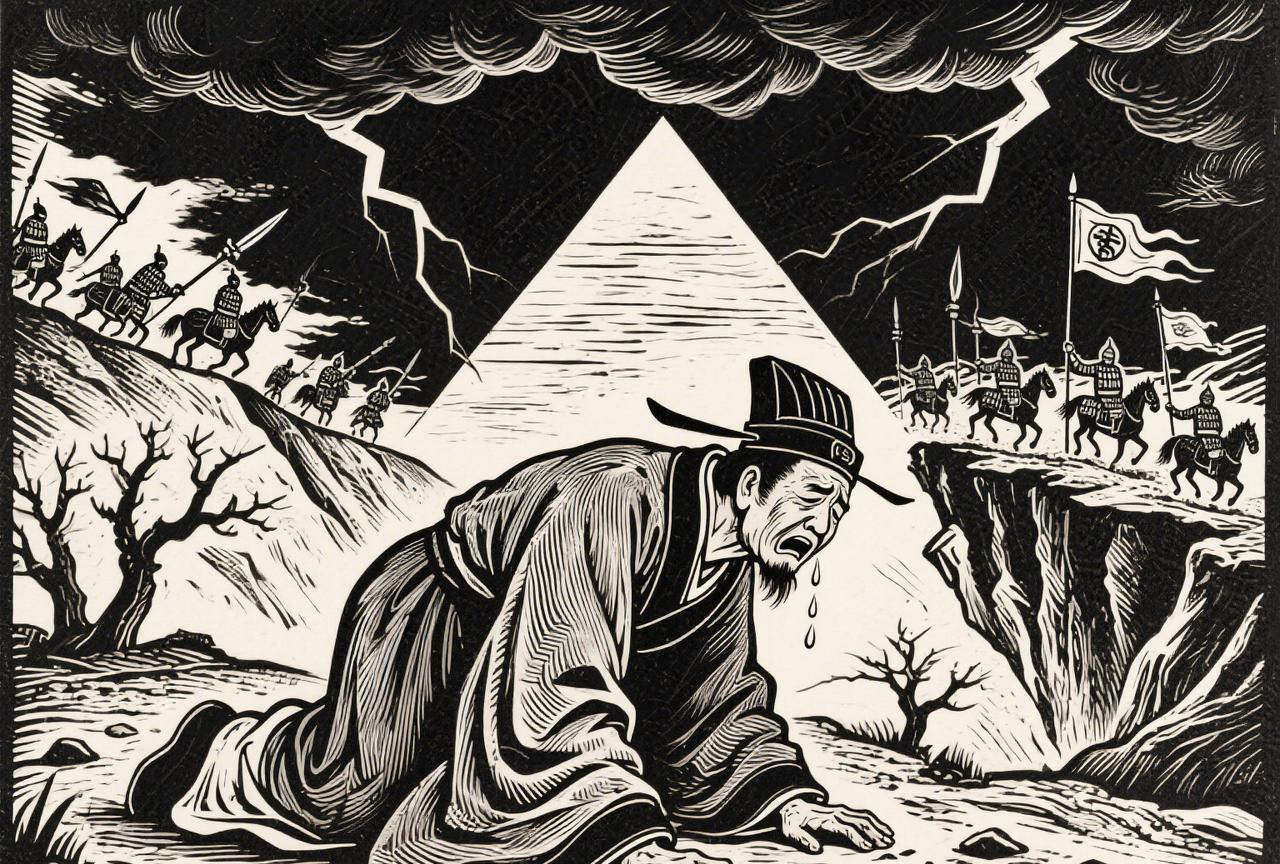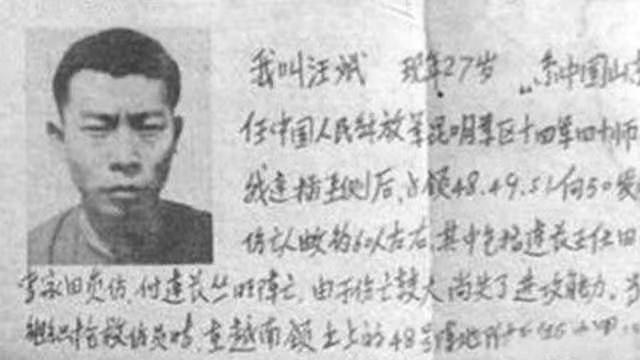1951年,2个漂亮的女战士,在进藏之前拍下的合影。她们头戴棉帽,身上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肩上挎着背包和水壶,看起来年龄并不大。 左边的姑娘叫李桂芳,陕西米脂人,家里是种枣树的。1949年家乡解放那天,她跟着秧歌队扭到半夜,回来就跟爹说要去参军。爹抽着旱烟袋叹口气:“女娃娃家,不在家学针线,跑那么远干啥?” 她把辫子往身后一甩:“解放军救了咱,现在国家要进藏,我得去搭把手。”临走时,娘把攒了半年的鸡蛋煮成咸蛋,塞进她背包,说:“到了那边,别省着吃,身子是本钱。” 右边的是四川妹子王秀兰,比李桂芳小一岁,原是县城药铺的学徒。她能背出《本草纲目》里大半的药材特性,部队招卫生员时,她揣着师傅给的《高原草药图谱》就报了名。 出发前在甘孜集结,她总被战友们笑“背着药箱比背包还沉”,她就把药箱往肩上紧了紧:“这药能救急,沉点怕啥?” 拍合影那天,是她们第一次见到汽车。之前部队都是靠马驮人扛,听说有几辆卡车要送物资,俩姑娘特意跑到车跟前,摸着铁皮车厢直乐。 李桂芳数着车斗里的帐篷,王秀兰盯着捆成摞的青稞粉,谁也没提路上可能遇到的塌方和暴雪。有老兵跟她们说,进藏要翻过十二座雪山,有的地方氧气薄,走快了能憋得眼冒金星。李桂芳拍着王秀兰的胳膊:“咱慢慢走,总能到。” 真正上路才知道,“慢慢走”都是奢望。卡车在乱石滩抛锚那天,她们跟着队伍徒步,王秀兰的布鞋很快磨破了底,李桂芳就把自己的鞋垫脱给她——那是娘纳的千层底,针脚密得能数清。 夜里宿在山洞,雪粒子从洞顶往下掉,王秀兰冻得睡不着,就给李桂芳讲药铺的事:“以前有藏民来抓药,说高原上的雪莲能治百病,等咱到了拉萨,说不定能采着。”李桂芳裹紧大衣笑:“采着了先给你治治这怕冻的毛病。” 她们的背包里,除了药品和干粮,还有本藏语小册子。每天歇脚时,就对着册子一个词一个词地念,“你好”“谢谢”“哪里不舒服”,念得舌头打结。 有次遇到赶着牦牛的藏民,王秀兰试着说“扎西德勒”,对方愣了愣,突然递过来一块酥油,李桂芳赶紧把自己的咸蛋塞过去,俩人手忙脚乱地交换,笑得比合影时还开心。 走了快两个月,李桂芳的脸被晒得脱了层皮,王秀兰的药箱轻了大半——大部分药材都给了生病的战友。 过唐古拉山那天,有人高原反应晕了过去,王秀兰跪在雪地里给人做人工呼吸,李桂芳在旁边烧雪化水,手冻得像红萝卜,却死死攥着烧火的树枝。等 那人缓过来,王秀兰瘫坐在雪地上,突然想起拍合影时的自己,那时总觉得进藏是件新鲜事,现在才懂,新鲜背后全是咬牙硬撑。 后来有人问她们,后悔吗?李桂芳指着路边新栽的树苗:“你看这树,现在看着细,等明年说不定就发芽了。”王秀兰则翻开那本快翻烂的药谱,上面多了好多新记的字,都是藏民告诉她的高原草药。 照片里的笑容是真的,后来路上的苦也是真的。那些像她们一样的女战士,有的成了接生婆,在帐篷里接生下第一个藏族婴儿;有的成了教员,教孩子们写“中国”两个字。 她们或许没意识到进藏意味着什么,但脚步从未停过——就像高原上的河,不管冰有多厚,总能找到流淌的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