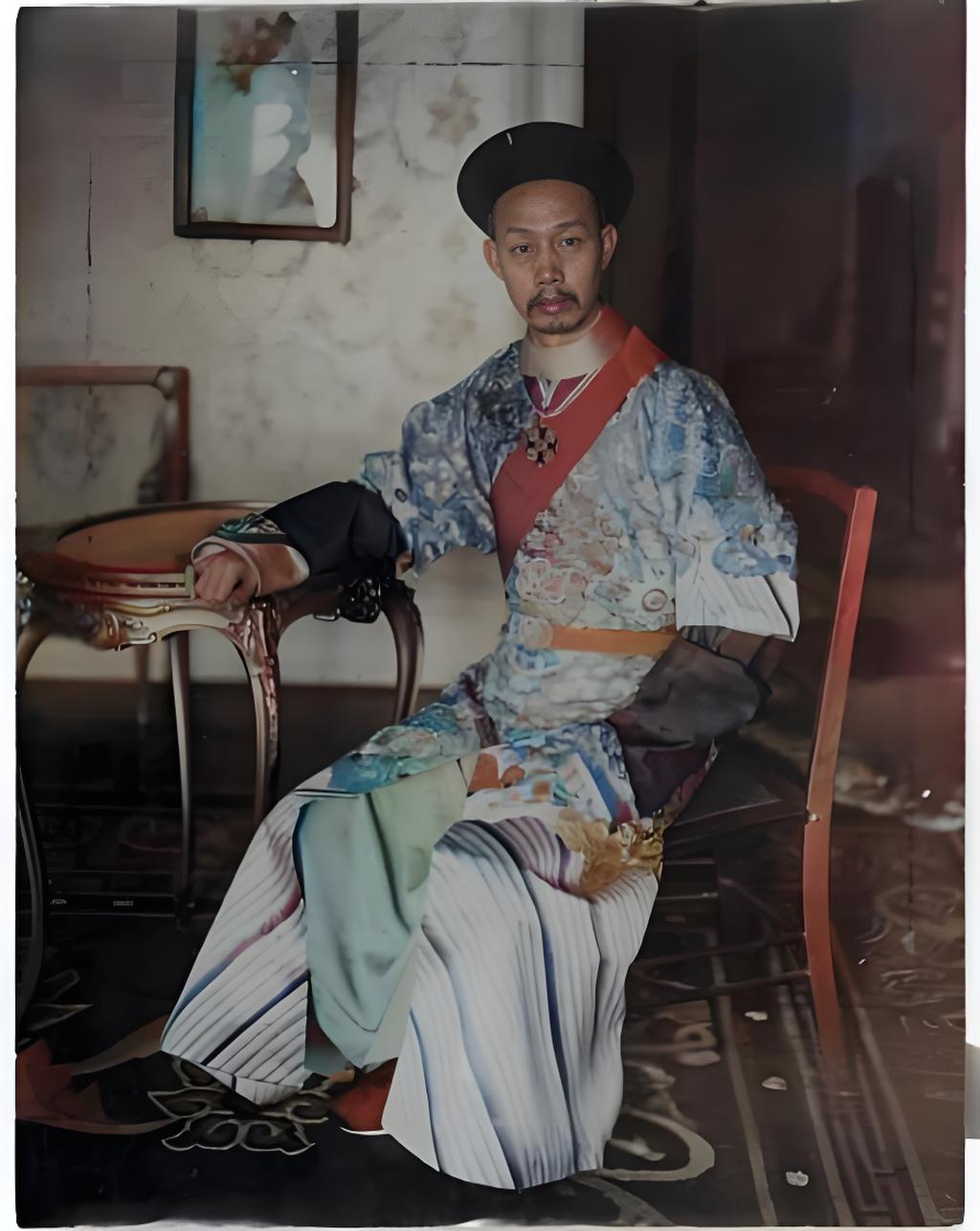1910 年 3 月 31 日晚上,在昏黄的灯下,陈璧君跟汪精卫说:我要将自己献给你。汪精卫吓得跳起,立即背过身:你快把衣服穿上,我对陈小姐只有敬重。 油灯的光晕在汪精卫的长衫上晃,像他此刻乱了节奏的呼吸。案上摊着的刺杀计划还压着半截铅笔,摄政王载沣的出行路线被红笔圈了又圈,墨迹透了纸背。 陈璧君的哭声细得像丝线,缠在他耳后 —— 这姑娘刚变卖了母亲的金镯,换了二十斤炸药,此刻玉体上还沾着筹备时蹭的火药灰,在灯下泛着冷光。 三年前东京的同盟会会场,陈璧君第一次见汪精卫。他站在台上念《民报》社论,声音清润如竹,"驱除鞑虏" 四个字被他念得掷地有声。 她攥着刚加入同盟会的申请表,指尖把 "陈璧君" 三个字描得发毛。 回去后,她把每期《民报》上汪精卫的文章剪下来,贴成厚厚的册子,扉页写 "为君赴汤蹈火",字是富家小姐特有的圆润,却透着股狠劲。 刺杀队的窝棚在北平城根,霉味混着汗臭。陈璧君把炸药包捆在汪精卫腰间时,手指故意碰了碰他的肋骨。 她听说他是广州秀才,身子骨文弱,却总在练刺杀动作时把自己磕得青一块紫一块。 "这炸药我试过,三斤就能掀翻马车。" 她笑着说,眼角的痣颤了颤,像颗没点牢的朱砂。 汪精卫没接话,只盯着她新做的布鞋,鞋面上绣的牡丹被炸药包磨得脱了线。 狱卒把鸡蛋篮子递进来时,铁栏杆撞得陈璧君手疼。1910 年的春天,北平还飘着雪,她裹着偷来的男装,把鸡蛋一个个往棉絮里塞 —— 每个蛋上都用指甲刻了个 "汪" 字,怕被狱卒搜走。 汪精卫在牢里收到时,蛋已经凉透了,他摸着蛋壳上的刻痕,突然想起那晚灯下她裸露的肩头,也是这样带着倔强的温度。 后来他在《狱中杂感》里写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笔锋间藏着的温柔,连自己都没察觉。 庭审那天,汪精卫的辫子被狱卒拽得生疼,他却扬着头念革命宣言。 法官的惊堂木拍得震天响,他忽然瞥见旁听席上的陈璧君,她穿了身素衣,左鬓别着朵白菊,像来送葬,眼神却亮得像要烧起来。 后来他才知道,这姑娘为了混进法庭,给狱卒塞了自己最后一支金钗,钗头的珍珠摔在地上,碎成了八瓣。 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北平狱时,汪精卫正用陈璧君送的钢笔写家书。笔尖漏墨,在 "勿念" 二字上晕开个黑团。 牢门打开那天,陈璧君扑上来抱住他,他闻到她身上的硝烟味 —— 这姑娘竟自己组织了支敢死队,在天津炸了清廷的粮库。 "我说过会等你。" 她笑出泪来,眼泪滴在他的囚服上,晕开的水渍像朵极淡的花。 1944 年的南京梅花山,汪精卫的墓碑被炸药掀翻时,碎块里混着块没烧尽的绸布。 那是陈璧君当年给他缝在炸药包上的衬里,上面绣的 "革命" 二字,早被岁月泡得发灰。 远处的清凉山火葬场,烟柱直冲云霄,像极了 1910 年那晚,他背过身时,油灯投在墙上的影子 —— 瘦长,倔强,却终究没能抵过后来的风。 陈璧君在苏州监狱里收到消息时,正用碎碗片在墙上刻字。她刻的还是 "为君赴汤蹈火"。 只是笔画抖得厉害,刻到 "君" 字时,碗片划破了手指,血珠滴在砖缝里,像极了当年鸡蛋上的刻痕。 有狱卒说她疯了,整天对着墙笑,却没人知道,她笑的是 1910 年那个春夜,那个背过身说 "只有敬重" 的青年,那时他眼里的光,比后来任何勋章都亮。 东京的旧书摊上,偶尔还能见到泛黄的《民报》。有一期的角落,有个模糊的指印,像是有人反复摩挲过 "汪精卫" 三个字。 买下报纸的学生不会知道,这指印或许来自一个富家小姐,她曾为这三个字,褪去过衣衫,扛过炸药,最后在监狱的墙前,刻完了一生的执念。 而那个曾让她仰望的青年,终究在历史的天平上,从 "革命者" 的一端,滑向了另一端,只留下那晚昏黄的灯光,还在时光里,照着他背过身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