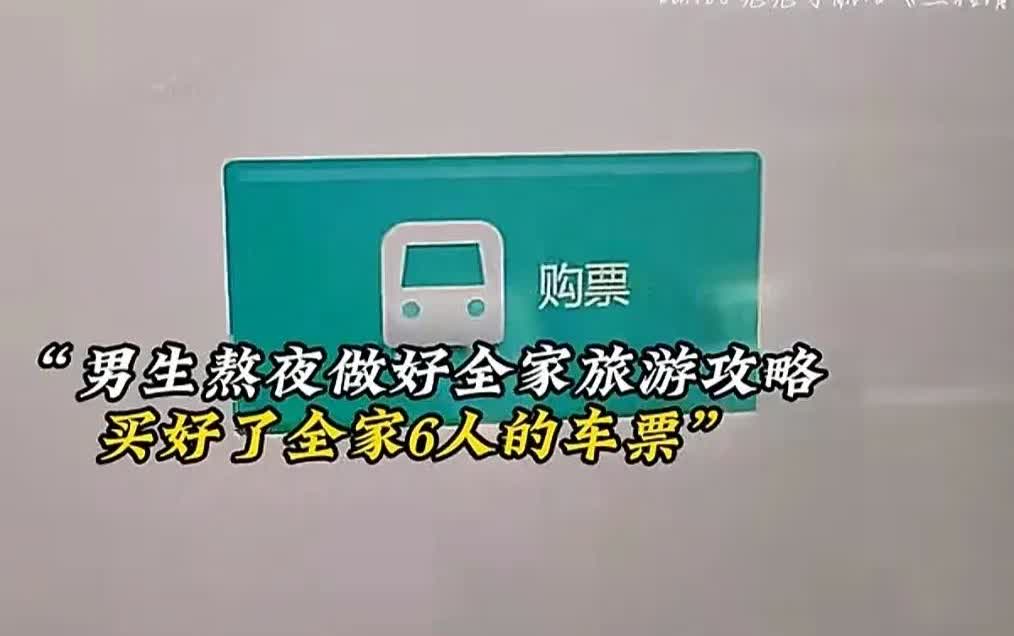县令的妻子死了,他叫来一些女工缝制丧服,女工中有个妇人,容貌温婉秀丽,姿色绝伦,县令很是喜欢,就把她留了下来。 那妇人姓苏,丈夫早逝,带着个三岁的儿子在乡下讨生活。县里贴出告示招缝补女工,她想着能挣几个铜钱给孩子买药,才揣着针线篓子进了县衙 苏妇人留在县衙西厢房的偏院,白日里跟着其他女工缝丧服,指尖翻飞时总带着股子稳当劲儿。丝线在她手里像有了灵性,针脚密得能数清根数,连最挑剔的老嬷嬷都忍不住夸:“苏娘子这手艺,怕是宫里出来的也未必及得上。 偏院的月光总带着股子冷意。 苏妇人把缝好的孝布叠得方方正正,手指划过布面,能摸到自己扎出的细小血点。同屋的张嫂凑过来,压低声音:“县太爷今儿又在窗根底下站了半晌,眼睛直勾勾盯着你手里的针呢。” 她捏着针线的手顿了顿,线头在指间绕了三圈才系紧,“咱是来挣钱的,别的不用管。” 话是这么说,第二天送饭的杂役就多给了她一碗肉羹。 油花浮在汤面上,晃得人眼晕。苏妇人把肉羹分给旁边咳嗽的小丫头,自己扒着糙米饭,脑子里全是乡下儿子的脸。小三儿昨天托人带信,说又开始发热,郎中开的药还在灶台上晾着,她得赶在雨前把钱凑齐。 县令来偏院的次数越来越勤。 有时是借着看丧服进度,站在她身后半天不动,呼吸扫过她颈窝;有时是扔给她一块上好的绸缎,说“给你自己做件衣裳”。苏妇人每次都把绸缎原封不动退回去,只说“不敢僭越”。 她见过前院的李管家怎么打量自己,那眼神像打量牲口,掂量着肥瘦好坏。也听过其他女工嚼舌根,说县太爷的原配夫人就是生不下孩子,被磋磨得没了气。 这天傍晚,县令屏退众人,单独留下她。 西厢房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着他鬓角的油光。“你儿子的病,我让人去瞧了。”县令慢悠悠地转着手里的玉佩,“城里最好的大夫,药材管够。” 苏妇人猛地抬头,眼里的光亮得吓人,又瞬间暗下去,“民妇不敢劳烦大人。”她屈膝要跪,被县令一把拽住手腕。 他的手指粗粝,带着官场应酬的酒气,捏得她骨头生疼。 “你那点工钱,够买几副药?”县令笑得暧昧,“跟着我,别说治病,以后让你儿子进学堂,考功名,都不是难事。” 苏妇人看着他身后墙上挂着的亡妻牌位,黑漆描金的字在灯影里泛着冷光。她突然想起丈夫临死前攥着她的手说:“咱穷点没关系,脊梁骨得挺直。” “大人的好意,民妇心领了。”她用力抽回手,指尖在袖口蹭了又蹭,“丧服明日就能完工,工钱结了,我就回乡下。” 县令的脸沉下来,像要落雨的天,“你以为你走得掉?” 夜里,苏妇人把攒下的铜钱用布包好,塞在鞋底。 窗外的虫鸣聒噪得很,她摸着针线篓里那把小剪刀,是丈夫生前给她磨的,刀刃锋利得能剪断头发。她想,实在不行,就用这剪刀划破脸,总好过被拖进那不见天日的后院。 第二天一早,她抱着叠好的丧服去前院。 刚走到月亮门,就见李管家领着个陌生妇人往偏院去,那妇人怀里抱着个孩子,眉眼竟有几分像县令。苏妇人心里咯噔一下,听见李管家谄媚地说:“这是王乡绅家的二姑娘,刚没了丈夫,跟大人正好相配。” 县令正陪着那妇人说话,看见苏妇人,只是淡淡扫了一眼,挥手让她把丧服放下。 苏妇人放下东西,转身就走,脚步快得像后面有狼追。走到县衙门口,她摸了摸鞋底的铜钱,硬邦邦硌着脚,却让她心里踏实。 出城的路上,遇见赶车去乡下的郎中。 “苏娘子,你儿子的烧退了!”郎中隔着车喊,“是个过路的老大夫给瞧的,分文没收,说瞧着孩子可怜。” 苏妇人站在路边,看着远处的炊烟,突然蹲下身,捂住脸哭了。眼泪砸在地上,混着尘土,像极了她这些年咽下的苦。 后来有人说,县令最终娶了王乡绅的女儿,很快添了个大胖小子。 也有人说,苏妇人回乡下后,凭着一手好针线,攒钱开了个小绣坊,供儿子读了书。那孩子后来真的考中功名,回来给母亲立了块碑,碑上没刻多少字,只说“母贤,守节,育子成人”。 信息来源:据宋代《太平广记》《夷坚志》等笔记小说记载,古代基层官吏与平民女性的互动常涉及权力不对等下的生存博弈,文中情节虽为虚构,但折射出传统社会中底层女性在生计压力与人格尊严间的艰难抉择,类似记载在明清话本中亦多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