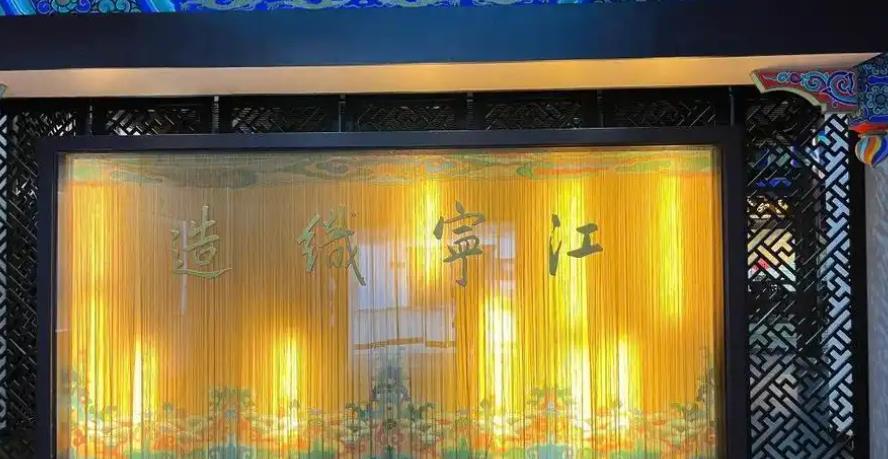1735年,雍正突然去世,享年58岁。25岁的乾隆听到圣旨,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没有人能阻止他。没想到,他即位三天后所做的一切,都打在了父亲雍正的脸上。 雍正皇帝生于1678年,是康熙的第四子,早年叫胤禛。从小在宫里长大,他亲眼见过兄弟们为争位斗得你死我活。康熙晚年,诸子争储闹得鸡飞狗跳,胤禛从中学会了低调和算计。1709年,他被封为雍亲王,负责军需事务,那时候清军在外打仗,他管后勤,经常检查物资,确保供应不出差错。 乾清宫的烛火燃了一夜,乾隆的哭声从沙哑到低沉,最后只剩下抽噎。 他跪在雍正的梓宫前,青布孝服被眼泪浸得发沉。旁边的张廷玉看着这光景,心里直打鼓——这孩子,是真伤心,还是在演给天下人看?毕竟谁都知道,雍正对儿子严厉得近乎苛刻,南巡时带他在身边,犯错了能罚他跪在船头,当着百官的面训斥。 第三天头上,乾隆擦干眼泪,走进了养心殿。 他坐在雍正生前常坐的紫檀木御座上,手指划过冰凉的扶手,那里还留着父亲攥过的痕迹。“传旨。”他的声音还有点哑,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释放允禵、允䄉等宗室,恢复爵位。” 太监们手里的茶盏差点没端住。 允禵是康熙的第十四子,雍正的亲弟弟,当年争储最凶,被雍正圈禁了十年,关在景山的马厩里,据说头发都熬白了。这道旨意,等于直接否定了雍正当年的铁腕——那可是雍正最恨的“政敌”。 紧接着,第二道旨下来了。 “凡是因欠税被抄家的官员,家产退还一半,让他们能养家糊口。”乾隆看着奏折上密密麻麻的名字,笔尖在“江南盐商”几个字上顿了顿。这些人,多是被雍正的“摊丁入亩”“耗羡归公”逼得走投无路的,父亲说他们“盘剥百姓”,可在他看来,弓弦绷得太紧,是会断的。 朝堂上炸开了锅。 老臣鄂尔泰急得胡子直抖,在殿外拦住乾隆:“陛下!先帝定下的规矩,怎能说改就改?那些人都是奸猾之徒,放出来是要惹祸的!” 乾隆停下脚步,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影子拉得很长。“鄂大人,”他语气平静,“父皇在位十三年,铁腕整肃吏治,是怕人心散了。可如今,该松松弦了。”他想起小时候偷听到的话,雍正深夜在书房叹气,说“朕做恶人,让后人做善人吧”,那时不懂,现在突然就懂了。 被释放的允禵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出马厩。 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看见来接他的侍卫,竟一时分不清是梦是醒。有人说这是新帝仁慈,也有人说乾隆是在打雍正的脸——当年雍正为了坐稳皇位,把兄弟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如今儿子全给翻了过来。 更让人咋舌的是对待曾静的态度。 曾静是个秀才,当年写信劝岳钟琪反清,被雍正抓住后,没杀他,反而让他游街宣讲“悔过书”,还编了本《大义觉迷录》,逼着全国学子背诵。乾隆上台没几天,就把曾静凌迟处死,书也全给烧了。“父皇想让天下人懂他的苦心,”他对张廷玉说,“可人心哪是靠逼就能懂的?倒不如让这事烂在土里。” 民间渐渐有了传言,说乾隆比雍正宽厚多了。 茶馆里的说书人开始讲“新帝仁政”,把当年雍正的严苛说成“磨砺”,把乾隆的调整说成“拨乱反正”。有个老秀才喝着茶叹:“雍正爷像把刀,砍得天下人不敢喘;乾隆爷像块棉,让人能松口气了。” 其实乾隆心里有本账。 他知道父亲的好,那些改革让国库充盈,吏治清明,只是手段太硬,得罪了太多人。他站在父亲的肩膀上,要做的不是推翻,是修补——用“宽”来平衡“严”,让天下人觉得,爱新觉罗家既有雷霆手段,也有菩萨心肠。 那天他去给母亲请安,太后摸着他的脸说:“你父皇要是看见,该高兴的。” 乾隆没说话,只是给母亲剥了个橘子。橘子是江南进贡的,蜜甜,不像雍正生前总吃的酸橙。他想起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守住这江山,比争江山难”,那时父亲的手凉得像冰,现在他才明白,所谓“打在脸上”,或许正是父亲想看到的——一个不必再做“恶人”的儿子,才能坐稳这江山。 信息来源:据《清史稿·高宗本纪》《清世宗实录》《乾隆起居注》等记载,乾隆即位初期确有释放宗室、宽免欠税等政策调整,与雍正时期的严苛风格形成对比。相关举措既体现了权力交接中的策略性平衡,也反映了康雍乾三朝统治风格的延续与演变,是清代中期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