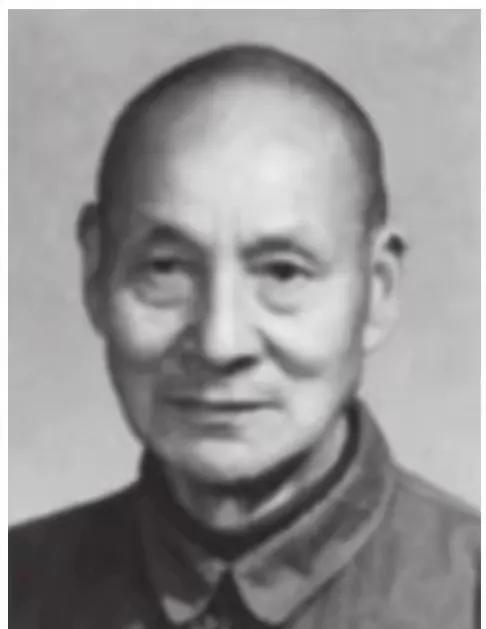新疆起义前,青马军长马呈祥带着数千两黄金逃离,张治中去电挽留,马呈祥说:“我手上有血债,不会被原谅的,电报上都是骗人的话,就像哄着给野马套笼头一样,套上的话,就身不由己了。”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的秋天,迪化城外的戈壁滩上卷起一阵阵黄沙,马呈祥的吉普车里塞满了沉甸甸的木箱,车轮碾过碎石发出的声响像极了命运齿轮转动的咔嗒声。
这个青海马家军的少壮派将领,此刻正攥着张治中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汗水浸透了纸张,"既往不咎"四个字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他忽然想起三年前在西宁马步芳公馆的夜晚,舅舅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们马家的男人,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
可如今兰州城破的消息传来,马家军的老巢已被端掉,他这支孤悬新疆的骑五军,就像戈壁滩上的胡杨树,再倔强也挡不住时代的风暴。
马呈祥的皮靴底下还沾着昆仑山的雪泥,腰间的佩刀是马步芳亲手所赠,刀鞘上"忠勇"二字早已磨得发亮。
这个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西北汉子,骨子里流着马家军的血,也背着河西走廊的血债。
当年红军西路军的女战士被绑在马后拖行的惨叫声,至今还会在午夜梦回时让他惊坐而起。
陶峙岳劝他起义时说得诚恳:"共产党讲宽大政策,傅作义在北平不是过得挺好?"
可马呈祥摸着办公桌抽屉里的黄金清单,八千两黄澄澄的金子映得他眼底发烫,这些从新疆各族百姓身上刮来的民脂民膏,既是保命符,也是催命咒。
出逃前夜的密谋像场荒诞剧,叶成捧着胡宗南的密电说要南撤,罗恕人蹲在地上数银元,马呈祥却盯着墙上的西域地图发呆。
他想起半个月前在喀什噶尔见过的那个维吾尔族老汉,老人用生硬的汉语说:"军长,我的羊群可以换条活路吗?"
当时副官一鞭子抽得老人滚下台阶,现在回忆起来,那声惨叫竟和河西走廊的哭声重叠在一起。
当陶峙岳单枪匹马闯进会议室时,三个将军像被捉奸的嫖客,马呈祥的佩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震得叶成怀里的金条撒了一地。
逃亡车队经过达坂城时遇到了沙暴,马呈祥的小妾在箱子里哭嚎着要透气,押车的士兵却盯着装满黄金的箱子咽口水。
张治中的信使就是这时候追来的,羊皮信笺上还带着迪化城里的葡萄香。
马呈祥把信纸凑近马灯,火苗窜起来的那一刻,他仿佛看见1937年那个雪夜,被马家军砍下的红军头颅在火把映照下像熟透的西瓜。
信纸烧焦的味道惊醒了装黄金的箱子里的女人,尖叫声中他喃喃自语:"野马套上笼头还能叫野马吗?"
这话听着硬气,可当车队夜过阿克苏,李祖堂的枪口对准他脑门时,这位军长掏金条的手抖得像风中的芦苇。
在印度德里的破旅馆里,马呈祥常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可嘴角总是不自觉地下垂。
有次在街头看见个背枪的锡克族警察,他竟条件反射地去摸腰间不存在的佩刀。
八千两黄金在异国他乡像雪糕般融化,打点英国殖民官员花去三成,买假护照又耗掉两成,等辗转逃到台湾时,箱底的金子只够在基隆港买套小公寓。
蒋介石给他挂了个参议员的虚职,有次酒会上白崇禧笑着问他:"马军长当年在新疆的威风呢?"他举着酒杯的手一颤,红酒洒在崭新西装上,像极了迪化起义那晚的晚霞。
晚年的马呈祥养成了剪报的习惯,尤其爱收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荒的新闻。
有次在《中央日报》角落看到篇报道,说当年骑五军的伙夫王大柱成了石河子农场的劳模,他盯着照片里那张黝黑的笑脸看了整夜。
临终前他让儿子买来青海湖的水,可装水的搪瓷缸子却怎么也找不着当年马步芳赏的银碗。
咽气前最后一刻,他忽然想起离开迪化时,陶峙岳站在城墙上喊的那句话没听清,现在终于明白了,那根本不是汉语,而是维吾尔语"胡达保佑"。
当年马呈祥用黄金买通的印度海关官员,后来全因贪污坐了牢;他花重金置办的假护照,有效期竟不到半年;而在台北替他收租的副官,最后卷走租金跑去了巴西。
倒是那些留在新疆的骑五军旧部,有人成了垦荒模范,有人当上人民代表,有个叫库尔班的骑兵连长甚至在1965年去了北京见毛主席。
马呈祥至死都没想通,为什么自己带着八千两黄金逃亡,最后却买不到一夜安眠;而那些两手空空留下的弟兄,反而在新时代找到了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