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丁玲去世,谈到当年被捕时,沈醉:她要叛变,我不会不知道 “1986年10月11日上午十点,你可以放心地写,我负责——她绝没有变节。”沈醉对面色憔悴的陈明如此保证。 当时的沈醉已从秦城旧事与国民党旧部的回忆录中抽身,定居北京陶然亭附近。陈明则刚刚办完丁玲的遗物移交手续,满脑子仍是外界传言:丁玲在南京狱中“交代问题”才得以保命。两位老人隔着茶桌对坐,窗外梧桐叶落,气氛凝重。 关于丁玲是否叛变,这个疑问在延安时期便有耳语,后来几十年时紧时松,从未彻底散去。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就是沈醉——1933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少校行动组长,也是逮捕丁玲的执行者。他一句“不会不知道”,确有分量。 时间倒退到1933年5月14日凌晨,上海霞飞路法租界。特工踹门的声响像硬币落地,丁玲只来得及把女儿抱进毯子,就被带上汽车。那天夜里,沈醉手握的逮捕名单上,丁玲排在最显眼的位置——理由并非文学,而是她党员身份与左翼宣传力度。 彼时的丁玲,三十出头。《莎菲女士的日记》让她在文化圈声名鹊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又是左联党团书记。双重身份令国民党情报部门如芒在背。戴笠授意“务必活捉”,原因简单:活人能制造宣传,死人只剩口碑。 被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后,连日车马劳顿加上高烧,让丁玲在入狱第一夜便虚脱晕厥。第二天清晨,审讯室里灯泡雪亮。沈醉例行威逼:“只要写下认识与悔过,三日即可离开。”丁玲没有吭声,只低头请求纸和笔——并非写供词,而是给狱中三岁的孩子留念。沈醉回忆道:“我看得出她心硬,她的沉默并非交易。” 有意思的是,审讯记录里一直找不到丁玲落款的“自白书”。国民党方面随后放出风声:“丁玲已悔悟,正向政府反映党内情况。”左翼内部于是有人怀疑。但凡翻检国民党档案,可发现所谓“悔悟材料”顶多是审讯人员自行撰写、盖章便存档。正因为缺少亲笔交代,直到戴笠决定“以名望为筹码暂缓枪决”,丁玲仍被圈在狱中长达三年。 1936年秋夜,她在鲁迅等人周密策划下逃离南京。一路辗转西安、保安,最后抵达延安。欢迎会上,毛泽东拍拍她的肩膀:“丁玲同志,你辛苦了!”那天丁玲穿着灰色夹袄,头发满是风尘,却冲主席露出难得的轻松笑容。延安时期,她主持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东奔西跑筹办展演,直到1942年《三八节有感》引发大讨论,再次站到风口浪尖。 抗战结束、新中国建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斩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丁玲人到中年又一次站在聚光灯下。可不到五年,反右风暴将她推往黑龙江北大荒。冻土盐碱、蚊虫成群,她硬是趴在炕沿上完成《杜晚香》的初稿。那时的她身形消瘦,却仍备三支钢笔——两支写作,一支记录每日劳动工分。 1969年,她被押解回京,投入秦城。糖尿病让她口干舌燥,审讯席上始终坚持一句话:“我是党员,不是特务。”1972年,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批示“严禁逼供”。几名审讯人员走进囚室低声道歉,她抬头只淡淡一句:“知道错就行,别再来。”仍无供词。 1979年1月,她离开山西嶂头村重返北京。随后恢复党籍、职务、名誉。可关于“南京叛变”的流言仍偶尔出现。丁玲笑对朋友:“历史会说话,只要别把我写成‘漏网特务’就行。”然而她终究没等到尘埃真正落定。1986年3月4日傍晚,坐在多福巷家中沙发上,呼吸渐弱,抬眼仿佛仍在寻找小说的下一句。 七个月后,陈明带着笔记和疑惑,拜访沈醉。两人对这位故人立场不同,却都不愿她的名字被误解。沈醉端起茶盏,凝视杯中青绿,重复那句保证:“她要叛变,我不会不知道。”说罢,他把茶一饮而尽。屋里安静,只有墙上老挂钟嘀嗒作响,仿佛在为一段终于分清黑白的往事计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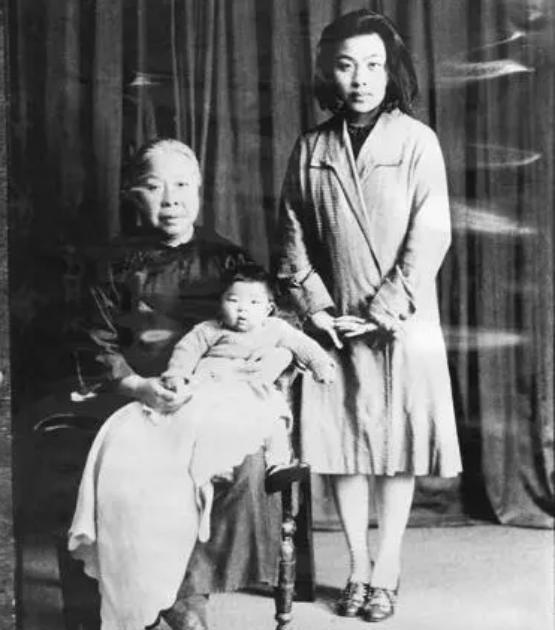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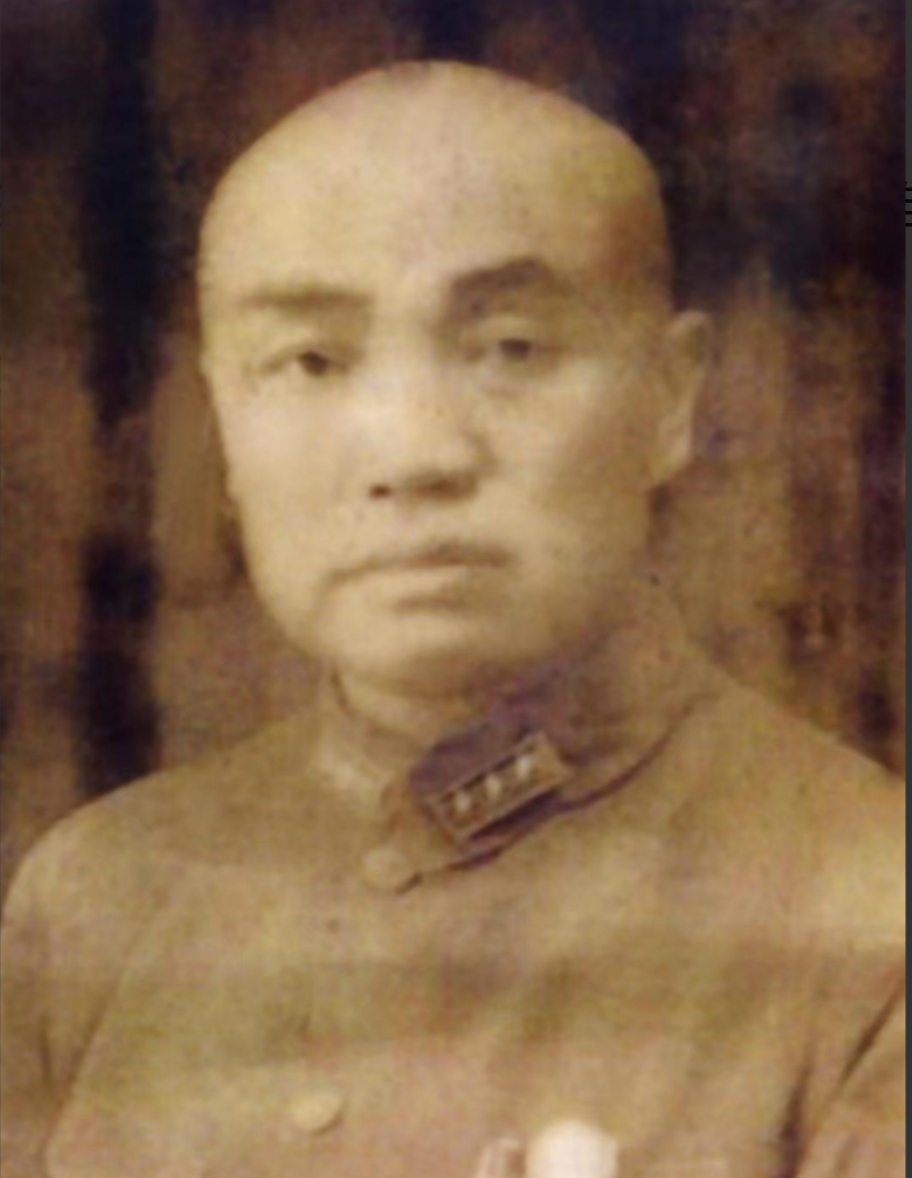






![里根总统用石油,干垮前苏联!特朗普这是学里根总统,用石油干垮俄罗斯吗?![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9997198250089616420.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