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的一天是怎样的? 乾隆3点起床,7点宠幸妃子,结束枯燥的一天。 漆黑的紫禁城中,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午门外传来,打破了凌晨的死寂。守门的侍卫揉着惺忪睡眼,勉强辨认出那是来自西北边疆的信使,身上沾满尘土和血迹,手里紧握着一封蜡封的急报。信使翻身下马,喘着粗气冲向养心殿的方向,而此时,乾隆才刚刚从浅睡中惊醒——难道是准噶尔又生变故?这封深夜而至的奏折,会不会颠覆他精心维持的帝国平衡? 这时候的乾隆,刚过四十,登基快二十年了。史书里说他“勤政爱民”,其实他自己也确实这么要求自己。打小被爷爷康熙带着读书,被父亲雍正盯着练政务,早就习惯了“天不亮就起”的日子。身边伺候的老太监李德全最清楚,皇上睡觉轻,稍有动静就醒,醒了第一件事准是问“有折子吗”。 “皇上,您醒了?”李德全轻手轻脚地挑开帐子,手里捧着温热的银耳羹,“西北来的急报,傅恒大人已经在殿外候着了。” 乾隆没接羹汤,一骨碌坐起来,披了件夹袄就往外走。养心殿的暖阁里,炭火烧得旺,却驱不散他眉头上的寒意。傅恒是他的小舅子,也是最得力的武将,这时候在殿外候着,定是急报里的事不小。 “说吧,准噶尔那边怎么了?”乾隆接过奏折,蜡封上的“加急”二字刺得眼睛疼。 傅恒单膝跪地,声音沉得像块石头:“回皇上,噶尔丹策零的儿子又反了,占了伊犁河谷,还杀了咱们三个驻兵官。” 乾隆捏着奏折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准噶尔这摊子事,从爷爷那辈就没断过,打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消停两年,又起波澜。他盯着墙上的舆图,伊犁河谷的位置被红笔圈着,那是帝国的西大门,丢不得。 “传旨,让兆惠带五千骑兵先去稳住阵脚,傅恒你筹备粮草,三日后朕要亲自部署西征。”乾隆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可李德全知道,皇上这是动了真怒——每次提到准噶尔,他眼里的光都带着刀气。 处理完急报,天刚蒙蒙亮,还差一刻到三点。李德全伺候着梳洗,太监们鱼贯而入,捧着朝服、朝珠、靴子,一样样摆得整齐。龙袍看着威风,穿起来麻烦得很,里三层外三层,领口勒得紧,天再冷也得挺直腰板。乾隆对着镜子理了理朝珠,忽然叹了口气:“这袍子,比盔甲还沉。” 七点不到,早朝的钟声响了。太和殿里,文武百官黑压压跪了一片,山呼“万岁”。乾隆坐在龙椅上,听着大臣们汇报各地的事——江南的水灾、河南的蝗灾、漕运的亏空……一件比一件挠头。有个老臣说要加征盐税,立刻被他怼了回去:“百姓刚缓过劲,你又要刮地皮?”那老臣吓得脸都白了,磕头跟捣蒜似的。 早朝散了,已经快午时。乾隆没回后宫,直接去了南书房。案几上堆着小山似的奏折,都是各地官员连夜送来的。他拿起朱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有错别字都要圈出来。有个知府写奏折拍他马屁,说“皇上圣明赛过尧舜”,他直接批了句“少拍马屁,多办实事”。李德全在旁边看着,心里直嘀咕:皇上这眼睛,比放大镜还尖。 午饭简单得很,四菜一汤,都是家常菜。他吃饭快,不像别的皇帝讲究“食不言”,边吃边问李德全:“令妃那边怎么样了?昨儿说她有点咳嗽。”李德全回:“太医瞧了,说是受了点凉,不打紧。”他“嗯”了一声,没再多问——后宫的事,他向来不怎么上心,不是无情,是真没功夫。 下午接着批奏折,批到太阳西斜,眼睛都花了。他揉了揉太阳穴,让太监读段《论语》解闷。读到“其身正,不令而行”,他忽然停下来,对傅恒说:“咱们这些当政的,自己站得直,底下人才不敢歪。”傅恒点头称是,心里却清楚,皇上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他总怕自己像前朝的皇帝那样,被安逸磨了性子。 傍晚时分,他去了趟令妃的翊坤宫。令妃正坐在窗前绣花,见他来,赶紧起身行礼。他没让她跪,拉着她的手坐了会儿,问了问孩子的功课,说了几句家常。没坐半个时辰,就起身要走:“还有几本奏折没批完,你早点歇着。”令妃知道他的性子,没挽留,只递给他一件披风:“夜里凉,皇上仔细着。” 回到养心殿,天已经黑透了。乾隆坐在灯下,接着看奏折。有一本是福康安送来的,说他在西北打了胜仗,俘虏了叛军首领。他笑了笑,提笔批了个“赏”字,又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这是他难得的孩子气,只有对着自己疼爱的晚辈才这样。 夜深了,李德全催了好几遍,他才放下朱笔。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不是准噶尔的战事,就是江南的水情,像有无数根线牵着,怎么也松不开。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康熙带他在畅春园放风筝,那时候多自在啊,不用看奏折,不用管朝政,风一吹,风筝就能飞得老高。 可现在,他是皇帝。这天下的风筝,都攥在他手里,松一分不行,紧一分也不行。 信息来源:基于《清高宗实录》《乾隆起居注》及清代《啸亭杂录》等史料记载综合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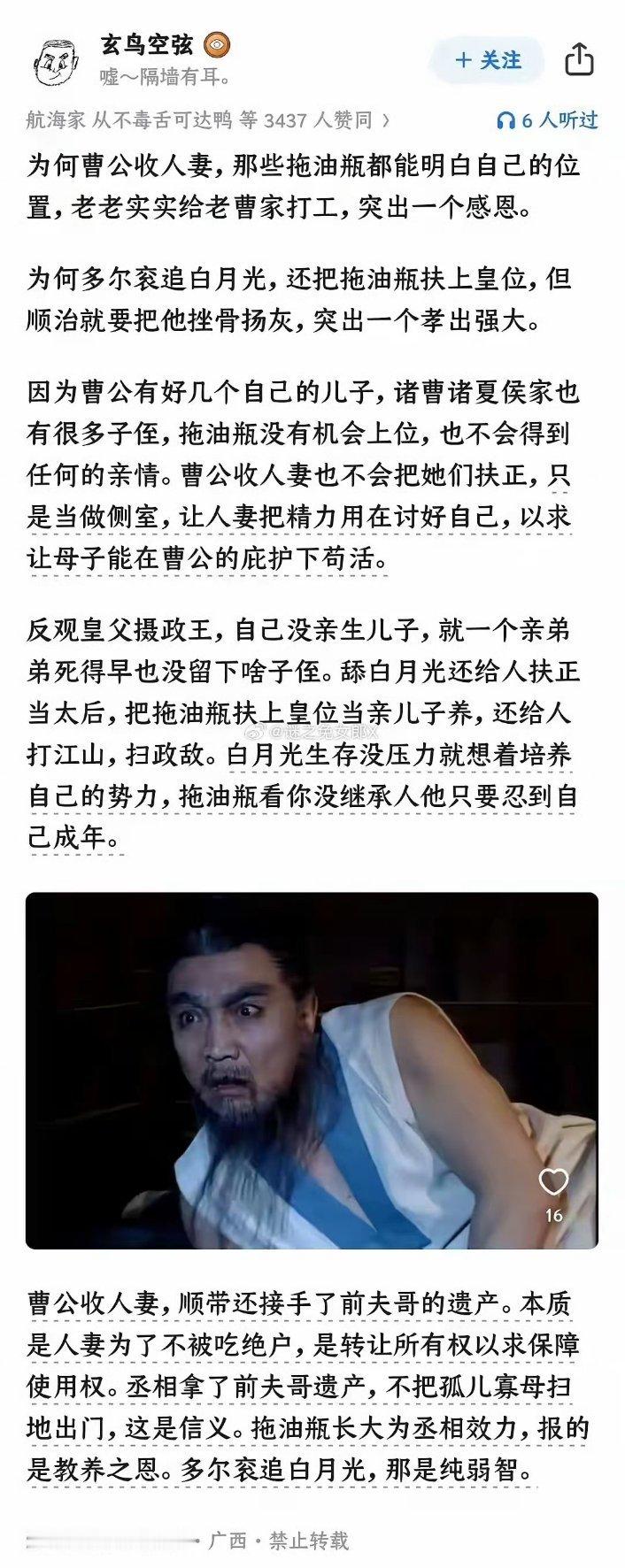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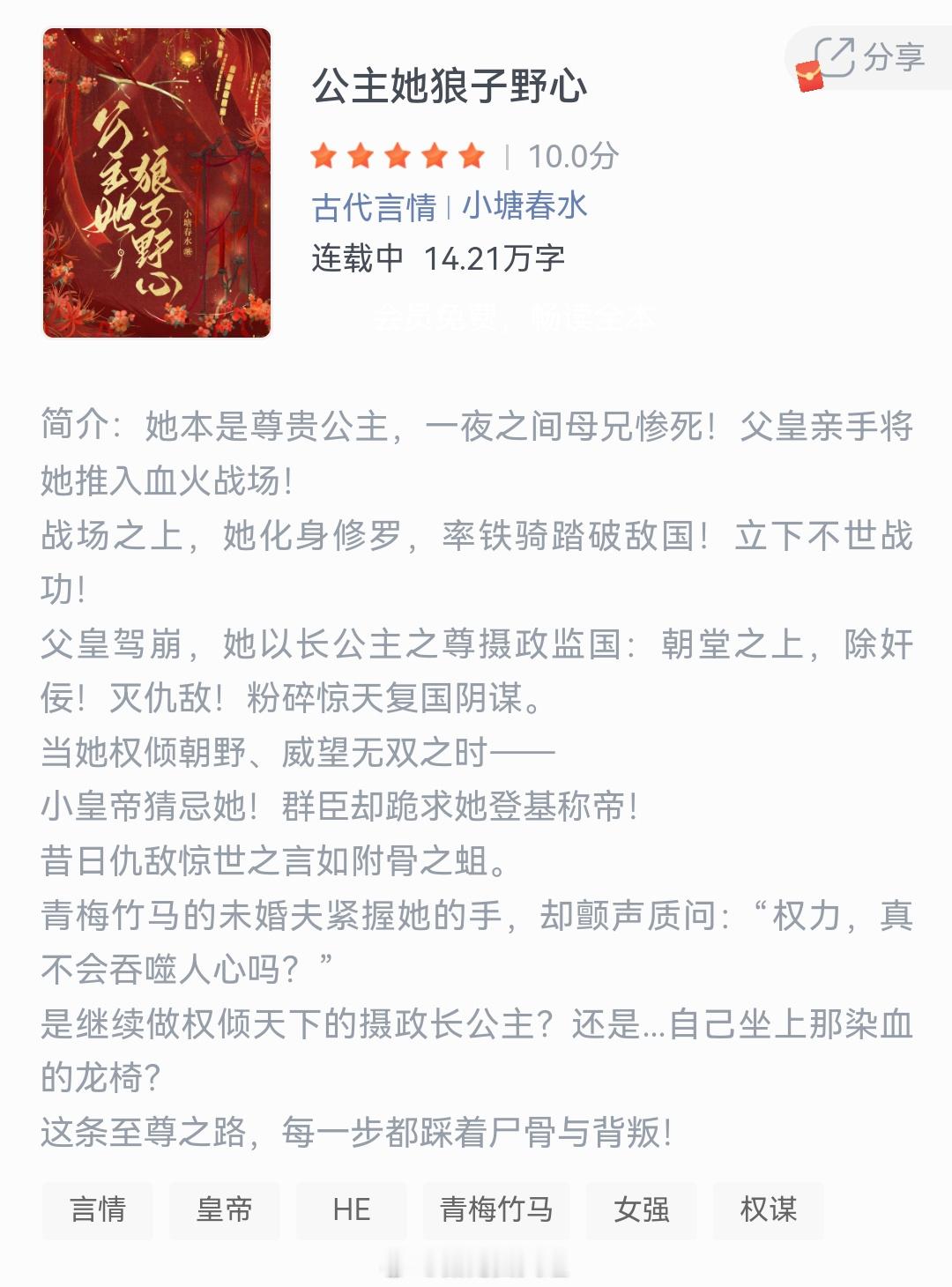



星辰大海
清朝对外积极进取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