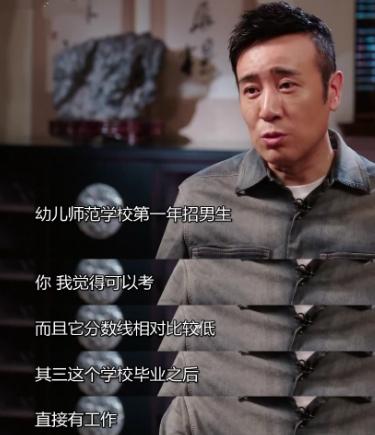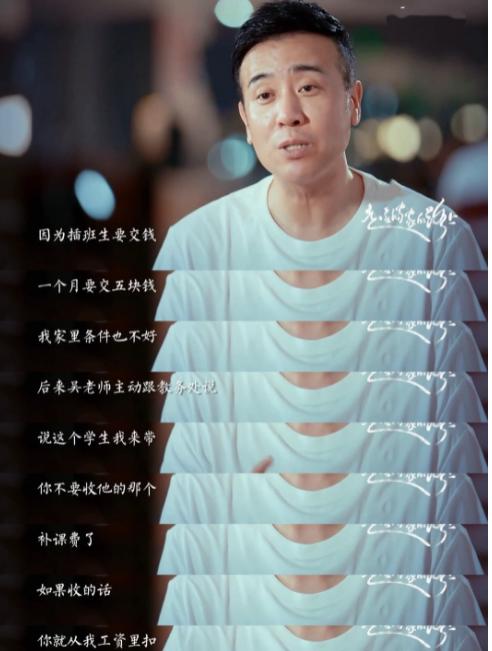于和伟:“我初三复读的时候,班主任吴宏斌老师和我说:‘于和伟,你的成绩考高中费劲,而且你考上高中又能怎么着?你家庭条件又不好,你还要接着念大学吗?今年抚顺幼儿师范第一年招男生,分数线比较低,你可以去考这个学校,一毕业就有工作。’ 在一次央视《艺术人生》的采访里,于和伟聊起人生最难忘的人时,突然红了眼眶。 他没提那些合作过的名导巨星,反而反复说起一个名字,吴宏斌,他初三时的班主任。 上世纪80年代的抚顺,老工业区的烟囱总在清晨冒着灰白的烟,于和伟家就在离工厂不远的老胡同里。 那时候他刚经历第一次中考失败,复读那年,于和伟转到了吴宏斌老师的班。 他是插班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上课不敢抬头,下课也很少和同学说话。 每天放学,他要先帮母亲收拾好缝补的摊子,再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里那盏昏黄的路灯下写作业。 路灯的光很弱,照在课本上总有些模糊,他得凑得很近,手冻得握不住笔时,就把笔揣进棉袄兜里暖一会儿,再接着写。 那时候班里要收每月五块钱的补课费,他攥着母亲给的皱巴巴的两块钱,在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敢进去。 吴老师大概是看出了他的窘迫,有天下午,于和伟正蹲在教室后门补作业本上的破洞,吴老师走了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办公室里,吴老师的桌上放着一个印着“抚顺三中”字样的搪瓷杯,里面的茶水已经凉了,旁边堆着一摞没批改的作文本。 于和伟,你的成绩考高中费劲,而且你考上高中又能怎么着? 吴老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于和伟的头埋得更低了,他以为老师要批评他不用功。 可没等他解释,吴老师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得整齐的招生简章。 今年抚顺幼儿师范第一次招男生,分数线不高,毕业就能分配工作,你试试? 于和伟盯着那张纸上“包分配”三个字,突然鼻子一酸。 他从没敢想过“毕业就有工作”,母亲每天缝补到深夜,也赚不了几个钱,要是自己能早点挣钱,母亲是不是就能少受点累? 后来他才知道,吴老师早就跟教务处说了,他的补课费不用交,要是学校不同意,就从吴老师的工资里扣。 不仅如此,吴老师还把自己孩子用过的课本拿给他,课本上用蓝笔标着重点,空白处还写着吴老师的批注。 那年夏天,于和伟如愿考上了抚顺幼儿师范,毕业后也如愿分配了工作,日子过得安稳,可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有天路过抚顺市话剧团,他看见墙上贴的招生海报,被风吹得哗啦响,上面写着“不限专业,热爱即可”。 他想起小时候偷偷在邻居家听话剧广播的日子,咬了咬牙,报了名。 面试那天,他没准备复杂的才艺,就唱了首在幼儿园教孩子的儿歌,没想到考官笑着问他,愿意学话剧吗? 刚进话剧团时,他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有次排戏,导演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台词像含着糖”。 他没反驳,晚上买了本《新华字典》,揣在兜里,没事就拿出来翻,一个字一个字地练发音,连吃饭时都在琢磨平翘舌。 后来话剧团有个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的名额,团里推荐了他,可学费又成了难题。 大姐知道后,把给儿子新买的钢琴卖了,钢琴被搬走那天,侄子抱着她的腿哭,她却笑着说,你小叔能去上海读书,比啥都强。 哥哥也把自己攒的结婚钱拿了出来,塞给他时,手上还沾着工地的水泥灰。 上戏的前两年,于和伟过得很艰难,小品总被老师批评,他甚至偷偷在被窝里哭,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演戏。 可一想起吴老师当年的话,想起家人的付出,他又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毕业后,他和女友宋林静一起进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没想到又回到了跑龙套的日子,这一跑就是好几年。 最绝望的时候,他走到南京长江大桥上,看着桥下的江水,差点跳下去,是宋林静从身后抱住他,哭着说,你妈45岁才生下你,她容易吗? 这句话让他醒了过来,后来他接了《曹操》里的小配角,拍了两天,赚了400块钱,用这笔钱和宋林静办了场简单的婚礼。 再后来,《历史的天空》让他被观众记住,《军师联盟》《觉醒年代》让他成了“演技派”的代名词。 成名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抚顺找吴老师。见到吴老师的那一刻,他没说什么华丽的话,只是抱着老师,哭得像个孩子。 他还给八个哥哥姐姐都买了房,当年他们帮他,他从没忘过。 现在有人说于和伟运气好,遇到了吴老师。 可只有他知道,吴老师当年的话,不是运气,是实实在在的守护。 比起空泛的鼓励,吴老师更懂一个贫困家庭孩子的难处,用最直白的方式,帮他找到了一条能走通的路。 而他能走到今天,不止是因为遇到了贵人,更是因为他把这份善意记在心里,用努力一点点实现了当年所有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