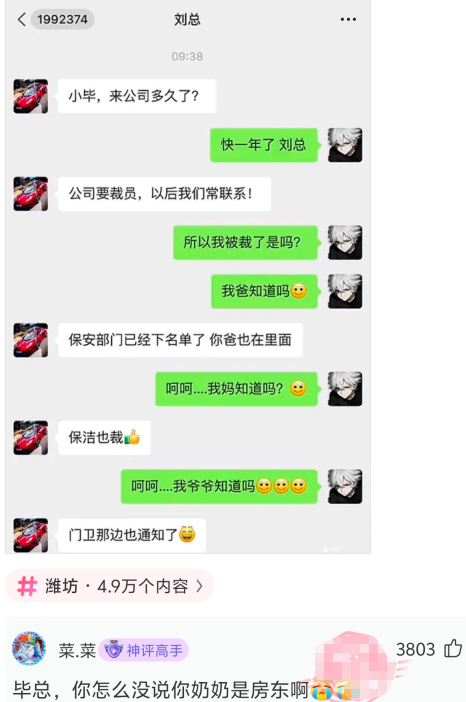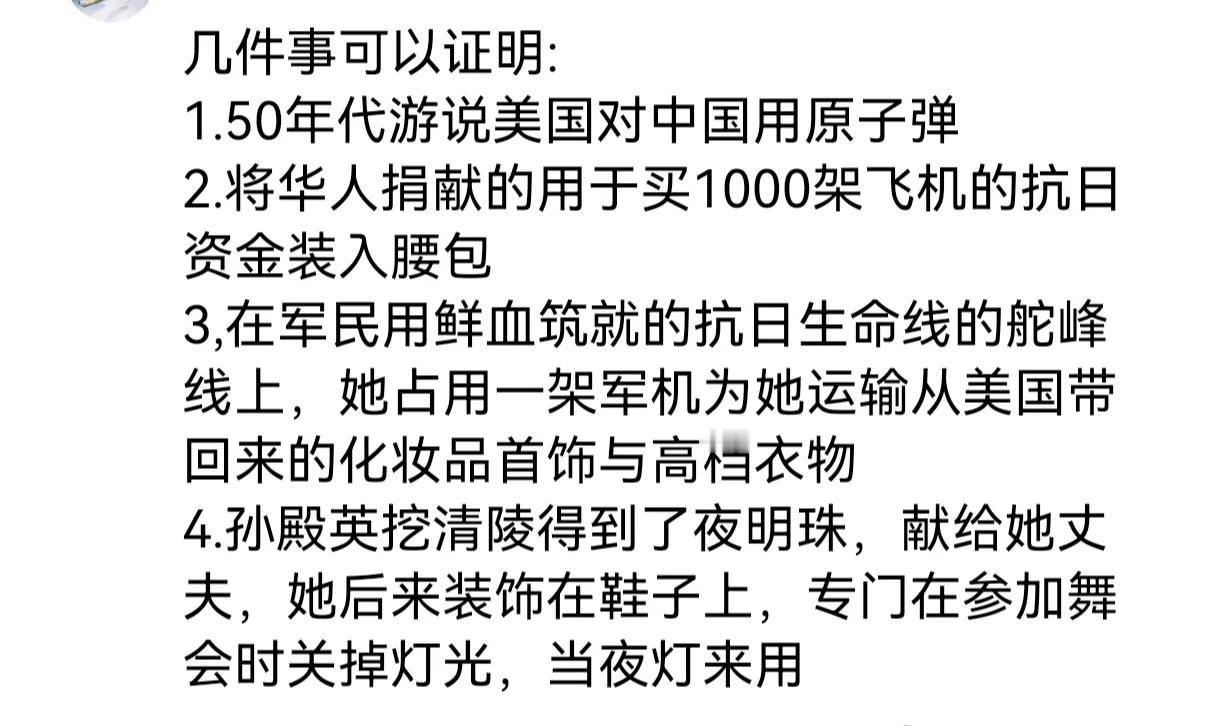非常令人深思的一段话: “一个可怕的现象:家庭社交,正在慢慢消失。家人的朋友,不是“共同好友”。老一辈的人,走亲访友,但是孩子根本不在乎,甚至都不会跟着去。一部分夫妻之间,不仅花钱AA制,社交都是各自为政了。家不待客,成为了一种常态。客人不到家里,那么家庭社交,就越来越少,家人各自的朋友,没有了过多的交集。” 上周母亲生日,我推开家门时,她正对着微信家族群里的祝福消息,一个个回复语音。 “谢谢二舅!” “小姑有心了!” 声音洪亮,带着表演性质的热情。 餐桌上放着外卖点的四菜一汤。我们母子二人相对而坐,中间隔着沉默。她的手机还在不停震动,那些她刚感谢过的亲戚,没有一个人打来电话。 这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今天。同样是母亲生日,家里挤满了人。父亲在阳台支起圆桌,男人们喝酒划拳;姑姑阿姨们挤在厨房,一边帮忙一边聊天;我们几个孩子满屋子追逐打闹。那时的家像个热闹的集市,空气里都是人间的烟火气。 现在,这套三居室安静得像酒店的套房。 上周表姐女儿满月,母亲想去喝喜酒,问我要不要一起。我正忙着赶项目进度,下意识拒绝:“妈,您代表就行了。”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你小时候,最喜欢去表姑家玩。” 我这才想起,确实有个表姑住在城南。她家有个院子,种着葡萄树。夏天我们去,她总会摘最大的一串洗给我们吃。可如今,我连她家具体地址都忘了。 老一辈的人,走亲访友,但是孩子根本不在乎。 这种断裂,在我自己的小家庭里更加明显。 我和妻子的手机通讯录,像是两个平行世界。她的闺蜜团定期聚会,照片里是我不认识的笑脸;我的球友群周末约球,她连名字都记不全。 上个月,她想请同事来家里吃饭。我第一反应是抗拒:“去餐厅不行吗?家里还要收拾。” 她愣了下,点点头。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三年没在家招待过客人了。 家不待客,成为了一种常态。 最让我震惊的是上个月对账。我发现我们连物业费都是各付一半。不仅如此,水电煤气、孩子学费、父母赡养费……所有开支都被精确地分摊。 “这样清楚。”妻子说。 是啊,清楚得像合租的室友。 今天下午,我鬼使神差地翻出老相册。有一张照片让我停留很久。那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在家聚餐,五六个人围坐,中间是冒着热气的火锅。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放松的笑。 母亲走过来,轻声说:“这是你爸四十岁生日。你看,老周、你张叔、李伯伯……现在都走散了。” 我看着照片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突然明白:家人的朋友,不是“共同好友”,这个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粘合剂。 曾经,父母的社交圈像一张网,把我们牢牢地罩在“家”这个概念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独立的点,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偶尔交汇,却再也织不成网。 我合上相册,走到客厅。妻子在追剧,儿子在房间打游戏。这个家什么都有,有Wi-Fi,有外卖,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卧室。 却唯独缺少了客人。缺少了那种推开门,热气扑面而来的喧闹;缺少了厨房里多炒两个菜的忙碌;缺少了送客时“常来坐坐”的客套话;缺少了孩子被塞红包时羞涩的推拒。 客人不到家里,那么家庭社交,就越来越少,家人各自的朋友,没有了过多的交集。 我拿起手机,给老周的儿子发了条微信:“周末有空吗?带上孩子来家里坐坐,我爸留了盒好茶。” 放下手机,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里面塞满了各种独立包装的食品,适合一个人加热,一个人吃。 但没关系,周末之前,我会把它清空,填上新鲜的、需要分享的食材。 也许,该让这个过于干净、过于安静的家,重新沾染上陌生人的气息了。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传统的家庭社交,正是以家庭为圆心推出去的波纹。父母的朋友、亲戚,自然成为子女社交圈的一部分,形成"共同好友"。 而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让每个人都成了独立的圆心,各自推出自己的波纹。"家人的朋友不是共同好友",本质是家庭作为基本社交单元的瓦解,每个人都在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网络。 鲁迅在《故乡》中写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家的温度,也需要人来人往才能维系。客厅那条通往沙发的路,厨房那套待客的茶具,都需要客人的足迹与使用来证明其价值。 "家不待客"让家的功能退化为单纯的栖息之所,失去了其作为情感交流空间的社会功能。一条无人走的路会荒芜,一个不待客的家也会失去温度。 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分析:"现代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社会给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家庭社交的消失,正是这种安全感流失的表现。 家庭社交的消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我们享受着独立与清净带来的便利,却未曾察觉正在失去什么。 家的温度,终究需要人来人往才能维持。那扇门的开合之间,流淌的正是生活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