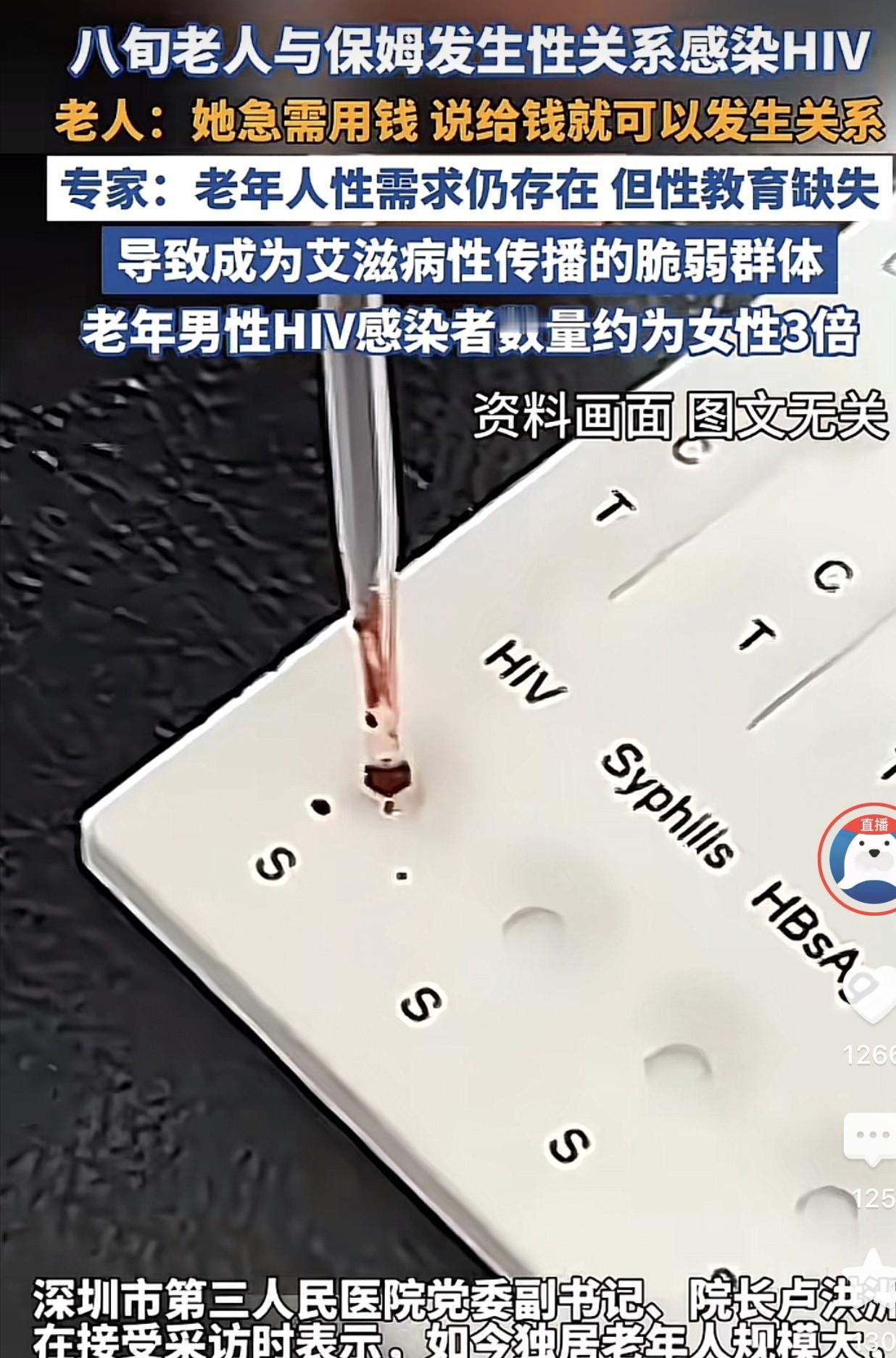北京,一八旬老伯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结果却发现竟然感染了HIV,经过深入询问,原来老伯家中雇佣了一个女保姆,女保姆告诉老伯现在急需用钱,只要给钱就可以发生,老伯按耐不住给了钱,结果却遭了殃。 那一纸化验单拿在手里,分量重得几乎要把那位八旬老人的腰给压断。 北京的某家医院走廊里,空气仿佛凝固了。医生看着眼前这位满头银发、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大爷,神色凝重地把“HIV阳性”的结果递了过去。大爷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愤怒和极度的错愕,他甚至觉得自己听到了这辈子最大的笑话。一辈子老实本分,老伴走了以后更是清心寡欲,平日里连大门都不怎么出,这怎么可能?嘴里哆嗦着“搞错了”,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就在几天前,他还只是觉得浑身没劲、昏昏沉沉,像是感冒却又拖着不好。是家里的保姆看着不对劲,不仅一如既往地殷勤伺候,还主动提议带他来医院瞧瞧。原本以为就是人老了零件老化,或者是流感作祟,谁能想到,这看似贴心的陪诊,竟然揭开了一个让老人在晚年身败名裂的脓疮。 医生见多了这种场面,等老人那股激动的劲头稍稍下去,便把他拉到诊室一角,避开旁人,轻声让他好好回忆:这半年内有没有输过血?用过不干净的针头?或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亲密接触? 老人的目光有些躲闪,端着保姆递过来的热水杯,那股热气没能暖了他的手,反而让他打了个寒颤。他的眼神不由自主地飘向了正在门口候着的那个身影——那是他雇来照顾自己起居的女保姆。 在这个充满消毒水味道的空间里,记忆被迫倒带,定格在了一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 那时候也是在家里,子女都在外地忙事业,诺大的房子里空空荡荡,只有他和保姆两个人。那天晚饭后,保姆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收拾家务,而是眼圈红红地坐在了一旁。这一坐,就坐出了事端。保姆声泪俱下,说是自家儿子骑车把人给撞了,对方索要高额医药费,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想求大爷救急。 这一开口就是五万块现金。对于退休金稳定、有些积蓄的老伯来说,钱不是给不起,但也不是小数目。见老人面露难色,保姆凑近了身子,压低了声音,抛出了那个带有暗示性的筹码:只要肯帮忙,她愿意用“那种方式”来报答。 人到了八十岁,身体机能虽衰,但情感上的孤独和渴求却未必会随着皱纹的增加而消逝。尤其是长期独居的老人,那种日复一日的死寂,往往比疾病更难熬。也就是那一瞬间的糊涂,老伯那道名为“理智”的防线彻底崩塌。第二天,五万块钱递了过去;紧接着的几天里,那原本仅仅是雇佣关系的界限,在昏暗的卧室里被几次逾越。 事后老伯不是没有后悔过。这种有悖伦理又难以启齿的交易,成了他心底的秘密,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只能烂在肚子里。但他万万没想到,那几次为了排解寂寞的“荒唐”,代价竟然是以生命倒计时为计量单位的。 回到家后,面对铁证如山的化验单和老伯几近崩溃的质问,保姆终于也没法再演下去了。那个“儿子撞人急需用钱”的理由或许有几分真假难辨,但她承认了最致命的一点:她早就知道自己感染了那个病,因为怕丢工作,也因为没钱正规治疗,一直瞒着。提出那种“报答”,无非是觉得老人年事已高,自己只要做得隐蔽,未必就会出事,纯粹是抱着一种极度自私的侥幸心理在赌博。 她赌赢了那一时的钱财,却输掉了老人余生仅存的尊严和健康。 从法律的角度把这事儿掰开了看,这一场看似隐蔽的“家庭内部交易”,早就越过了红线。保姆那是明码标价,给钱就能发生关系,这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在法理上已经构成了卖淫嫖娼。根据治安管理相关规定,这至少得面临行政拘留和罚款。 但更让人脊背发凉的还在后面。这个保姆是在“明知”自己有严重性病的情况下,依然选择通过这种高危途径去进行交易。这种行为在刑法上早已被死死盯住——明知自己患有严重性病而进行卖淫嫖娼的,那就涉嫌传播性病罪,五年以下的刑期是跑不了的。 甚至,如果细究起来,她明知病情却隐瞒,最终导致老人遭受重创,这就不仅仅是传播疾病那么简单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故意伤害,而且是导致他人“重伤”。要知道,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量刑起步就是三年,最高可达十年。为了那五万块钱,这女保姆算是一脚把自己踹进了监狱的大门。 虽然子女不在身边是常态,虽然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不分年龄,但这种将情感慰藉寄托在金钱交易上的“地下情”,终究是走在悬崖边上。社区的讲座也好,普法宣传也罢,往往难以触达这部分隐秘的角落。那些平日里看着体面、有着稳定收入的独居老人,往往在面对这种“温情陷阱”时,比年轻人还要脆弱得多,也容易被拿捏得多。 老伯瘫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北京灰蒙蒙的天,那笔用来“救急”的五万块钱,如今看来,买来的竟是一张通往绝望的单程票。晚年本该享享清福,哪怕腿脚不便也就是少走两步路的事,可现在,等待他的将是无休止的病痛折磨和漫长的抗病毒治疗。那份羞耻感,比病毒蔓延得还要快,彻底吞噬了他剩下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