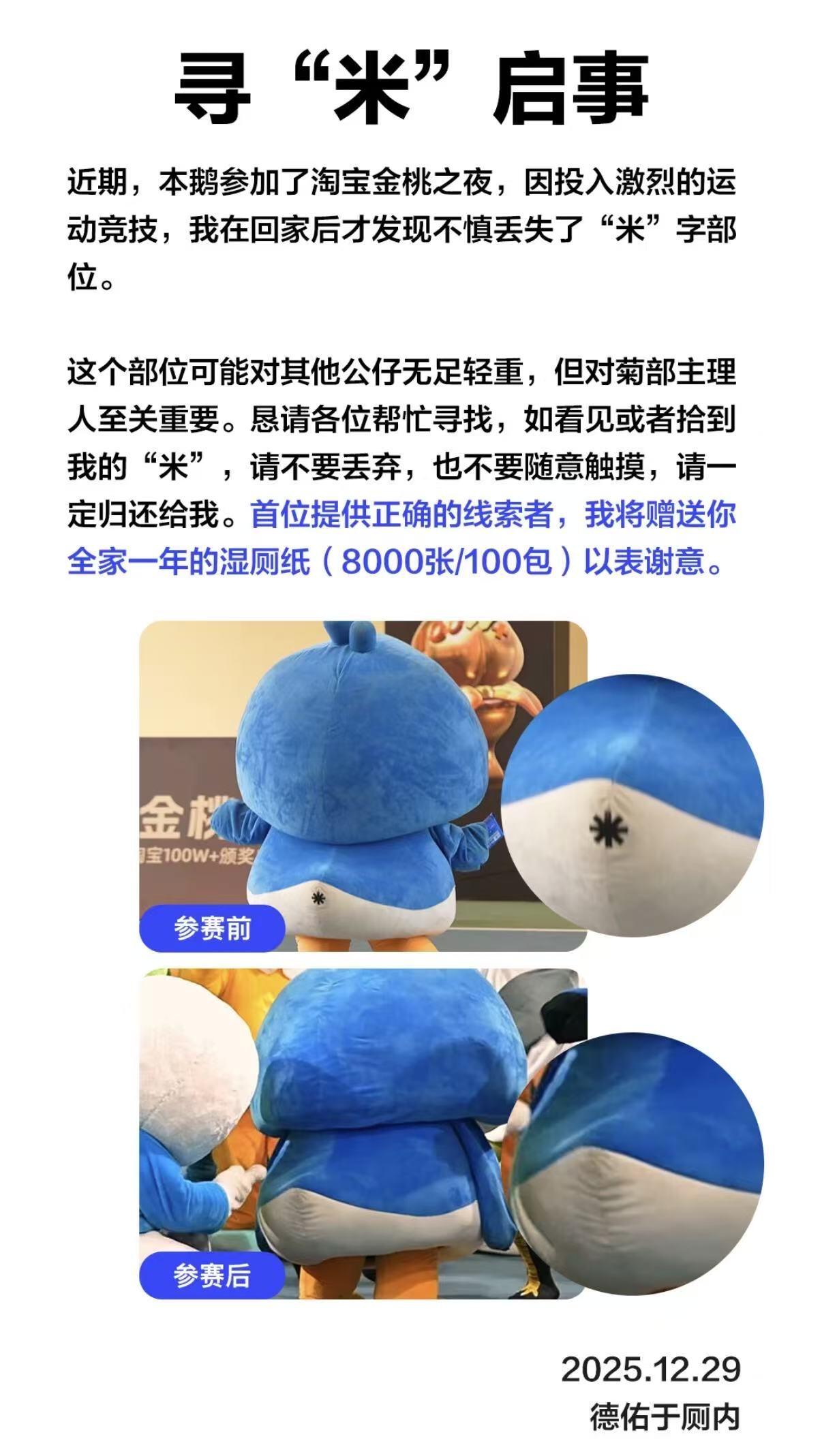一个18岁的姑娘,眼看追兵一脚踹开了家门,她一咬牙,跳上炕,挨着那个满头是血、昏迷不醒的陌生男人坐下。她冲着那帮凶神恶煞的兵喊:“别过来!他是我男人,得了传染病,头都烂了!” 1940年的那个冬夜,河北平山县的一间破茅草屋里,18岁的姜达泉披头散发,死死护在炕前。屋里那盏豆油灯晃得厉害,把鬼子兵影子拉得老长,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鬼怪。带头的那个小胡子眯着眼,手里刺刀明晃晃的,往前凑了半步。炕上那男人的血已经渗到破褥子外头,黑红黑红的一片。姜达泉能闻见血腥味混着土炕的柴火味儿,她手心全是汗,冰凉冰凉的。 “传染病?”小胡子中国话倒利索,可那调子阴阳怪气,“什么病?” 姜达泉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她猛地扯开男人头上那块浸透血的破布,那是她刚从他伤口上撕下来的。伤口暴露在昏黄灯光下,皮肉翻着,血糊糊的一片,看着真像是烂掉了。“瘟病!会过人的!”她嗓子又尖又颤,不知哪来的劲儿,竟往前挺了挺身子,“你们不怕死就上来!俺们夫妻要死一块儿死!” 这话喊出来,她自己都吓了一跳。什么夫妻不夫妻的,她连这男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半个时辰前,她正打算插门睡觉,就听见外头乱糟糟的脚步声、狗叫声。然后院墙那头“扑通”一声闷响,她大着胆子举着煤油灯出去瞧,就见这人倒在她家柴火堆边上,棉袄都让血浸透了。还没来得及想清楚,村子东头已经响起了砸门声和哭喊声。她几乎是本能地,连拖带拽地把这血人弄进了屋,刚抬上炕,自家那扇破木门就被踹开了。 现在想想真是后怕。要是被鬼子发现她在藏人,别说她活不成,恐怕整个村子都得遭殃。可那时候哪顾得上那么多?她只看见一个血人,听见外头是鬼子的声音,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她脑子里就剩下一个念头: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炕前那几个兵明显犹豫了。那年头,缺医少药的,传染病真是能吓住人。尤其那伤口的样子,看着确实骇人。小胡子用刺刀挑开男人另一只胳膊的袖子,胳膊上也有伤,但不像头上那么吓人。他盯着姜达泉,这姑娘脸煞白,头发乱糟糟的,可那双眼睛直勾勾瞪着他,里头有怕,但更多的是豁出去的狠劲儿。 “搜!”小胡子一挥手,但自己却往后退了半步。 屋里本来就没啥东西,一个破柜子两口缸,鬼子用刺刀胡乱捅了捅,米缸里搅和几下,又踹翻了墙角的破篓子。姜达泉跪在炕上,身子挡在男人前头,指甲都快掐进自己手心肉里了。她感觉炕上那男人好像动了一下,极轻微地,吓得她后背一凉,赶紧用身子往后靠了靠,把他挡得更严实。 “走!”小胡子大概觉得这破屋和这两个“病秧子”实在没啥油水,也可能真怕染上什么病,终于带着人撤了。脚步声和叽里呱啦的说话声渐渐远去,村里零零星星还有哭喊声,但姜达泉家这小院,总算暂时安静下来。 油灯噼啪爆了个灯花。姜达泉浑身一软,差点从炕沿栽下去。她缓了好一阵,才哆嗦着手去探那男人的鼻息——还有气,弱得很。她打来凉水,一点一点擦他脸上头上的血。伤口在左边额角,像是被什么钝器打的,肉都翻开了,血糊住了半张脸。擦干净些才看清,这人年纪不大,估摸也就二十出头,脸虽然没血色,但眉眼周正,不像附近的庄稼汉。 他棉袄里头露出半截灰蓝色的衣服边,那颜色让姜达泉心里咯噔一下。她听说过,山里那边的人,有时候就穿这个颜色的衣服。她手顿了顿,但很快又继续清洗伤口。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不是鬼子汉奸。就冲鬼子追他,这人就不会是坏人。 那年月的平山,天是鬼子的天,地是鬼子的地,可人心深处,总还有那么一块地方,亮着一盏不肯灭的灯。很多像姜达泉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没念过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们认得清谁在祸害自己的家,谁在保护这片土地。那种选择,往往就在一刹那,凭着骨子里的血性,和心里最朴素的是非对错。 后来姜达泉总想,要是当时知道这人真是八路军的小交通员,身上还揣着要紧的信,她会不会更害怕?或许吧。但再想想,知道了又怎样?她还是会把他拖进屋,还是会跳上炕喊出那句话。有些事,怕也得做,那是做人的底线。 那个冬天特别冷,可很多人的血是热的。姜达泉用家里最后一点草药给那人敷上,把仅有的半碗高粱米熬了粥,一点一点喂他。三天后,男人醒了过来。他没说太多,只深深看了姜达泉一眼,说了一句:“大姐,救命之恩,记下了。”然后在某个夜里,悄悄走了,像他来时一样突然。 姜达泉后来还是嫁了人,生了娃,经历了更多战乱和困苦。她很少跟人提起那个冬夜的事,仿佛那只是漫长岁月里一个模糊的片段。但我知道,有些选择会刻在一个人的骨子里。在那么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一个18岁的农村姑娘,用她全部的勇气和本能,守护了一个陌生的生命,也守护了她心里那份未曾言明的信念。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普通人最真实、也最伟大的地方——他们没有冲锋陷阵,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了照亮黑暗的抉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