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蜷在铺了钩针桌布的小沙发里翻《给麻风病人的吻》,读到一半突然把书扣在腿上 —— 不是读不下去,是胸口那股闷劲上来了,像把半块浸了凉茶水的糕堵在喉咙口,涩得连呼吸都慢了半拍。
书的封面是淡蓝底配嫩黄色块,衬着个没画脸的女人侧影,我当初是冲着 “莫里亚克的冷门短篇” 捡回来的,没成想一翻开,就撞进了诺埃米和让・佩鲁埃尔那摊温吞又刺人的婚姻里。

这是桩从开头就写满 “不情愿” 的包办婚姻:诺埃米嫁的让,是个体弱到连床都嫌大的男人,苍白、瘦削,连靠近妻子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卑微。
我在书页里看到自己划的线 ——“他故意小口慢啜,只为让那温软的臂弯在颈间多停留片刻”,旁边写着 “同床共枕却像隔了万水千山”,现在再看,还是觉得扎心:两个躺在一张床上的人,一个要假装熟睡躲着对方的触碰,一个要借着喝水的由头贪念一点体温,连 “夫妻” 这两个字,都像裹了层砂纸,磨得人疼。

书名叫《给麻风病人的吻》,我原先以为是隐喻爱情里的 “病”,读到中间才懂:诺埃米给让的那些吻,从来不是情爱里的柔软,是像圣人俯身给麻风病人施予的怜悯 —— 她凑到他汗湿的额角印下嘴唇,他却偏过头受不住,那哪里是心动的羞怯?是知道 “这温柔不是给我的” 的难堪。
我在这段旁边写了 “诺埃米的吻无关情爱,只剩对苦难灵魂的怜悯”,合上书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让哪里是 “麻风病人” 啊,他是被婚姻这张网裹住的囚徒,连对方施舍的善意,都要捧着怕碎了。
最让人喘不过气的,是这俩人都不是 “坏人”。
诺埃米会给让煮加了陈年酒的汤,会高声念书哄他消食,哪怕知道对方早就睡着,也硬撑着不肯停 —— 她在尽一个 “妻子” 的本分,哪怕心里的厌恶已经快漫出来;
让更不必说,他知道诺埃米不爱自己,所以连睡在一张床上都要选窄的那侧,连碰一下对方的衣角都要假装是 “不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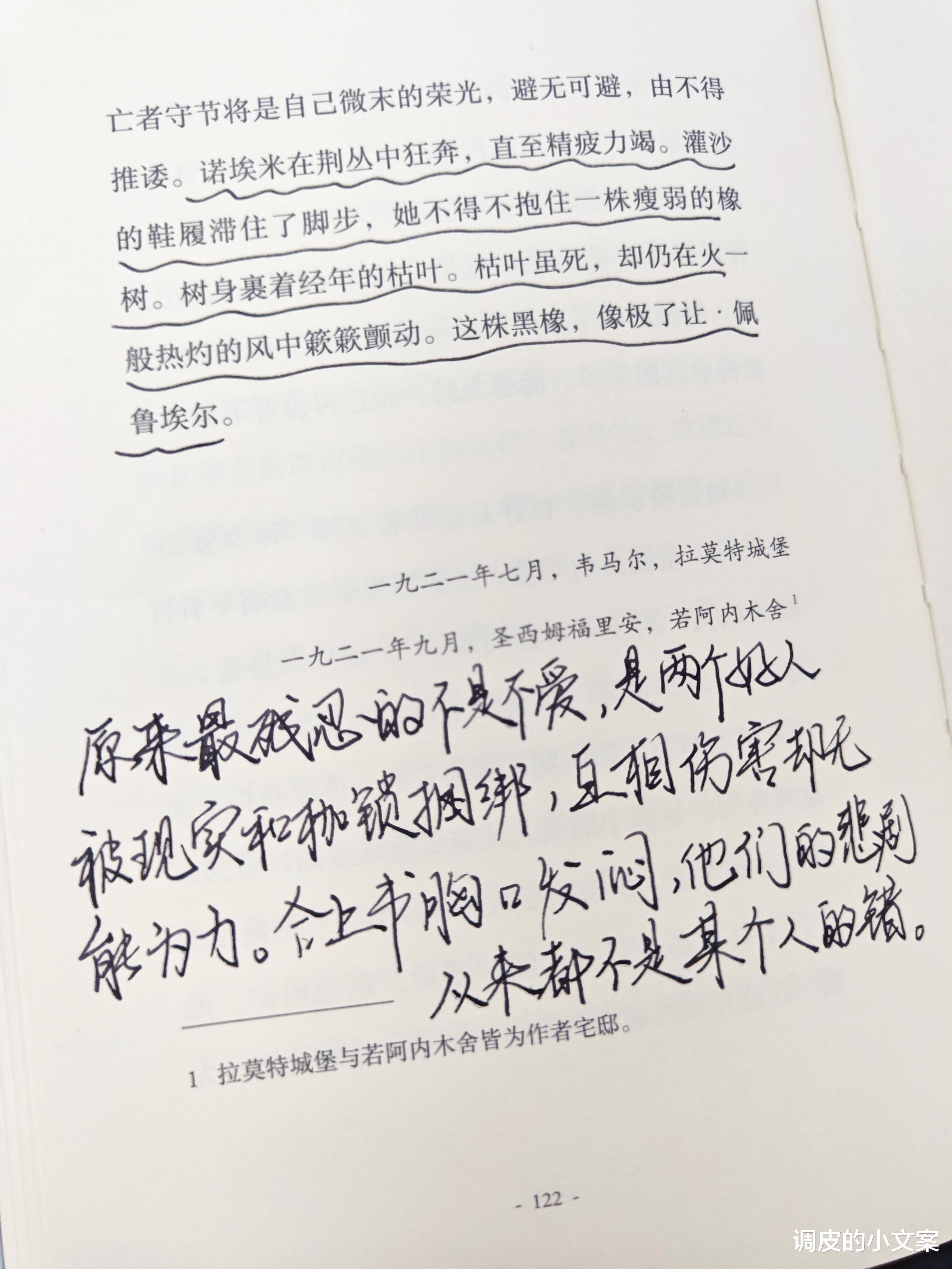
我在书的最后一页写:“原来最残忍的不是不爱,是两个好人被现实和枷锁捆绑,互相伤害却无能为力。”
合上书的时候盯着这句话看了好久:没有出轨,没有争吵,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可就是这种 “相敬如‘冰’”,才是最磨人的 —— 诺埃米在荆丛里狂奔,把那棵颤巍巍的黑橡树比作让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了他们的婚姻:枯着,弱着,连风一吹都要抖,却只能钉在原地,熬着那点微末的 “体面”。

读到让因为诺埃米的一个吻而掉眼泪那段,我把书页折了个角。
书里写 “却触到一片温热的咸湿”,我在旁边写 “夜里诺埃米的退缩像刀子扎心,让便主动躲得更远,并流下奢望温情的滚烫泪水”—— 他的爱太卑微了,像落在尘土里的星子,连发光都怕晃着对方;而诺埃米的厌恶太真实了,真实到她要把自己缩在床和墙的夹缝里,才能熬过每一个同床的夜晚。
这哪里是婚姻啊?
是两个被推到一起的陌生人,披着 “夫妻” 的外衣,做着最熟悉的 “绝缘体”。我们总说 “找个好人就过一辈子”,可莫里亚克偏要把这层漂亮的布扯下来:好人凑在一起,没有爱的黏合,剩下的只有 “熬”—— 熬着长辈的期待,熬着世俗的眼光,熬着连自己都骗不过去的 “相安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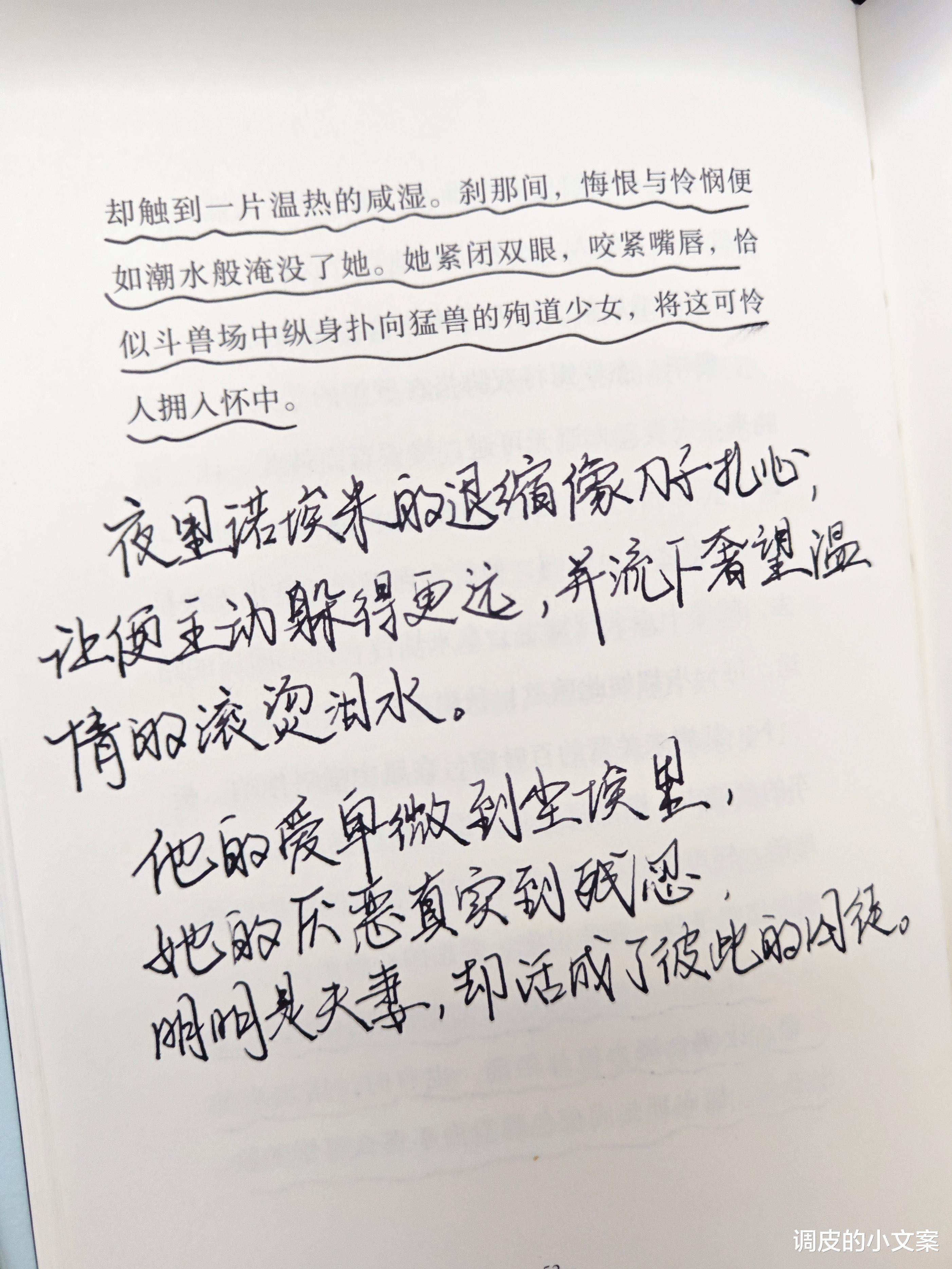
合上书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我盯着扉页那句 “无人知晓,那些满身溃疡的麻风病人,是否会因疮口沾染了圣洁之气而欢欣” 发愣。诺埃米的吻是 “圣洁” 的,是符合所有人期待的 “贤妻” 所为,可让接住的哪里是吻啊?是裹着糖衣的钝痛,是明明够不到爱,却还要假装被温暖的难堪。
到现在我再想起这本书,脑子里还是诺埃米缩在床缝里的样子,和让那滴落在枕头上的眼泪 —— 有些婚姻,从来不是 “两个人的圆满”,是两个好人,在枷锁里互相熬着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