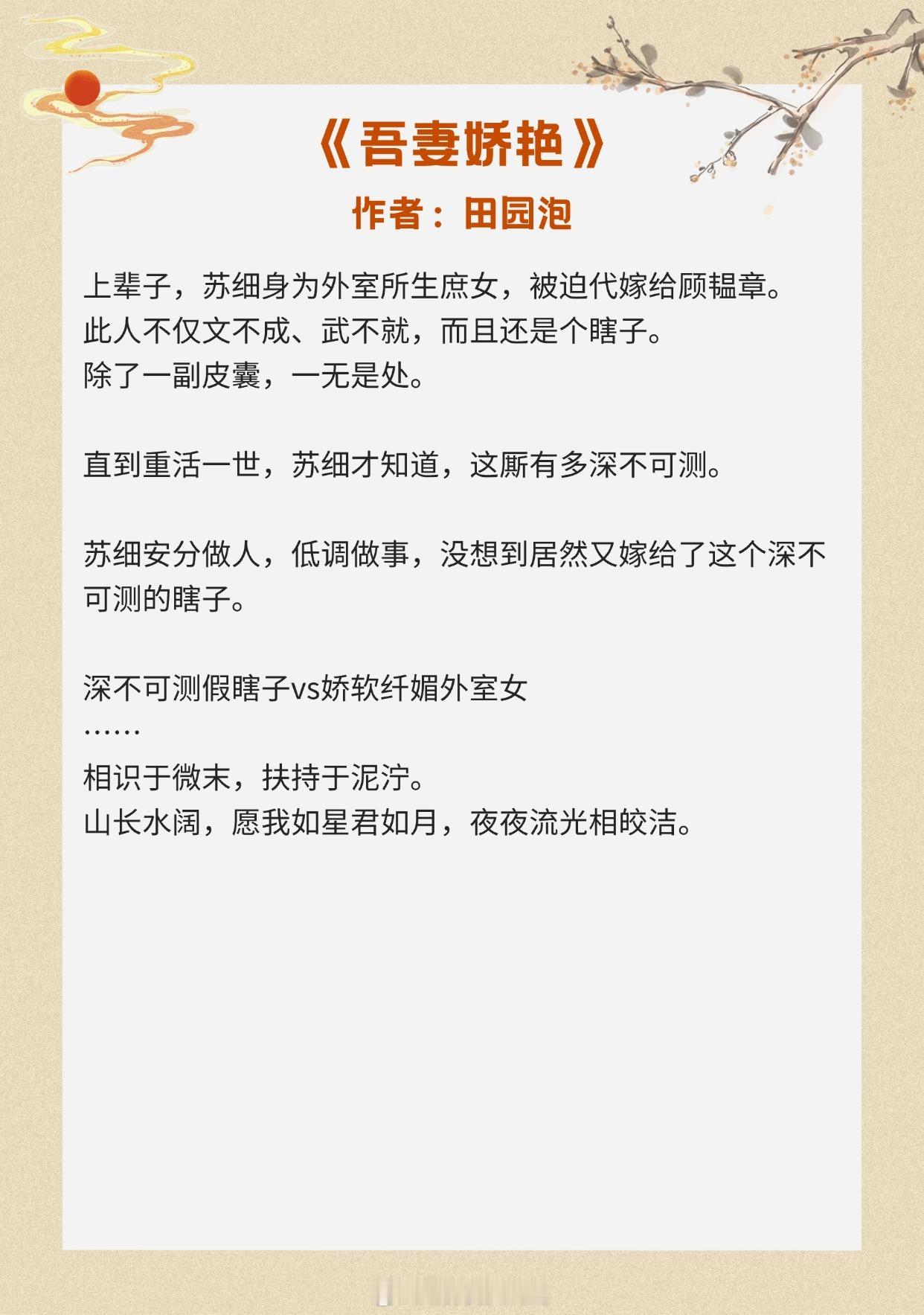我女扮男装撩了裴公子6次,他次次都躲我如避蛇蝎。
第6次,我翻墙夜访,想给他最后一击。
却听见他在祠堂里,对着他祖父一字一句地发誓:
“孙儿断袖,此生不渝!”
老镇国公气笑了,一棍子砸在他背上:“人家是个姑娘!”
01
我被谢淮堵在自家大门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门檐下挂着的灯笼刚刚被小厮点燃,昏黄的光晕落在他月白色的衣袍上,氤氲开一片温软模糊的影子。
他站得笔直,像一棵风雨里也纹丝不动的青竹,可眼底那片浓重的青黑却泄露了他同样彻夜未眠的秘密。
听见我出来的脚步声,他猛地抬起了头,目光像带着实质的钩子,一下子就把我钉在了原地,让我连脸上那早就练习好的玩世不恭的笑容都差点挂不住。
“容兄。”
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粗砺的砂石狠狠打磨过,透着一股筋疲力尽的味道。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折扇却“唰”地展开,故意摇得漫不经心,抢先开了口,试图把主动权抓回自己手里。
“哟,谢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在我这侯府门口站了快一天,是打算给我们家当新门神,还是昨天诗会上被我逗得没过瘾,特意找上门来求我继续?”
谢淮没有像往常那样被我轻佻的话语激得面红耳赤或者拂袖而去,他只是静静地,一步一步地朝我走过来。
他身上那股极淡的、像是松针混着初雪的书墨冷香,随着晚风幽幽地钻进了我的鼻子。
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仅仅一步,近得我能看清他眼白里纵横交错的血丝,和他紧紧抿着的、有些苍白的嘴唇。
“容兄。”他又叫了我一声,这次声音里压着一种让我心慌的急切和笃定,“昨夜,镇国公府祠堂外面……”
来了!我心里警铃大作,面上却把眼睛瞪得更圆,摆手摆得差点把扇子甩出去,声音拔高,充满了刻意的惊讶和不解。
“祠堂?什么祠堂?谢兄你可别吓我,你们家那摆着祖宗牌位的庄严地方,我跑过去干什么?偷香火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努力让自己的笑声听起来自然又没心没肺。
“我昨晚睡得可沉了,雷打不动!谢兄你肯定是读书太用功,眼神恍惚看错人啦!”
谢淮的目光没有半分动摇,像深潭一样锁着我,根本不理睬我蹩脚的表演。
他的视线微微下移,落在我因为紧张而微微握紧的手上,然后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戳穿了我的谎言。
“那坛被打碎的酒,是窖藏了二十年的女儿红,香气独特得很,整个A市也找不出几坛。”
02
我的笑容彻底僵在了脸上,脑子里“嗡”的一声,昨夜那声清脆刺耳的碎裂声仿佛又在耳边炸开。
是了,我昨晚慌得六神无主,只顾着没命地逃跑,怀里那坛原本想用来“赔礼”兼“逗弄”他的上好女儿红,早就在祠堂窗下摔得粉身碎骨,浓烈的酒香恐怕瞬间就弥漫了整个角落。
谢淮怎么可能闻不到?他又不是傻子。
昨夜……
我穿着一身便于行动的深色衣裳,怀里揣着他白天掉落的玉佩,手里拎着那坛沉甸甸的女儿红,像个真正的梁上君子一样,蹲在镇国公府那高耸的围墙底下。
心跳得有点快,不仅仅是因为要做翻墙越户这种勾当,更因为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的、隐隐的期待和兴奋。
翻墙对我来说轻车熟路,谢淮那个规整得过分、无趣得冒泡的院子我也不是第一次来“观光”。
可这次,他房里黑漆漆的,空无一人。
我正觉得纳闷又有点莫名的失落,一阵压低的呵斥声就顺着夜风飘了过来。
我鬼使神差地循着声音摸到了祠堂外面,躲在了东侧的窗户底下。
祠堂里灯火通明,谢淮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素色中衣,背脊挺得笔直,跪在冰冷的地砖上。
他祖父,那位以威严著称的老镇国公,手持一根看起来就分量不轻的蟠龙棍,脸色铁青,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孽障!你还要糊涂到几时?那容家的小子……”
“祖父!”
谢淮猛地出声打断,声音嘶哑却异常决绝,紧接着重重一个头磕在地上。
“孙儿……孙儿无法违背自己的本心!”
他抬起头,额上一片刺目的红。
“求祖父成全!”
“成全?成全你什么?”老国公的声音气得发颤。
谢淮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声道:“孙儿愿终身不娶!只求祖父……莫要再逼孙儿断、断这份……这份龙阳之好!”
“龙阳之好”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劈进我的耳朵,把我震得魂飞魄散。
他……他对谁?难道是……
还没等我想明白,老国公的怒吼就如同火山般喷发了。
“我让你龙阳!我让你不娶!”
蟠龙棍带着风声砸在他清瘦的背上,发出一声让人牙酸的闷响,谢淮的身体向前一倾,却死死咬住牙,没吭一声。
老国公用棍子指着他的后背,痛心疾首又怒不可遏地吼出了那句让我魂飞魄散的话:“那容家小子根本就是个姑娘家!你眼睛是瞎了,心也跟着盲了吗?!”
“哐当——!”
我手里那坛女儿红,终于还是没能逃过坠落的命运,在青石板上炸开一片狼藉。
浓烈的酒香瞬间弥漫开来。
“谁在外面?!”
老国公的厉喝和随之而来的杂乱脚步声让我瞬间清醒,我什么也顾不上了,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字——跑!
03
我几乎是连滚爬爬地逃回了永宁侯府,心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后背惊出了一层冷汗,被夜风一吹,冰凉。
整整一夜,我瞪着头顶的帐子,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终身不娶”、“龙阳之好”、“姑娘家”……像魔咒一样循环播放。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睡过去,却梦见谢淮提着那根蟠龙棍,面无表情地追着我跑了十八条街。
醒来时,日头已经老高,我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瘫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感觉全身的骨头都被抽走了。
小丫鬟夏荷小心翼翼地端来我爱吃的点心,我也只是恹恹地瞥了一眼,毫无胃口。
我哥容长清摇着扇子溜达进来,一看我这副样子,就笑得见牙不见眼,活像偷吃了十只鸡的狐狸。
“啧啧啧,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容小爷,这是怎么了?听说谢家那位玉树临风的谢公子一早就堵在咱们府门口,指名道姓要见你,你却躲在家里装鹌鹑?”
他把脸凑到我面前,挤眉弄眼。
“快跟哥哥说说,是不是终于玩过火了,把人家正经公子撩拨得狠了,人家现在找上门来,非要你给个名分不可?”
我抓起手边的软枕就砸了过去。
“滚!少在这里说风凉话!”
容长清轻松接住枕头,笑得更欢了。
“让我猜猜,你昨晚是不是又干坏事去了?该不会是夜探香闺,结果探出问题了吧?”
我的心虚被他一眼看穿,顿时恼羞成怒。
“容长清!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今晚就往你被窝里塞一罐活蚂蚱!”
他大笑着躲开我胡乱砸过去的果子。
“行行行,我闭嘴。不过人家谢公子可是说了,见不到你,他今天就杵在咱们门口不走了。这份痴心,真是感天动地啊……”
容长清走了,我的烦躁却一点没减少。
阳光一点点西斜,把院中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
夏荷又跑进来,小声说:“小姐,谢公子还在门外站着呢,晌午都没动地方。”
黄昏时分,她再次来报,语气里都带了点不忍。
“小姐,谢公子还在那儿……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我知道,我不能再躲下去了。
再躲,明天全B市都会流传“永宁侯府容小爷始乱终弃,镇国公府谢公子痴情守候”的离谱话本了。
我把心一横,深吸了几口气,努力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下去,重新端起那副玩世不恭的纨绔架子,大步朝着府门口走去。
04
说起来,我和谢淮这莫名其妙的“纠葛”,还得从大半年前那次踏青游湖说起。
那是我第一次女扮男装溜出府去参加所谓的“文人雅集”,一身男装,一把折扇,自觉风流潇洒无人能及。
然后我就看到了谢淮。
他穿着一身淡青色的长衫,独自站在船头,看着远处的水面出神,侧脸的线条干净又清隽,和周围那些高谈阔论、争相吟诵的公子哥儿格格不入。
像一幅误入了喧嚣集市的水墨画。
鬼使神差地,我就凑了上去,用扇子敲了敲船舷。
“这位兄台,独自赏景多无趣,不如一起喝一杯?”
他转过头,看清我的样子后明显愣了一下,随即微微颔首,礼数周全却疏离。
“在下谢淮。兄台好意心领,只是不善饮酒。”
声音清清冷冷的,像山涧里的泉水。
我却来了劲,越是这般一本正经、难以靠近,我就越想撕破他那层平静的伪装。
那之后,我便“偶遇”了他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昨天的诗会,是第六次。
诗会总是那些调调,我懒洋洋地靠在亭柱上,目光逡巡,果然又在池塘边看到了那抹月白身影。
他正往池子里撒鱼食,修长的手指捻着细碎的饵料,神情专注,仿佛周遭的欢声笑语、诗词唱和都与他无关。
我整理了一下衣襟,摇着扇子晃了过去。
“谢兄,好巧啊。”我用扇骨敲了敲他身侧的栏杆,“又在这里躲清静?可怜满园芳心,又要碎一地咯。”
他的手顿住了。
我满意地看着那抹熟悉的薄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白皙的脖颈蔓延到耳尖。
他转过身,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后挪了半步。
“容……容兄。”
“嗯?”我故意拖长了调子,又逼近半步,展开扇子朝他脸上扇了扇风。
“谢兄每次见了我,都跟见了洪水猛兽似的,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小弟我可真要伤心了。”
他终于抬眼看向我,那双总是平静无波的眼眸里,此刻盛满了显而易见的慌乱,甚至还有一丝……无奈?
“容兄,请……自重。”
“自重?”我挑眉笑了,手腕一转,合拢的扇子就挑向他的下巴。
“我容小爷的字典里,可没这两个字。”
我的目光扫过他染了霞色的俊逸脸庞,戏谑的话脱口而出。
“谢兄这般品貌,若是个女儿身,我容昭必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把你风风光光迎进门。”
这话我说得坦荡又无赖。
谢淮猛地偏头躲开我的扇子,连眼尾都泛起了红,语气里带上了明显的愠怒和羞窘。
“容兄莫要再胡言!此等玩笑,万万开不得!”
他那副又羞又恼、束手无策的样子,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幼鹿,莫名地取悦了我,让我心里那点欺负人的念头更盛。
我大笑着转身离开,没走几步,就听见身后一声轻微的脆响。
回头一看,是他随身佩戴的那枚羊脂玉佩,掉在了地上,青色的穗子散开。
我走回去捡起来,玉佩触手温润。
揣着这块玉佩,我忽然觉得,晚上去“还”玉佩,顺便再“逗逗”他,是个绝妙的主意。
05
“那香气独特的女儿红,是我及笄那年,父亲亲手埋在后院槐树下的。”
谢淮的声音把我从回忆和昨夜的惊惶中拉了回来,他的目光沉静而专注,仿佛早已看透我所有强撑的伪装。
“他说,要等到我出嫁之日再启封。”
我的喉咙发紧,想反驳,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谢淮又往前走了一小步,我们之间的距离近得几乎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他缓缓抬起一直垂在身侧的另一只手,掌心向上摊开。
那枚我昨夜仓皇逃跑时不知掉落在何处的、坠着绯色流苏的扇坠,正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里,被灯笼的光照得泛着柔润的光泽。
“祠堂窗下,不止有酒香。”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地敲在我的耳膜上。
“你跑开的时候,太急了,踩断了我窗外那株桃树新发的枝桠。”
他的目光深邃,里面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有疲惫,有无奈,或许还有一丝极淡的、让我心跳失衡的温柔。
“容兄。”
他最后这样叫我,尾音轻轻落下,却带着千钧的重量。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