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早春,洛阳城里的夜风仍带寒意。二十四集团军司令部昏黄的油灯下,少校秘书赵荣声在整理当天收到的延安书报。没人会想到,这名穿着国民党军装、行走于大小会议之间的青年,其真实身份早在1936年便已写进中共中央的机要档案。
时间回溯到1938年1月31日。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晋西前线采访,赵荣声随团抵达马牧村。当天恰逢卫立煌来向朱德拜年,双方寒暄之后举行欢迎会。赵荣声撰写的《西线上的一个盛会》刊发到《群众》周刊,卫立煌读后大为惊讶:“这笔头,正是我需要的人。”一句感慨,成了他与赵荣声长达十年共事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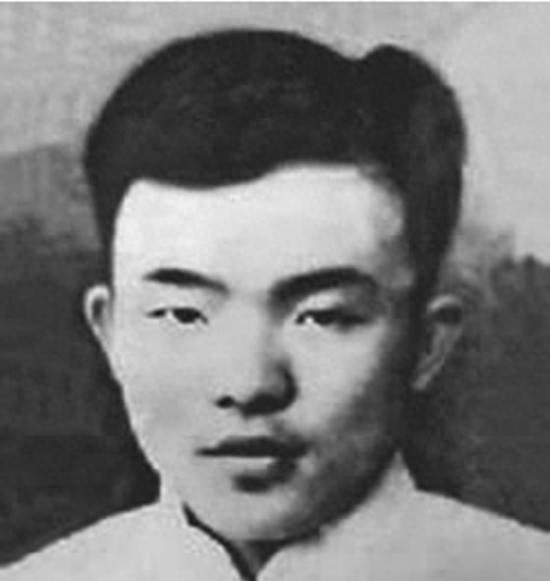
接到傅钟的指示后,赵荣声以“民族先锋队员”身份接受卫立煌延聘,2月下旬来到霍县司令部。第一次深夜谈话里,卫立煌打开话匣:“我想仿照八路军办战地工作团,你看行不行?”赵荣声顺势递上分析,既表明抗日立场,又避免暴露党员身份。两人谈到天亮,气氛意外融洽。
韩信岭失利后,部队筹划西移。赵荣声建议“假道延安”,卫立煌迟疑,却还是采纳。4月17日的延安之行,毛泽东、周恩来接待卫立煌,分析华北局势、点明国共协作的必然。抗大欢迎会上,卫立煌脱稿演讲,用朴素话语诉说合作抗日的决心,这场意外的即席演说在司令部内被视作态度转折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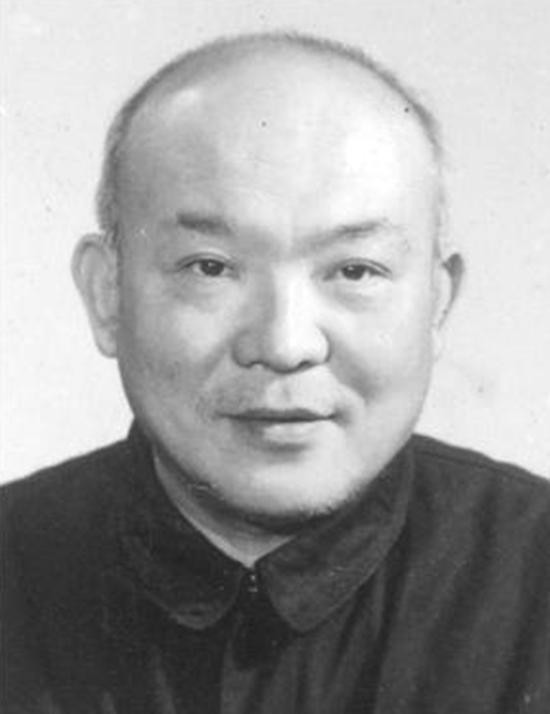
离开延安后,卫立煌在西安签发百万发步枪子弹、二十五万枚手榴弹支援八路军。兵站分监杲海澜因顾虑中央军禁令拖延发放,赵荣声一面通过“拖字诀”稳住卫立煌情绪,一面向林伯渠通报。林老一句“夜长梦多,必须办成”让赵荣声下定决心施压。数日后,弹药与罐头分批运抵晋察冀前线,成为前方急需的火力补给。
赵荣声借秘书之便,每周为卫立煌口述《新华日报》《解放》周刊要闻。口语化的讲解配合事实对比,让这位嫡系将领对延安政策逐渐产生好感。夜深时,他常端着雪茄反复追问:“日本真这么快就打不动了吗?”赵荣声用战例和数字回应,既满足好奇,又潜移默化削弱“攘外必先安内”的成见。
1940年初,中条山阵地告急,司令部撤往灵宝。山路颠簸,卫立煌独处车厢,突然发问:“倘若我加入共产党,是否更能救国?”一句话让赵荣声心口一紧。他稳住语气:“此事非同小可,可否请示林伯渠?”对方爽快掏出百元大洋:“烦你跑一趟。”这段简短对话,是十年潜伏中最反常的瞬间,也成为后来无数史家争论的悬案。

赵荣声携密信抵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听完经过,沉吟片刻,只留下八个字:“做真正的革命国民党员。”带着这个回应,赵荣声回到灵宝。卫立煌默默点头,没有再提入党之事,却在随后数次战役里,坚持按比例为第十八集团军提供弹药、粮秣,做法较多数中央军将领更为积极。
1943年至1945年,赵荣声用“军务忙碌”作掩护,向中共中央华中局传递情报三十余次,内容包括豫西公路修筑、兵站调拨、粮草储备等关键细节。每一次递送,他都需步行穿越封锁线数十里,风险极高,但成效显著——我军对二十四集团军的后勤动向了然于胸。
抗战胜利后,内战阴云再起。蒋介石令卫立煌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赴沈阳组建东北保安司令部。赵荣声并未随行,而是在1945年底奉命转至南京“中央训练团”暗线,监控“整军备战”动向。10年之间,他的潜伏身份始终未被识破,连最亲近的郭寄峤也只当他是“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安徽才子”。

1949年1月,平津战役宣告结束,华北大势已定。赵荣声结束秘线任务,改道天津向中共华北局报到。短短几天后,傅钟发来简讯:“长期任务完成,立即调往新政务院筹备组。”自此,这位燕大学子从“红色卧底”转身成为新中国行政体系的早期骨干。
回望这段历程,赵荣声之所以能在卫立煌身边坚持整整十年,一靠过硬的政治素质,二靠不露锋芒的处世技巧,更靠那股“写出来”的本领——文稿、日记、报告,既是工作需要,也成了与对方沟通桥梁。至于卫立煌当年那句“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是真情流露还是探口气,史料仍在散见。可以确认的是,他在关键时刻为八路军提供的枪炮补给,确实挽救过无数前线官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