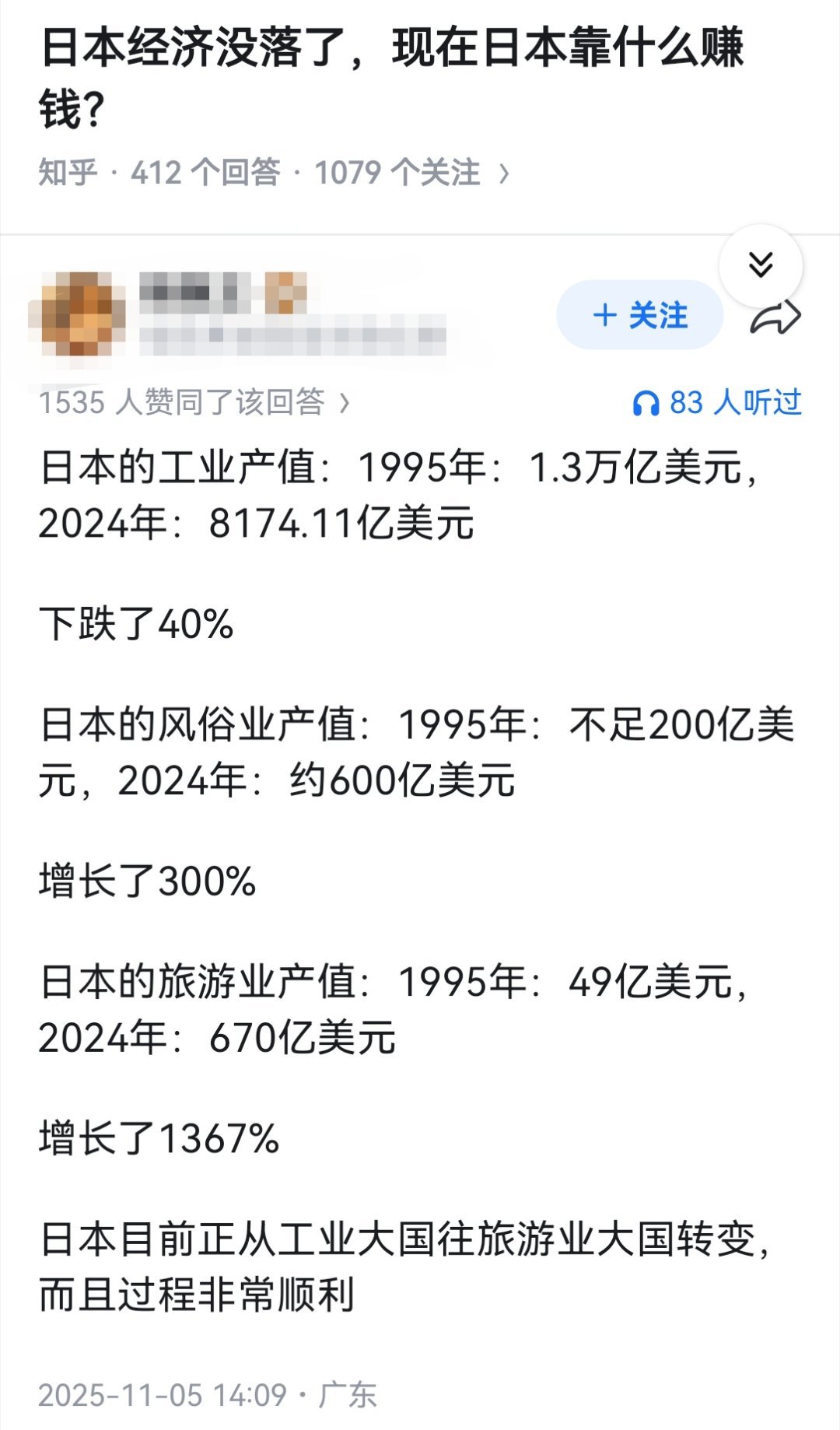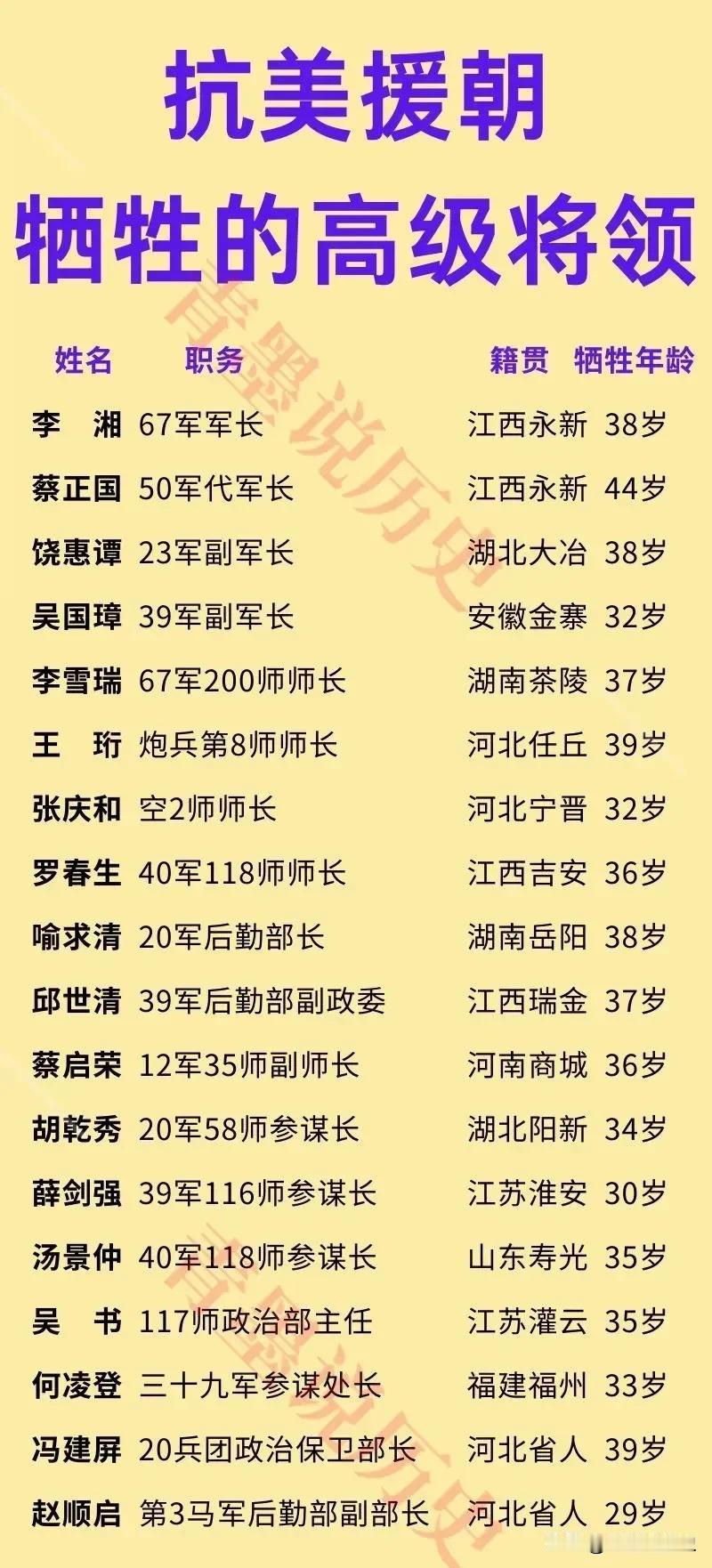1951 年深冬,朝鲜半岛的盖马高原上。
志愿军运输排的卡车陷进雪窝,无法前行,又突然遭到美国空军轰炸。
“卧倒!”20 岁的张荣清扑向身旁的新兵,爆炸的火焰窜起来。
他从燃烧的车厢里拖出三具战友遗体,左腿的伤口又裂了,血渗过绷带。
他仍然咬着牙,把志愿军遗体拖回我军阵地。
因为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张荣清受到了部队的嘉奖。
没人知道是,这个操着东北口音的战士,户口本上该写的却是 “日本福冈”。
为什么日本人会出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这一切,都与他的父亲有关。
1937 年,卢沟桥的枪声炸响时,他还是砂原惠,刚满 5 岁。
父亲拎着皮箱,母亲抱着他,挤在开往满洲的船里。
“去奉天,找好日子。” 父亲说。
那时的奉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烟囱插在天上,铁轨像毒蛇,缠着东北的土地。
他们住的日式住宅区,围着铁丝网。
每天清晨,他要对着东方鞠躬,背《教育敕语》。
老师说:“你们是大和民族的骄子,要帮天皇开拓疆土。”
可他总偷偷趴在铁丝网上看 ——中国劳工扛着钢轨,背上的血痕结了痂,监工的皮鞭抽下去,能听见骨头响。
火车站台边,饥民啃着树皮,孩子哭着要饭,日本宪兵一脚踹过去,孩子滚在泥里。
他问母亲:“为什么他们那么苦?”
母亲捂他的嘴:“别问,会被杀头的。”
那时他不懂,所谓 “开拓疆土”,是把别人的家,拆成自己的战场。
1945 年 8 月,砂原惠迎来人生的一次大挫折。
父亲咳着血,躺在病床上,收音机里的日语断断续续:“本土遭空袭,天皇陛下宣布……”没等说完,父亲断了气。
母亲拽着他和弟弟,挤上开往大连的火车。
满洲国垮了,货币成了废纸。
大连码头挤满日本侨民,船票炒到天价。
他们攥着空口袋,站在码头上哭。“回不去了。”
母亲说。他们流落到辽宁北镇,一个小村子。母亲给地主做针线活,一天挣半个窝头。
13 岁的他,只得去地主家当猪倌。
天不亮就起床,去河滩割猪草,冬天的河水冰碴子割脚,他得光着脚踩进去。
有次猪跑了,地主拿棍子抽他,后背的血印子半个月没消。
他躲在猪圈里哭,听见外面枪响 —— 国民党兵闯进村子,把不交粮的农民吊在老槐树上,皮鞭抽得肉溅出来。农民的孩子跪在地上求,兵一脚把孩子踹进泥坑。
那天晚上,他抱着小猪,第一次恨 “日本人” 这三个字。
如果不是日本打过来,他不会有家不能回;如果不是战争,中国人也不会这么苦。
1946 年,村里来了穿灰布军装的人。
他们不抢东西,还帮老百姓挑水。
有个连长看见他冻得流脓的脚,蹲下来,把自己的布鞋脱给他:“孩子,别冻着。”
那鞋还带着体温,他穿在脚上,暖到心里。
连长说:“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是老百姓的兵。”
他不懂什么是 “民主联军”,但他知道,这些人不打人,不骂人,还给人饭吃。
1948 年,土改的消息传到村里。工作队的人说:“雇农分地,地主的地要还给老百姓。”
他家被划为雇农,分到 37 亩地,还有一头黄牛。
土地证递到他手里时,他看见上面写着 “张荣清”—— 这是工作队帮他起的中国名字。
他跪在地上,对着土地磕了三个头。
泥土的香味钻进鼻子,他突然哭了:这辈子,终于有自己的地了。
工作队的人说:“是共产党让你有地种,是解放军保护你。”
那天晚上,他找到连长:“我要参军,我要当解放军。”
连长看着他:“你还小。”
他拍着胸脯:“我能扛枪,能打仗,我是中国人!”
其实他没说,他怕哪天再有人把地抢走,怕再有人欺负老百姓。
他想保护这份 “有地种” 的日子,想做个能保护别人的人。
1948 年 10 月,锦州攻坚战打响。
他成了侦察兵,化装成小贩,挑着担子进市区。
国民党哨兵拦住他:“干什么的?”他操着东北话:“卖糖的,老总尝尝?”
哨兵拿了块糖,没多问。
他趁机摸遍敌军的火力点,把位置画在烟盒纸上。
晚上摸出城时,被巡逻兵发现。
他跑过小巷,子弹在耳边飞。
跳进护城河时,冻得牙齿打颤,可手里的烟盒纸,攥得死死的。
当他把地图交给营长时,营长拍着他的肩:“好样的,小张!”“小张”—— 这两个字,比任何奖励都让他开心。
他终于不是 “日本侨民砂原惠”,是 “解放军张荣清”。
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又跟着部队打平津。
丰台火车站的弹药库,国民党军守得严。
他带着突击小组,夜里摸进去,用炸药包炸门。
导火索 “滋滋” 响,他看见敌军的探照灯扫过来,一把推开战友:“快撤!”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出去,胳膊被弹片划开一道口子。
他爬起来,看见弹药库的火映红了天,笑着晕了过去。
醒来时,指导员给他颁奖章:“张荣清同志,立三等功!”
他摸着奖章,心里想:以后,要立更大的功,要保护更多人。1950 年 10 月,鸭绿江边的树叶落尽了。
部队接到命令:入朝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
报名时,表格上有 “国籍” 一栏。他盯着那两个字,手有点抖。
指导员说:“外籍人员不能入朝,这是规定。”
他想起锦州的战友,想起北镇的老乡,想起那些在雪地里牺牲的人。
他拿起笔,在 “国籍” 后面,写下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