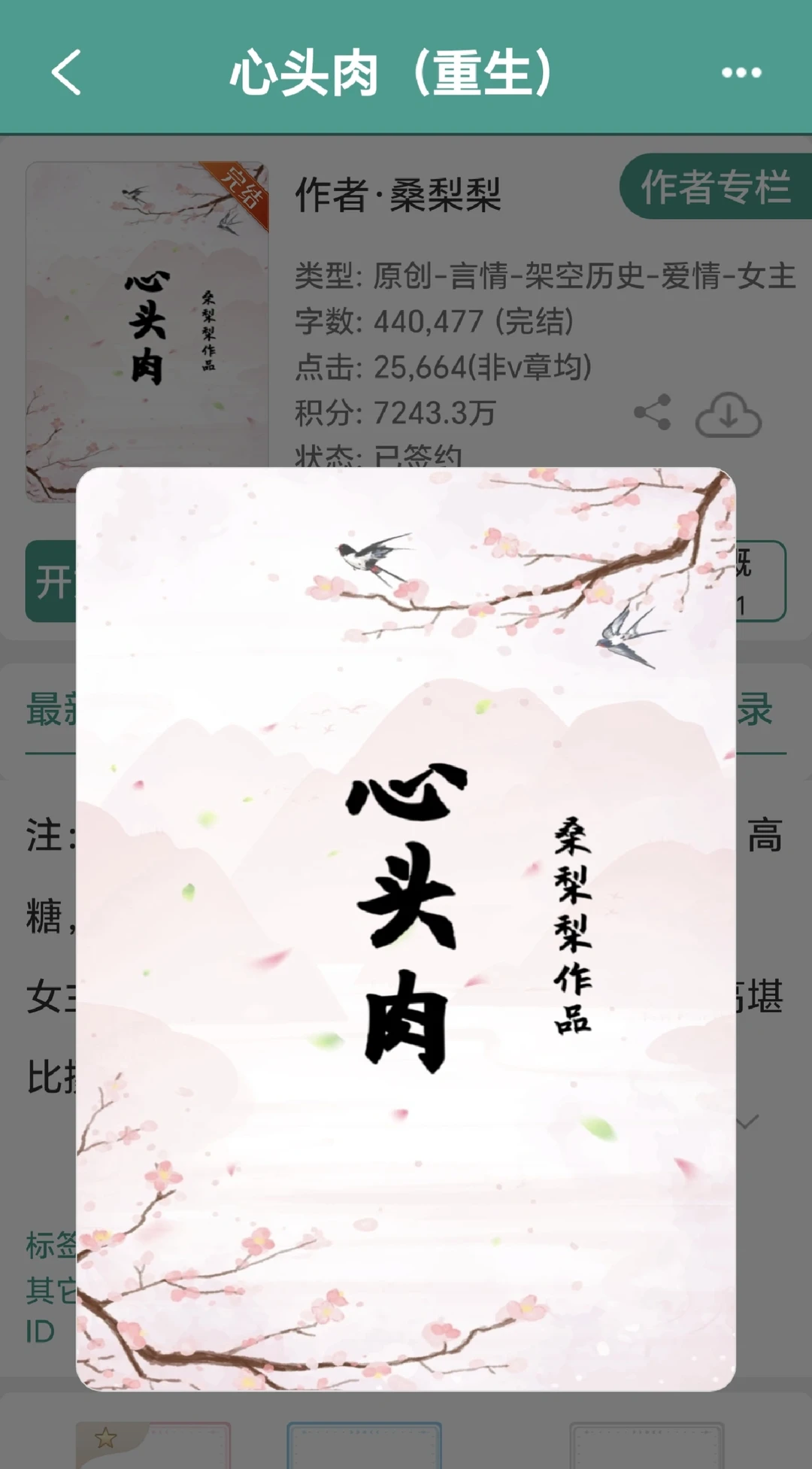六年前,女知青沈怡棠考上大学,嫁给教授的儿子后,
她用二十块钱买断了我们的婚姻。
再见面,她带着新婚丈夫走进我的面馆。
见到她的着装,我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
我平静的为她端上,曾为她做过数不清的阳春面,
她看见墙上的全家福时手在抖,吃面时眼泪掉进碗里。
当儿子说出年龄时,她打碎了面碗,脸色惨白。
多可笑。
当年她娘把我推出门,说“沈家只要教授儿子做女婿”;
如今她功成名就,却在我面前崩溃。
1
北城的雨季,黏腻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
诚诚在堂屋里跳皮筋,满头是汗。
我放下手里的账本,拿了块干毛巾走过去给他细细擦着脖颈。
这时,木门却突然被推开了一道缝。
风裹着雨,灌了进来。
我下意识地眯了眯眼。
现在是晚上九点。
镇上的人睡得早,这个点,平时街上连条狗都看不见。
我抬头,却看见一个男人。
他身上披着部队那种老旧的军绿色雨披,雨水顺着边角滴滴答答地往下淌。
他侧着身,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个怀着孕的女人进来。
我站起身,脸上的微笑客气又疏离。
“不好意思啊两位,我们快打烊了。”
男人扶着妻子在离门最近的桌边坐下,她丈夫缓了一口气,这才带着北城独有的嗓音开口:
“老板,实在对不住。”
“我们回来探亲,车在路上抛了锚,走了半天才到镇上,现在只有你这一家店还亮着灯。”
“我……我怀着孩子,折腾一天,还没吃上口热饭。”
她的声音。
很熟悉。
熟悉到我的心脏瞬间漏跳了一拍。
这时女人也脱下雨披,挂在门后的挂钩上。
雨披底下,是最时兴的毛呢大衣,一看就价值不菲。
她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
直到她抬起正脸。
沈怡棠。
我如遭雷击,好似四肢百骸都僵住。
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也骤然凝固。
那双曾经含着星辰大海的眼睛里,先是错愕,然后是震惊,最后是无法掩饰的……狼狈。
我们就这样隔着三米的距离,对望着。
“怡棠?”
她身边的男人先开了口,声音温柔。
他顺着沈怡棠的视线看向我,眼中带着一丝不解,但还是礼貌地笑了笑。
然后他轻轻吸了吸鼻子,对沈怡棠说。
“这面闻着,好香啊。”
一句话,将我从地狱拉回人间。
我垂下眼,避开沈怡棠的视线,浓密的睫毛遮住眼底所有的情绪。
指甲虽然陷进了掌心,但我感觉不到疼。
我开口:
“既然这样,那稍等。”
“我去做两碗阳春面。”
男人温柔地道谢:“谢谢您。”
我没应声,转身进了后厨。
灶膛里,封着的火还留着余温。
我添了两把柴,火苗“呼”地一下就窜了起来,
我舀水,下面,动作一气呵成,熟练得像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这双手,曾为她编过上千个竹筐。
也曾为她做过数不清的阳春面。
但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再见面时,她已经是这般有身份的人物了。
身边还有那个看起来就很有教养的丈夫。
他们才是一类人。
而我,是烂在泥里的。
2
那年高考刚恢复。
沈怡棠还是个刚给我生完孩子,在乡下的女知青,每天趴在四处漏雨的知青点里,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一遍遍地做着演算。
她说,子膺,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她说,我想考出去,我想出人头地。
可她娘不让,说一个女娃娃读什么书,考试报名要两块钱,买书要花钱,去县城的路费也要钱。
她说,家里没钱给你瞎折腾。
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吃饭。
是我跪在堂屋,求我爹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
是我没日没夜地点着灯熬着油,编竹筐,一个柳条一个柳条地给她换去县城的盘缠。
拿到钱的那天,她眼睛亮得惊人,她攥着我的手,在油灯下立誓。
“子膺,等我。”
“我沈怡棠若负你,永失所爱,天打雷劈。”
我送她去坐长途汽车进城。
临上车前,她眼眶通红的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最后往我手心里塞了一颗水果糖。
糖纸都快被她攥化了。他说:
“等我考上大学,就回来接你去北京。”
“子膺,等我。”
那颗糖,我含在嘴里,甜到了心里。
我等了。
可我等来的,不是她接我去北京的信。
而是一封写着“我们不合适”的分手信。
还有她托人捎回来的二十块钱。
二十块。
买断了我的青春,我的爱,和我们的孩子。
如今,物是人非。
她成了人上人,身边有了温柔的丈夫,很快,还会有个可爱的孩子。
而我,只能守着这个小面馆,守着诚诚,守着北城这一方小小的天地。
锅里的水开了,咕噜咕噜地冒着泡。
我把面捞进碗里,撒上葱花,淋上猪油,香气瞬间就弥漫了整个后厨。
我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吐出。
胸口那股翻江倒海的窒息感,终于被我死死压了下去。
没什么。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
都过去了。
我端着面,转身,准备出去。
外面却突然传来诚诚清脆又好奇的声音,
“爹!”
“你快看!”
“这位阿姨,和咱们家全家福上面的那张照片,长得好像啊!”
沈怡棠的丈夫,闻声站了起来。
“是吗?让叔叔看看。”
他从诚诚手里接过那张已经泛黄的老旧相框。
只看了一眼,他就惊讶地笑了起来。
“哎呀,还真是!”
他举着相框,一头看看照片,一头看看沈怡棠。
“怡棠,你快看,真的好像啊!跟你像是亲姐妹一样。”
他开着玩笑。
“你老实说,是不是在老家还藏了个亲姐妹,没告诉我?”
照片上的人,和现在的沈怡棠有七分像。
可照片上的她,眼神清澈,带着一股子少年气,穿着我给她做的的确良衬衫,皮肤是常年下地干活晒出的麦色。
不像现在,保养得当。
只是神似罢了。
我快步走过去,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小孩子乱说话,别当真。”
我想把照片拿回来。
搪塞过去。
可那男人的手一转,相框已经递到了沈怡棠的面前。
她的手伸过来,接住了,指尖微微发着抖。
随即视线便像被钉子钉在了那张照片上,一动不动。
3
我只能扯出一个僵硬的笑。
“大概是长得像吧,天底下人有相似。”
“这上面的人,是我……表妹。”
男人“哦”了一声,似乎信了,注意力很快被我刚端出来的阳春面吸引了过去。
“好香啊,我快饿死了。”
我稍稍松了口气。
这张照片。
是当年她临走前,拉着我,还有我爹娘,一起去镇上照相馆照的。
我爹娘在世时,待她像亲儿子。
她说,等她回来,我们就把这张照片挂在新房里。
照一张相片要一块五,差不多是我家半个月的嚼用。
我爹娘走后,我就只有这一张“全家福”可以睹物思人了。
我伸出手,从她僵硬的指节间,轻轻将相框抽了回来。
声音又冷又平。
“小姐,还给我吧。”
“一张老照片,没什么好看的。”
沈怡棠像是被我的声音惊醒,猛地回过神。
她抬起头,眼睛里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声音也沙哑得厉害。
“照片上那两位老人家,他们……还在吗?”
我垂下眼,将相框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
“过世两年了。”
沈怡棠的眼眶,“刷”地一下就红了。
她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什么,却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怡棠,快吃面呀,都要坨了。”
她丈夫温柔地催促着。
沈怡棠应了一声“好”。
她拿起筷子,夹起一小撮面,轻轻吹了吹,送进嘴里。
然后,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极轻地呢喃了一句。
“真好吃。”
“味道……一点都没变。”
就在这时,诚诚歪着头,一脸天真地看着她。
“阿姨,你怎么哭了?”
一句话,像惊雷。
她丈夫紧张地看向她:“怡棠,你怎么了?”
我也愣住了。
沈怡棠整个人慌乱不堪,她仓促地抬手抹了下眼睛。
“没,没事。”
她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刚刚在外面,风太大,迷了眼,一直忍到现在才觉得难受。”
“我看看,快让我给你吹吹。”
她丈夫一脸心疼,就要起身。
“不用!”
沈怡棠猛地摆手,她悄悄地,极快地看了我一眼,又飞速移开。
“已经好了,真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狼狈的侧脸,在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沈怡棠。
这么多年了。
我连恨都觉得累了,早就放下了。
你现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做这番姿态,又是给谁看呢?
何况。
当年是你先负了我。
4
沈怡棠走的那年,我们的孩子才满月。
乡下人都结婚早,但扯证晚。但我们既已有了事实,便就是夫妻。
我爹娘更是把家里最后一点积蓄都拿了出来,托人给她捎去,怕她在省城吃苦。
我以为,等她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可我没等来她的人,只等来了她娘的冷脸。
冬至那天,北城下了第一场雪。
我抱着刚满月的诚诚,被她娘推出了沈家大门。
“滚!我们沈家,要出大学生!出城里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想扒着我们怡棠不放!”
我娘买给她的那台崭新“飞人”牌缝纫机,被她从屋里拖出来,“哐当”一声,砸在我脚边。
零件碎了一地。
她指着我的鼻子,一字一句,淬着冰。
“沈怡棠要嫁给教授的儿子了!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不信。
我不信那个说着要带我孩子去城里,回来要和我爹娘一起拍新全家福的女人,会这样对我。
我把诚诚放在我爹娘那里,发了疯似的扒上村里去镇上的拖拉机,又从镇上挤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
两天一夜。
我终于站在了她大学的门口。
学校门口,最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大红的喜报。
红纸,黑字。
却刺得我眼睛生疼。
【热烈祝贺我校沈怡棠同志参与研发的‘丰收二号’农用机荣获省级科技进步奖……】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
在喜报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
写着她即将和本校谢教授的独子订婚,欢迎同学们届时前去喝喜酒。
我看着那张喜报,脑子里“嗡”的一声。
天,塌了。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省城的大街上,街上人来人往,喇叭声、叫卖声,都离我很远。
然后,我看见了沈怡棠。
就在街对面的百货商店门口。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碎花红裙子,头发烫着卷,正笑着,从一辆小汽车上下来。
而她的身边,是一位器宇轩昂,很有学时的男人。
我急忙躲在供销社的廊檐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
我听见有人路过他们身边,笑着恭贺。
“谢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啊!”
“怡棠,你可真有福气。”
她笑着,谦虚地回应着什么。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刀子,捅进我的心窝。
我再也站不住,把头埋进膝盖里,捂嘴痛哭起来。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
她不要我了。
也不要我们的儿子了。
我当天就回了老家。
我爹娘知道后,气得浑身发抖。
我爹抄起扁担,眼睛通红。
“我就是爬,也要爬到省城去,问问她沈怡棠,是不是没有王法了!”
我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她的腿。
“爹,娘,我求你们了。”
“别去。”
“她好不容易才考出去,我们不能毁了她。”
“算我求你们了。”
纵然她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我还是……舍不得。
我爹最后把扁担狠狠砸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爹娘因为这事,生了一场大气,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
直到两年前,他们前后脚走了。
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对不起我。
说当年要是狠心一点,不同意我跟她好,我也不会一个人带着诚诚,过得这么凄苦。
他们到死,都没能闭上眼。
想到爹娘,我鼻尖一通发酸,刚想转身去后厨平复一下情绪。
堂屋里,却传来了沈怡棠的声音。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连她自己都未察觉的小心翼翼。
“小朋友,你……你今年多大了?”
我心里猛地一沉,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下意识地就要冲出去,想随便找个借口打断他们。
可是晚了。
只听见诚诚清脆的,带着童稚的声音在小小的店堂里响起。
“六岁啦!”
“阿姨,我属虎的!”
“哐啷!”
一声巨响。
是瓷碗掉在水泥地上的声音。
沈怡棠的丈夫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
“怡棠!你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