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翠柏间,杨振宁先生安卧其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五星红旗。遗体正前方,夫人翁帆和子女敬献的花篮缎带上写着:“我们永远怀念您”。
北京,秋风萧萧。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外,老早排起了百米长队。人们手里攥着白菊,脸绷得紧紧的。
人群中,那个穿黑衣服的瘦身影,看着就让人心里一酸。

那是翁帆。一身立领黑外套,背挺得笔直,可浑身都透着累和难过。露在外头的眼睛“肿得快睁不开了”,眼尾红得吓人。
有人远远看见她抬手擦眼泪,指尖都在抖。
最后的送别告别仪式现场,翁帆站在亲属队列的第一位。黑色大衣穿在她身上显得宽松,很明显的消瘦了。
签到的时候,她拿笔的手顿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写下自己的名字。有人上前劝她,她就哑着嗓子说句“谢谢”,声音轻得风一吹就没影。
杨振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为沉痛悼念这位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清华大学全体校领导、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送别。
哀乐低回。杨振宁先生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五星红旗。
礼堂内,翁帆同前来吊唁的来宾握手致谢。安静的大厅内,只有一声声“保重”和低低的啜泣声。
家人的身影在送别现场,翁帆的母亲也出席了。这位76岁的老人前来送别女婿最后一程,整个人看起来沧桑了不少。
记得多年前,翁帆一家曾与杨振宁合照过,当时的翁母还很年轻。岁月流逝,如今的她站在告别厅里,内心想必复杂万分。
杨振宁的胞弟年逾九旬的杨振汉连夜从上海赶来,见兄长最后一面。他回忆起10年前的一次相聚,兄弟俩说了好多话,杨振宁谈起中国那些年的巨大变化,“他说中国是真正看到曙光了”。

从2004年结婚到2025年,28岁到49岁,翁帆与杨振宁相伴走过了21个年头。
这段婚姻开始时,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嫁给了一位迟暮之年的耄耋老人,颠覆了全中国人民的认知。网上骂声一片,说啥的都有。
面对外界的质疑,翁帆几乎没发表过任何表态。她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陪伴杨振宁上。
日常生活的点滴里,全是情分。杨振宁走到哪儿都爱给翁帆拍照,照片背面密密麻麻写着哪天在哪拍的,攒了好几本。翁帆就跟着他,他90岁后腿脚不利索,她天天扶着他在华园里慢慢走。
茶水晾到不烫嘴才端给他,书房里的手稿整理得整整齐齐。
彼此的礼物杨振宁曾深情地说,翁帆是“上帝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
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进一步阐释:“一个人到了80多岁,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
对于这份跨越54岁年龄差的感情,翁帆有自己的理解。当被问到如何区分爱和崇拜时,她坦诚地回答:“你要知道,当一个你崇拜的男人对你表达了喜欢或者爱的时候,你很易就爱上他了。”
她选择用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句子表达自己的心境:“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同。”
生命的终章在杨振宁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翁帆的陪伴更加精心。就在他走前一个月,杨振宁病危得说不出话,是翁帆找了块小白板,一笔一划写字帮他跟人沟通,陪着他到最后。
杨振宁的学生、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荟在告别仪式上几度哽咽:“杨先生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临终前,他最关心的仍是我们的科研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也表示:“先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祖国科技走到世界前列,我们一定会铭记教诲,让他的愿望早日变成现实。”
仪式结束后,翁帆捧着骨灰盒慢慢走出礼堂。太阳照着她,可看着还是冷冷的。
她一直低着头,护着骨灰盒的样子,跟护着啥稀世珍宝似的。
二十载相伴,从满是争议到安安稳稳过日子,翁帆在八宝山的眼泪,早把“陪伴”俩字刻进时光里了。
那些藏在照片、手稿里的温柔不会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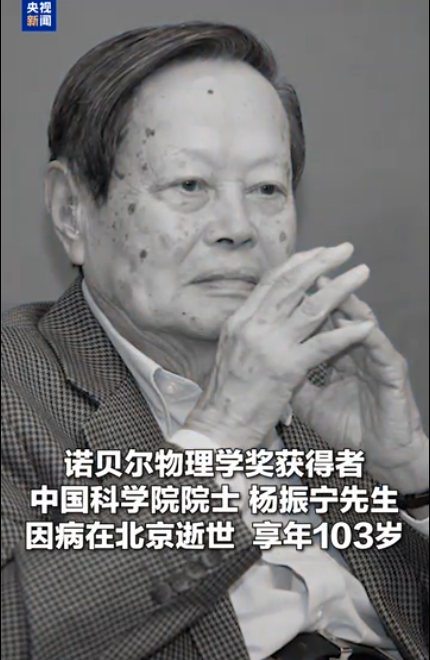
也许回了清华园的晚上,她还会像以前那样整理他的手稿,只是书房里再也没有那个坐那儿看报纸的人,再也没人给她拍照片记日子了。
我们总用世俗的眼光去评判别人的选择。
说年龄差太大的婚姻长不了,说年轻女子嫁给长者必定另有所图。可二十一年的陪伴,七千多个日夜的相守,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一颗真心吗?
真正的爱情,或许从来就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