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央视有个短发女主持,普通话很干净,早上六七点一开电视,经常能看到她,名字叫耿萨。
可真要说起她的出身,很多人会意外,一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甘肃牧区姑娘,能一路走到《朝闻天下》,靠的居然是父亲留下的一台旧收音机,还有她嘴皮子磨破也不停的那股劲儿。

耿萨是甘肃牧区的孩子,那一带马多牛多,人不多,说汉语的不多,大街上,羊圈边,炕头上,大家开口就是地方话,那种一听就知道是草原出来的腔调,说实话,什么普通话,对那时候的她来说,是很远的词。
她家在当地算条件不错,父亲是村里的干部,母亲是赤脚医生,父亲要参加会议,要写点材料,脑子转得比一般人快一点,母亲拎着药箱,半夜被人叫醒去看病也常有,在牧区,这样的家庭已经算“见过一点世面”,但跟城里比,又差一大截。
父亲有个很固定的小习惯,手里总揣着一台旧收音机,灰色塑料壳,天线一拉老长,音量调到屋里刚好能听清的程度,一拧开,就是一口她听不大懂的普通话,父亲会笑着说一句,这是汉话,城里人都这么说。

那会儿,她哪懂什么“标准音”这些词,她只觉得收音机里的人说话很顺,很干净和身边大人那种大嗓门的方言比,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她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刻,其实很简单,就是晚上挨着父亲坐,一起听广播里的新闻和故事。
有一次,她忍不住问父亲,城里到底什么样,父亲其实也没真见过多少,只能顺着她的想象往外描,有高楼,有车,有亮着灯牌子的街道,说着说着,他自己也笑,说反正跟咱这不一样,大概更热闹一点。
父亲去世,只剩一台收音机,她抓着当命根子这样的日子,其实没持续多久,十三岁那年,父亲突然生了重病,人就走了,来的快,走得也快,她还没反应过来,家里就一下子塌了一个角,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知道“再也见不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段时间,家里人来来回回忙,她反倒不太说话,别人惦记的是丧事怎么办,她盯着的,是父亲留下的那些小东西,能留下来的,说实话也不多,没有存多少钱,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最值钱的,居然就是那台天天响着的收音机。
从那天起,她就几乎每天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别人听广播,是打发时间,她有点不一样,她更像是借着这个声音,对父亲说一句,你别急着走太远,只要收音机还在,她就觉得,父亲好像还坐在屋里,只是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在说话。

父亲走后,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顶梁柱,压力都砸在母亲身上,母亲那点赤脚医生的收入,本来就不宽裕,现在要养一堆孩子,日子有多紧,她自己心里最清楚,也有人劝她改嫁,过个轻松点的后半辈子,可她看着几个没长大的娃,心一横,直接把这个念头掐掉了。
兄弟姐妹都挺懂事,谁能干活谁干活,能帮就帮,没人喊累,家里不太说那些“苦”字,但那种绷着劲过日子的感觉,空气里都是,就这样,耿萨在这种环境里,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都要听一段收音机里的汉语节目,几乎没断过。
对着收音机学普通话,嘴角裂开也没停过刚开始,她其实听不太懂新闻里在说什么,语速快,词又陌生,但她没打算只当背景音,她会一边听,一边小声地跟着念,念错了自己笑一下,再重来,嘴里那股牧区腔调改不掉,就一点点往回拽。
有时候,她站在窗边晾衣服,收音机放在小板凳上,一边抖衣服,一边跟着念新闻,冬天风刮得脸生疼,她嘴皮子是真的裂过,嘴角裂开一条小口子,说多两句就火辣辣的,她回屋抹点油,喝两口水,忍一忍,第二天还是照样开机学。

她心里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外面的世界,大概都这样说话吧,想出去走走,得先学会这套说话方式,没人给她立目标,也没人逼她练,其实哪天不学也没人管,可是她自己心里清楚,这事早晚有用,现在多花时间,后面也许能轻松一点。
时间一长,差别就出来了,牧区里很多同龄人,到初中都还听不太明白广播里的内容,有些词连个大概都猜不到,她呢,已经能大致听懂新闻里的意思,老师要她复述一段,她虽然说不出“专业表述”,但能把七八成说清楚。
后来她自己回想也说,如果不是当年那台收音机,如果那阵子她没那么坚持,很可能后面的人生,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这话听着有点玄,又挺实在,说白了,就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对自己做了一件很多大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坚持每天练,没人盯着也练。
考上甘南民族学校,她才发现自己这一口普通话是优势因为成绩一直不错,她后来考进了甘南民族学校,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折,从牧区到了一个集中读书的地方,人多了,声音也杂了,她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原来各种说话方式混在一起,是这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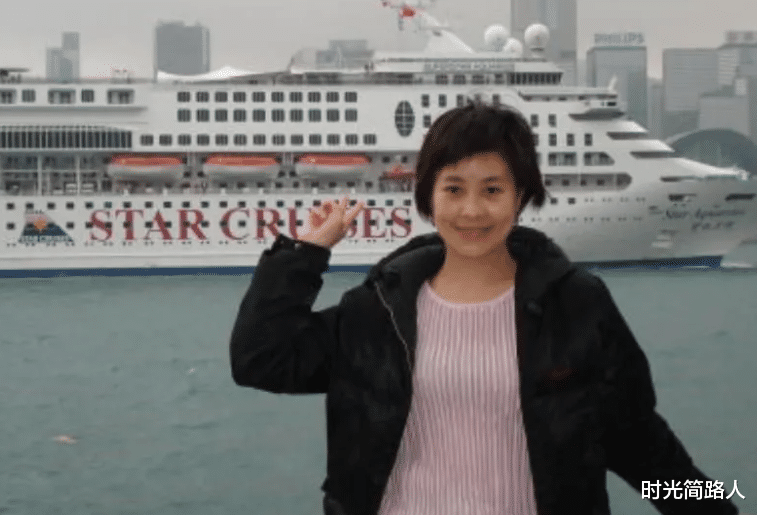
学校里,大多数同学平时还是说地方话,课间走廊里一片方言,只有一小部分,会自然用汉语聊天,而且不多,这时候,她的“收音机普通话”,突然成了明显优势,她一张口,就能听出跟别人不一样。
虽然还带一点点牧区口音,但发音清楚,句子顺,最重要的是,她敢在大家面前说,不怵话筒,同学有时候会打趣,说她说话跟广播里的人似的,声音一出来,很有辨识度,她那会儿其实有点害羞,又有点小得意,心想,原来我这几年没白练。
正好那段时间,学校想推进普通话,就想着建个广播站,缺一个学生主播,消息一传,她几乎没犹豫,主动跑去报名,说我可以试试,老师递给她一张稿子,她在办公室当场读了一遍,声音不算专业,但一点都不虚。

老师听完,笑着说,那就你吧,从那天起,学校中午广播,第一句“同学们中午好”,就是她,音乐刚响两句,很多人就知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那个牧区女孩的声音。
每天中午,她坐在简陋的广播室,桌子上一个话筒,一叠稿件,有时念快了,自己会绊一下,有个生字读错,下了节目就去查,慢慢地,她感觉到一件事情,自己已经不仅仅是在“模仿收音机”,而是真的在“做播音”了。
从校园广播到甘南台,第一份真正的播音员工作来了毕业以后,很多同学回到家乡,找一份稳定工作,或者继续读别的专业,她想来想去,脑子里总是浮现两个画面,一是父亲握着收音机,二是自己在广播站对着话筒说话,她有点犹豫,但最后还是给自己定了个方向,要去做播音主持这一行。
那会儿,她没有漂亮简历,也没什么“名校”光环,但甘南台刚好在招播音员,她硬着头皮去试,领导先听她说了几句,又看了看她的经历,觉得这个姑娘普通话挺标准,人也不张扬,就点头留下了。

就这样,她从一个牧区学生,变成了一名正式的播音员,刚进台,什么都得学,怎么拿稿子,怎么对镜头,红灯亮了该怎么压节奏,有时候一条新闻要提前在心里过好几遍,生怕上台出错。
她回宿舍时,经常把当天的稿子再念一遍,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表情是不是太僵,有一回,她自己都笑,说镜子里的这个人,跟当年缩在炕角听广播的小姑娘,已经不太一样了,但她也知道,不管在哪里,说好每一句话,才是本事。
她还做了一个小决定,把“耿萨”这个藏语名字,直接当主持名用,这个名字简单,好记,又有一点特别,一念出来,观众就能对上号,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挺聪明,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名字,把她记住的。
在甘南台工作的几年里,她什么节目都上,有严肃一点的新闻,也有轻松一点的本地故事,还有线下的活动主持,节目不算大制作,但每一次对着镜头开口,都是给自己加一层底气。

四年下来,她在甘南台已经算小有名气,有人看节目会特地说一句,这姑娘说话挺清楚,但她心里知道,甘南台可能不是最后一站,她想看看,再往前一步,是不是还有更大的舞台。
正好,甘肃电视台在招播音员,她报名去试,一上来,给她安排的就是难度很高的《甘肃新闻》,这种硬新闻,稿子密,节奏紧,几乎不允许出大错,她坐到台前时,手心其实出汗了,灯光一亮,一片白,
她在心里跟自己说了一句,照平时练的来,就行了,那十几分钟,她基本没给自己留空,一句接一句,说完才发现,腿有点发软,播完那一场,领导就记住她了。
后面,她又陆续接了《新闻大观园》等节目,观众的反馈挺直接,有人打电话到台里,说那个女主持,说话挺舒服,这类话不算什么大奖,却是对她最实际的肯定。

按理说,能在省台做到这种位置,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满意了,但她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这样吧”的人,她一边上节目,一边又悄悄给自己加了一个任务,去兰州大学读新闻系,把学历这块补上。
白天跑台里,晚上跑学校,周末写作业,身边人都知道她挺累,有时候她也会想,这么折腾值不值,普通话已经不错了,播新闻也播得顺,再去读书,真的有必要吗,但转念一想,她心里那个目标一直没变,中央电视台,还是在那里等着她试一次。
第一次去央视,她被学历和条条框框挡在门外有了兰大新闻系的学历,又有了甘肃台的经验,她终于鼓足勇气,去了北京,参加央视主持人选拔,走进那栋楼,看见一群人,有的北广出身,有的中传毕业,简历一张张翻过去,都挺亮眼,她站在其中,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轮到她上场,她稳了稳呼吸,把这些年的练习,全部摊出来,播读、即兴,她都尽量发挥在自己的正常水平线上,不求惊艳,只求不掉链子,下场以后,她觉得还可以,至少没明显失误。

结果出来,她没在录取名单上,不是因为临时发挥太差,而是卡在了“学历层次”“院校出身”这些不太好改变的地方,央视没有把这事说得太死,他们留了她的资料,还顺带把她推荐给了浙江卫视。
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一次不小的机会,她晚上躺在床上,也在算这笔账,如果去浙江卫视,平台也挺大,知名度可能上得更快,但她心里又很诚实,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其实还是央视。
她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太轴了,是不是应该先去别的台锻炼,再说别的,纠结了一圈,她最后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行,那就咬咬牙,再试一次。
第二次得到认可,却被“调不走”卡住,她只好换个方式挤进去又一轮央视主持人选拔,她再去了一次北京,这一次,她心态稳了一点,知道流程,也知道评委大概会看什么,她照样把播音水平往外拿,这回,她的表现得到更直接的肯定,成绩不错,人也被央视这边记住了。
按道理,这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甘肃台不肯放人,她是台里重点培养的主持,要人放她走,并不是一句话的事,体制内的调动,有很多看不见的条条框框,卡着卡着,这个机会就拖没了。

那阵子,她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你要说完全不难过,不真实,她也会一个人在宿舍想,是不是当初应该先去浙江卫视,是不是自己这一路有点拧,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也知道,自己这个人要是不拧一拧,可能就走不到今天。
纠结归纠结,她没有就此躺平,央视那边开主持人研修班,她第一时间报了名,说白了,就是先站到门内再说,在研修班里,她重新当学生,发声、形体、写稿,一样样练,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持人一起打基础。
研修结束后,她终于有了一个折中的机会,以实习的身份,走进了央视,不是正式调入,但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往前多迈出的重要一步。
走进《朝闻天下》,她终于从“听广播的人”变成“说话的人”第一次走进央视大楼那天,她在门口停了几秒钟,抬头看那块牌子,心里闪过一个很具体的画面,小时候在土炕上抱着收音机听新闻的自己,那时她根本不敢想,有一天,自己会站到声音发出来的这头。

实习期,她什么活都接,写稿,整理资料,跑来跑去看别人怎么主持,有人上节目,她就在旁边盯着,记提词器的走法,记导播的手势,记每一个小细节,有时候,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就在那儿看,看完回去再自己默默练一遍。
慢慢地,她开始被安排上小栏目,表现稳定,就往更重要的位置挪,真正坐上《朝闻天下》的主播台,那天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隆重”,闹钟定在五点多,起床,化妆室里面对镜子,心里默背几句开场词,走进演播室,灯一亮,导演一个手势,她开口。
《朝闻天下》这个节目,很多人是边刷牙边听,边给孩子穿衣服边听,他们不一定能一下叫出每一位主持人的名字,只会说,那个短发女主持,说话挺利索,她知道,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她要做的,是让那一早上的新闻,干净地传到每一间屋子里。

从牧区炕头听广播,到央视演播室说新闻,这条线如果拿笔画出来,其实不算直,中间太多弯弯绕绕,有考试,有失败,有被卡住,但到了这个位置,她多少还是会在心里,对十三岁的自己说一声,你那会儿那些一个人对着破收音机练习的夜晚,都没白费。
她主动从镜头前退下来,把时间交给家庭和公益在很多人眼里,进了央视,就等于拿到一张“终身饭票”,待到退休算一条完整路但她的后半程,走得有点不一样。
在央视工作的那几年,她低调结婚,也悄悄当了母亲,她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提丈夫的情况,家人的信息都保护得很严,很少曝光,在这点上,她挺坚定的,节目归节目,家是家,两边要分开。
孩子出生后,她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早班节目要天不亮就出门,录完了回家,孩子可能还在床上睡,有时候,前一晚孩子闹腾了大半夜,她抱着哄,凌晨三四点才睡一会儿,天刚露亮,她又得提着精神坐到镜头前,不能让观众从她脸上看出一丝疲惫。
这样的拉扯,持续一段时间后,她自己也开始问自己,这条路要怎么走下去,事业和家庭总要做个平衡,鱼和熊掌,很难两头都夹在手里,她想过很多种可能,最后给自己选了一个,旁人看着有点可惜的答案,主动离开央视,把更多时间留给孩子和家庭。

离职那天,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公告,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跟熟悉的走廊和演播室对了几眼,心里说了句,行,就到这儿,转身出门时,她其实也有一点舍不得,但那种感觉里,多了一层释然。
从荧屏上退下来之后,她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大家看到她的方式,变了,从电视里那个正式的主持人,变成了一些公益活动上的志愿者,她会去一些学校,
尤其是偏远地方的,和孩子们聊普通话,聊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她很清楚,那种站在封闭环境里,对外面几乎没概念的感觉,因为她自己就从那走出来的
她也会参加一些公益项目,帮忙主持,或者干脆就在台下搬东西,安排座位,她不太愿意别人总是提起她“央视主持人”的身份,更希望别人记得的是,她现在在做的这些小而实在的事。

有人问她,会不会后悔离开央视,她想了想,说,好像谈不上后悔,只能说,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角色,有些人适合一直站在聚光灯下,她呢,现在更喜欢回到生活里,做一些看起来不显眼,但自己觉得踏实的事。
出身牧区也没关系,关键是你敢不敢拿起那台“旧收音机”这一辈子,其实没什么“天降奇迹”,收音机,是父亲留下的,小到不能再小的东西,普通话,是她每天跟着练出来的技能,央视,是她花了很多年,一次次去敲门,最后站上去的舞台。
你说她命好,也可以这么说,可要是当年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没有每天把收音机打开,嘴角裂了也要多读几句,第一次没进央视,心里难受完还是去补学历,第二次被卡,又跑去读研修班、当实习生,那后面这些故事,大概率就都换成别人的名字了。
出身牧区也好,小城也好,这些谁都改不了,真正能改的,是你愿不愿意拿起手里那台“旧收音机”,每天多听一会儿,多练一句话,不见得人人都能站到央视,但至少,可以把自己,从原地,一点点挪出去,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