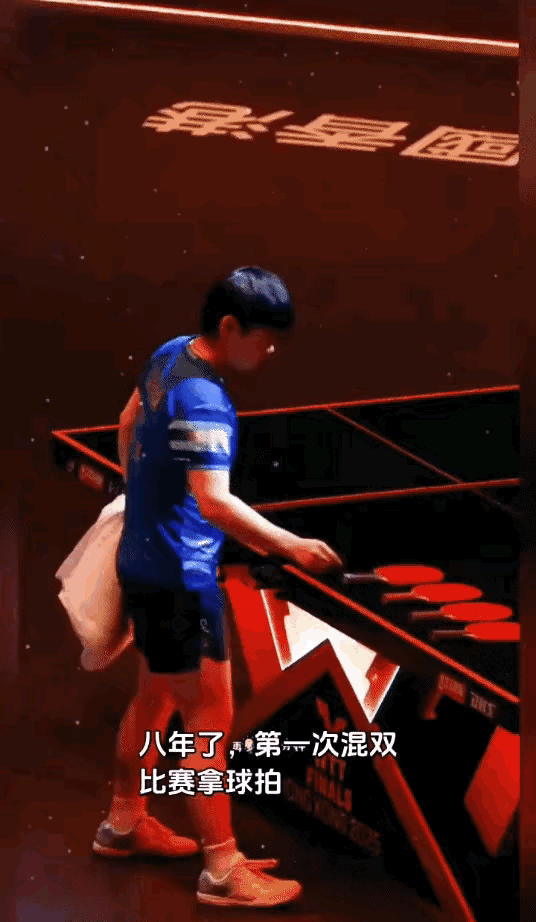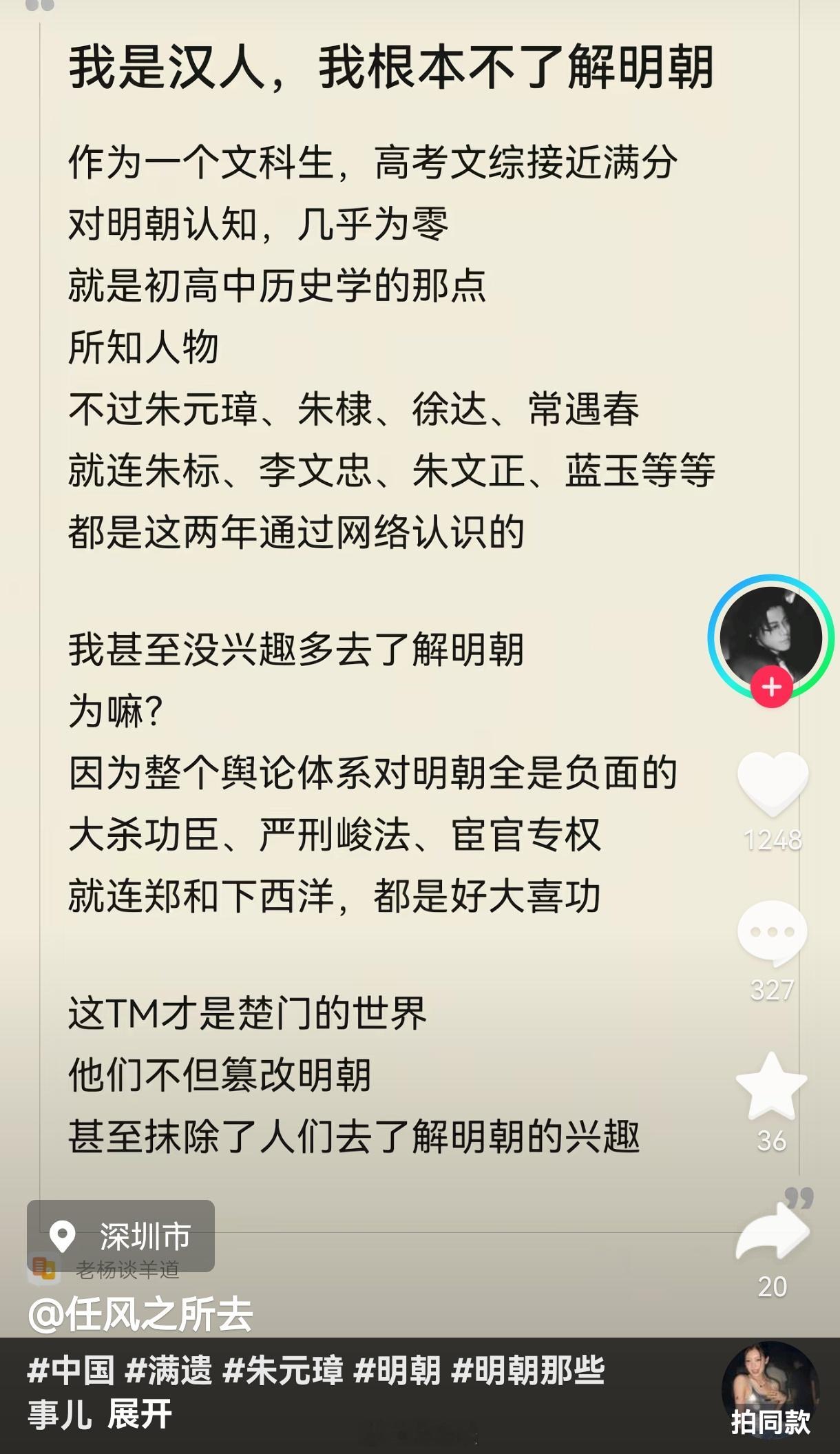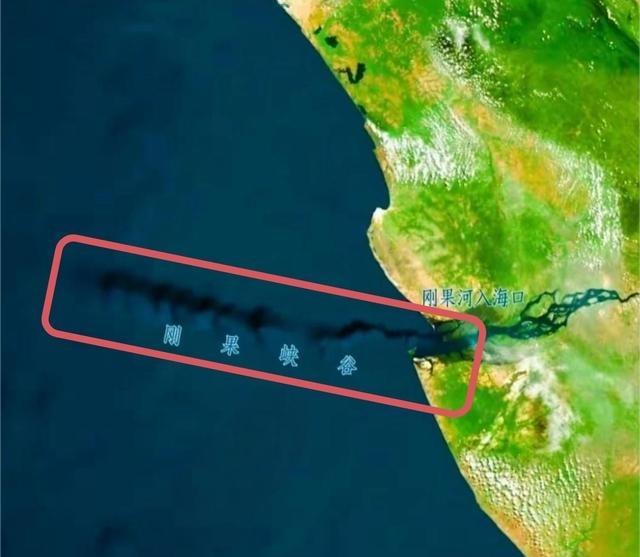作者:黎荔

在中国古代,兔子被赋予了两种性质,一种是世俗的,一种是神圣的。
什么是世俗之兔?——试想一个三千年前诗经时代的清晨,泥土是新翻过的,混着腐叶潮润的气息。三个着短褐的汉子,正俯身于林间那片空地上,紧绷的麻绳在他们粗粝的指间穿梭,发出“咝咝”的微响。他们在以木桩钉地,以麻绳布网。网已张好,隐在浅草与低枝间,成了一个静静等待的、肃杀的圆。他们退到不远处的土丘后伏下,呼吸也屏住了,只有眼睛亮着,像暗处的星子,紧盯着那片注定要有生命闯入的死亡之圈。
不多时,窸窣声起。一只土褐色的影子,箭一般射入圈中。是只草兔,毛色与这秋日的山野浑然一体,是土地最忠实的儿女。网“唰”地弹起,收拢。那团褐色在里面疯狂地冲撞、弹跳,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蛮力与绝望。挣扎是短暂的。汉子的手有力地扼住了它的颈项,那温热的、还在剧烈搏动的小小身躯,便陡然僵直了。傍晚,篝火燃起。那只兔子被处理干净,一根削尖的树枝穿过,架在火上。
在古代生活中,世俗之兔被当作食物来源。《诗经·周南·兔罝》早已写得明白:“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说的是就设置大网,捕捉野兔,捉到的兔子会被做成烤肉、兔羹。《诗经·小雅·瓠叶》中具体描写了炮制兔肉的方法:“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炮,就是炮制,用泥包兔肉煨烤;燔,是直接在火上烤;炙,则是把肉挂起来熏烤。兔肉入馔,或炮、或燔、或炙,泥裹煨烤,火上翻转,烟熏火燎之间,兔成了百姓餐桌上的滋味,成了宴席上的佳肴。
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也有很多捕猎兔的画面。如南阳王庄出土的汉石画像显示:山势嶙峋如犬牙,两只猎犬,一前一后,将那土黄色的影子逼入绝境。前头那只猎犬倏地回身,截断了最后的去路。那被围困中央的生灵,筋肉绷紧,后腿蹬地,眼里映着天光与逼近的死亡。汉画像石上的线条,将这一刻凝成了永恒。猎犬奔逐,人呼犬应,兔影仓皇——那是生存的日常,是人与自然最朴素的角力。我们的先祖,早已将捕食野兔的技艺,锤炼成诗,锻刻入石,化为最寻常的生存图景。

然而,若有一只兔,通体雪白,如月华凝成,便立刻从尘世抽身,步入神圣之境。
白兔之“白”,非寻常色相,而是天降异象。明代以前,华夏大地并无驯化的家兔。明代之前,中国传说、记载里提到的兔子,大概率都是野兔。毛色大抵是贴近大地的土黄、褐灰,那是为隐匿而生的保护。白色,是僭越,是突变,是自然秩序中一丝迷人的、不谐的颤音。在今天看来,野兔毛发呈现白色,多为白化病等疾病导致。而在古代,古人缺乏这方面的医学知识,对于超出认知范围的事件多赋予神性解释。于是,葛洪在《抱朴子》里笃定地写道:“虎及鹿、兔,皆寿千岁。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白色,成了时间的勋章,是活了五百载光阴、通达灵异的证明。那捣药的玉兔,何以是白的?因为它捣的是不死药,它自身,便是“寿”与“变”的化身,是时间淬炼出的精灵。因其罕见,遂成祥瑞。
当古人的目光,从那惊惶的草兔身上移开,投向一片更渺远的、清辉流溢的所在。那是一片没有猎犬与罗网的净土。在那里,月轮如冰盘,桂影婆娑,一只莹洁如玉的兔子,正持着玉杵,一下,又一下。神话中的玉兔,高居广寒,陪伴着永恒寂寞的嫦娥,那玉杵声声,捣的是不死之药,也是人间对长生的执念。在昆仑之巅,西王母座下亦有白兔,非为口腹,而为仙班。这抹白色,跳脱了尘土,滤净了血腥,羽化登仙,成了悬浮在古老中国梦境高处的一缕精魂。它不再奔跑于草莽,而是静驻于永恒,与嫦娥的清寂、仙家的玄渺,浑然一体。这,便是兔子的另一副面目,神圣,纯白。
白,这颜色是关键的密钥。史官们郑重地记下某年某地“献白兔”的异事,那团雪也似的身影被呈于御前,不再是“燔之炙之”的肉肴,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意味着帝王的仁德感召了天地,意味着四时有序、海宇澄清。它被圈养,被凝视,被赋予一个王朝对“天命所归”的自我确认。《宋书·符瑞志》载:“白兔,王者德盛则至。”地方官吏一旦发现,必郑重其事,装笼进献,一路快马加鞭,直送京师。皇帝览之,或颁诏褒奖,或减赋免税,以应天意。
神圣性究竟源于何物?或许,它本就源于认知的边界之外,源于对“非常”现象的震撼与附会。然而,神圣的光环,往往经不住“多见”的消磨。随着记录的增多,到了北宋,白兔的神秘性有所降低,不再仅供皇家,大臣也可拥有。欧阳修就曾被滁州百姓送过一只白兔——祥瑞已走入士人庭院,不再独属帝王。欧阳修收到百姓献瑞时,那份惊喜,大约已更多是文士对珍奇之物的赏玩,是“太守与民同乐”的风雅点缀,而少了一份面对“神迹”的战战兢兢。我常想,那只被欧阳修收下的白兔,是否曾在醉翁亭畔跳跃?它是否知道,自己曾是天命的信使,是王朝德政的象征?抑或它只是懵懂地啃着青草,全然不知自己背负着千年的神性?而欧阳修是否会想起《诗经》里“炮之燔之”的焦香,想起南阳汉画像石上猎犬的吠声,想起渭水边设罝的丁丁木桩——同一只兔子,何以在彼处是釜中肉,在此处却成了案前仙?
明代崇祯年间,当“家兔”随着西方海船的到来而成为庖厨常物,那层迷离的光晕便不可避免地黯淡了。今日回望,兔子的神圣,并非来自它自身,而来自人心对未知的投射。当科学解释了白化,当家兔遍布乡野,白兔便回归为兔。只是,在某个桂香浮动的秋夜,当我们举头,望见那轮明月中依稀的暗影,心头是否还会掠过一丝古老的悸动?那已不是对“神圣”的迷信,而是对一种文化记忆的温情回望。我们不再相信月亮上真有玉兔捣药,但我们仍会将月饼做成玉兔的形状,仍会在孩子的耳边讲述那个流传了千年的故事。那捣药的玉兔,那作为祥瑞的白兔,它们从未真正“死去”。它们从神坛走下,化入了诗词、画卷、民俗与口耳相传的故事里,成为一种更坚韧、更绵长的存在——文化的基因。
在华夏大地的晨曦初露中,野兔跃过田埂,草叶沾露,蹄声轻悄。它不是神兽,却曾被奉为祥瑞;它不登庙堂,却屡见于史册。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世俗烟火,也映出神圣想象。一半是肃肃罝网下的求生之实,一半是皎皎月华中,那永远捣着幻梦的、神圣的虚影。兔虽小,却照见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图景:既脚踏实地烹兔为食,又仰望明月思兔成仙。这便是中国人的浪漫——在烟火与星河之间,为一只兔子,留出了独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