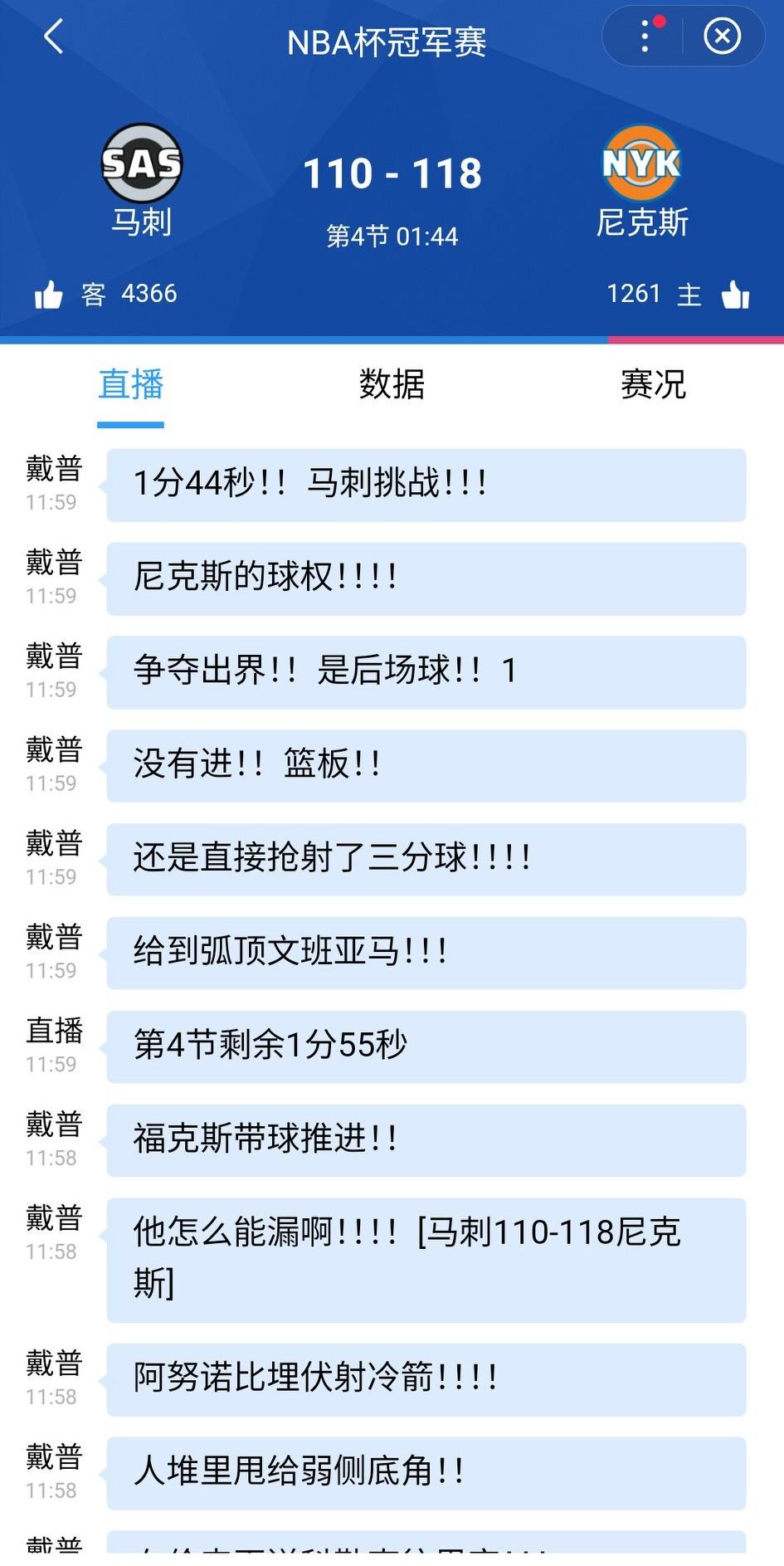我叫李亨,我的父亲是天子。
窗外秋雨敲打着西内的琉璃瓦,我站在甘露殿外已经一个时辰。宦官李辅国躬身低语:“陛下,太上皇……怕是熬不过今晚了。”雨水顺着我的冕冠流下,像泪水,但帝王无泪。
殿内飘来熟悉的龙涎香,混合着药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腐气。这是我少年时最向往的气息——父亲临朝时的气息。那时他是开元天子,万国来朝;我是东宫太子,如履薄冰。
“亨儿,进来吧。”声音嘶哑如裂帛。
一、盛世暗影
天宝五载正月,那个决定我一生走向的夜晚,雪花大如席。
父亲在花萼相辉楼宴饮,新得的美人杨玉环跳着《霓裳羽衣曲》,她的哥哥杨国忠刚刚升任御史中丞。我作为太子,坐在下首第三个位置——这已经比去年的第五位有所进益。
“太子近日读何书?”父亲忽然问,声音不大,却让整座楼阁安静下来。
我起身行礼:“回父皇,在读《贞观政要》。”
“哦?”父亲放下酒杯,眼神似醉非醉,“读到哪一篇了?”
“《论君臣鉴戒》。”
满堂寂静。这篇讲的是玄武门之变,讲的是太宗如何对待退位的父亲。杨国忠的笑容僵在脸上,高力士的手按在了拂尘上。
父亲大笑起来:“好!太子知史鉴今,当赏!赐金带一条,玉璧一双。”
那夜我抱着赏赐回到东宫,浑身颤抖。那不是赏赐,是警告。一条金带可以束腰,也可以勒颈;一对玉璧可以祭天,也可以陪葬。
我的老师李泌说:“殿下,圣人在告诉您,您的位置他给的,也能收回。”
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活在刀尖上。父亲用盛世的光芒笼罩大唐,那光芒太耀眼,耀眼到足以灼死阴影中的太子。
二、马嵬血月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长安城破前夜,父亲带着我们仓皇西逃。
马嵬驿的夜晚,士兵们的怒吼声如潮水般涌来。陈玄礼将军跪在父亲面前:“陛下,六军不发,请诛杨氏以谢天下。”
我看见父亲的手在颤抖,那只手曾执笔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曾拨动琵琶引来百鸟朝鸣,如今却握不住一个美人的性命。
杨玉环被白绫绞死时,父亲背对着佛堂,我站在他身后三步之外。他的肩膀垮了下来,那一刻他不是天子,只是个失去爱人的老翁。
“亨儿,”他忽然回头,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空洞,“你说,朕是不是错了?”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太大,大到足以压垮盛世。
次日,百姓拦住车驾:“宫殿,陛下家居;陵寝,陛下祖墓。今舍此欲何之?”父亲无言以对。
一个老翁跪在尘土中:“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率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谁为中原百姓主?”
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眼中的光彻底熄灭了。不是愤怒,不是悲哀,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他看见了权力的转移,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在衣衫褴褛的百姓眼中,悄然发生了。
我留了下来。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城南门城楼,我即皇帝位,遥尊父亲为太上皇。
那天夜里我梦见父亲,他站在花萼相辉楼上对我微笑:“亨儿,现在你是天子了。”
梦醒时,我摸到了满脸的泪水。
三、还京囚父
至德二载九月,长安光复。
我派李辅国迎父亲回京。十一月,父亲入城那天,我脱下黄袍,穿上紫衣,在丹凤门外跪迎。
“儿臣不孝,让父皇受苦了。”我叩首。
父亲扶起我,他的手很凉:“亨儿,你做得很好,比朕好。”
我们相拥而泣。在场的群臣、将士、百姓无不落泪。多感人的场面——历经劫难的父子,破碎山河的团圆。
但眼泪干了之后,权力重新显形。
父亲住进兴庆宫,那里有他五十年的记忆。他开始召见旧臣,有时在长庆楼接受百姓瞻仰,人们高呼“万岁”,不知是在呼他还是呼我。
李辅国提醒我:“太上皇身边有高力士、陈玄礼,还有玉真公主,他们……”
“他们怀念开元。”我接过了他的话。
是啊,谁不怀念开元?那个流光溢彩的时代,连月亮都比现在圆。可是他们忘了,正是那个时代的奢靡,孕育了安禄山的铁蹄;正是那个时代的宠爱,催生了杨国忠的专权。
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率五百甲士“护送”父亲从兴庆宫迁往西内太极宫。美其名曰“颐养天年”,实为软禁。
那天父亲走过横亘在两宫之间的夹城时,忽然停下,望着南内兴庆宫的方向:“五十年……朕在那里住了五十年。”
我没有去送行。我站在大明宫的含元殿上,望着西南方向。秋风吹来,我仿佛听见了父亲的叹息,也听见了开元盛世最后一丝回响的消散。
四、甘露之殿
现在,我站在父亲病榻前。
他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清澈到能映出我的愧疚。
“亨儿,你恨朕吗?”他问。
我沉默。恨?当然恨。恨他让我做了十八年战战兢兢的太子,恨他宠爱杨氏差点毁了大唐,恨他即使退位依然是“开元天子”而我只是“灵武继位”的皇帝。
但我也爱他。爱那个教我写诗的父亲,爱那个开创盛世的君主,爱那个在危难时刻将江山托付给我的老人。
“朕这一生,”父亲喘息着说,“有两个最大的缺憾。一是未能护住玉环,二是……未能与你做寻常父子。”
我的喉咙发紧。
“你母亲窦氏死的时候,你还小。”父亲闭上眼睛,“有人告发她行厌胜之术,朕……朕赐死了她。那时你七岁,抱着朕的腿哭:'父皇,儿臣冷。'”
我想起来了。那个冬天特别冷,母亲宫里的炭火熄了,再也没有点燃。
“朕后来知道她是冤枉的,但天子不能错。”一滴泪从父亲眼角滑落,“所以朕加倍宠爱你,立你为太子,又加倍防备你——因为朕对不起你,也怕你恨朕。”
权力如此荒谬。它让我们相爱相杀,让我们在拥抱时藏刀,在微笑时下毒。
“父皇……”我握住他的手。
“听朕说完。”他的手微微用力,“你在灵武即位,朕不怨你。国难当头,需有主君。朕怨的是……是你让朕活得太久。开元天子不该看见山河破碎,不该成为儿子的囚徒。”
我浑身冰凉。
“但朕也理解你,”父亲忽然笑了,那个笑容竟有几分开元年间的洒脱,“若换作朕,也会如此。这就是天家,这就是皇权。”
五、缺憾之宴
父亲临终前想吃一口冷淘面。
那是关中夏日的吃食,用井水浸过的面条,浇上蒜泥、酸醋、茱萸酱。他说年轻时和五王兄弟常吃,后来当了皇帝,御厨做的总是差一味。
“不是手艺差,”父亲说,“是少了那份烟火气。”
我下旨让尚食局做,但正值深秋,没有新蒜,井水也不够凉。送来的面,父亲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
“还是不对。”他喃喃道。
那一刻我明白了,他要吃的不是面,是回不去的青春,是五王宅里兄弟嬉戏的午后,是没有权力重压的轻松时光。
就像我要的不是他的死,而是他从未给过的、纯粹的父爱。
但我们都被困在各自的身份里:他是开创盛世又终结盛世的矛盾帝王,我是被他塑造又背叛他的惶恐太子。
深夜,父亲进入弥留。他忽然睁开眼睛,清晰地说:“亨儿,让朕去吧。你好好当皇帝,把大唐……重新撑起来。”
这是他最后的嘱咐,也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终的和解。
我点头,泪水终于落下。
六、缺憾永生
父亲去世后第七日,我也病倒了。
御医说是风寒入体,但我知道不是。是愧疚在啃噬我,是权力在反噬我,是那个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在折磨我:如果我不是太子,他不是皇帝,我们会不会是一对寻常父子?
弥留之际,我看见了母亲。她说:“亨儿,你做得对。”
又看见了父亲,他穿着开元初年的常服,对我招手:“来,为父教你写诗。”
还有杨玉环,她在跳《霓裳羽衣曲》,旋转中化为漫天桃花。
原来死亡是一场大解脱。解脱了爱恨,解脱了权力,解脱了“皇帝”和“太子”的枷锁。
宝应元年四月十八,我崩于长生殿。与父亲去世相隔仅十三日。
后世史官会争论:是我饿死了父亲吗?是我囚禁了他吗?是我辜负了孝道吗?
他们不会明白,在那场权力的盛宴里,我们都是饥饿的囚徒。父亲饥饿于失去的盛世,我饥饿于从未得到的认可,大唐饥饿于永难恢复的完整。
这就是天家的缺憾——爱被权力异化,孝被政治扭曲,死亡成为唯一的和解。
但也许,这就是人间最深的真实:我们都在缺憾中求生,在破碎中求全,在永恒的丧失中,寻找瞬间的圆满。
父亲,如果真有来世,愿我们生在寻常百姓家。
您教我写诗,我为您煮面。没有盛世需要开创,没有山河需要拯救,只有一对父子,在某个夏日的午后,吃一碗正确的冷淘面。
那碗面,将是我们最圆满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