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1941年冬夜的昆明郊外,日军轰炸机轰鸣声掠过山脊。 中央防疫处防空洞内,汤飞凡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将发霉的皮鞋底刮下的菌斑涂抹在培养基上。 洞壁渗出的水珠砸在培养皿边缘,与三公里外滇缅公路上伤员哀嚎声遥相呼应,这是中国战场上最寻常的寒夜,也是改写抗生素史的关键时刻。 七个月前,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带来的消息仍灼烧着汤飞凡的神经。 盟军已将青霉素列为最高军事机密,中国黑市上的进口青霉素价格等同黄金。 滇西战场转运站的报告显示,截肢士兵中70%因伤口感染丧命,这个数字在汤飞凡脑中化作三千个具象的溃烂创口,每个创口都在渗出混着磺胺粉的脓血。 实验室铁架上摆着两百七十四只培养皿,标记着从腐烂柚子皮到茅厕砖缝采集的菌株。 为寻找能产青霉素的青霉菌,汤飞凡团队化身微生物猎手,研究员卢锦汉翻遍昆明菜市,将长绿毛的冻土豆裹在棉袄里保温。 技术员把皮鞋浸在米汤中培养霉菌,恶臭引来村民误以为他们在制作生化武器。 1943年6月某日凌晨,编号XP-22的培养皿突然泛起奇异蓝光,这正是产青霉素菌株特有的代谢荧光。 菌种筛选仅是开端 ,没有恒温箱,他们用炭火盆与棉被搭建简易培养室,缺乏离心机,便手工摇动盐水瓶进行菌液分离。 某次空袭中,汤飞凡抱着培养瓶滚进弹坑,玻璃碎片扎进大腿仍死死护住三个月的心血。 这些细节后来被李约瑟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称其为“东方巴斯德式的执着”。 1944年9月,首批国产青霉素在怒江战役前夜诞生。 每支药剂标签都印着汤飞凡手书编号,装入竹筒由马帮穿越日军封锁线。 惠通桥守军记录,当磺胺无效的重伤员注射后退烧时,军医跪地亲吻沾满泥浆的竹筒。 这支5万单位的粗制青霉素,纯度虽仅为国际标准的60%,却使伤员死亡率直降40%。 量产挑战接踵而至,为扩大培养规模,汤飞凡带人改装寺庙浴缸作发酵罐,用脚踏风箱代替空气压缩机。 某次培养液污染事故中,他连续72小时值守,最终在发霉的玉米浆里找到替代培养基。 这种“土法上马”的智慧,后来被写入哈佛医学院案例库,成为资源匮乏条件下科研创新的典范。 1955年深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暗室里,汤飞凡将沙眼病原体滴入自己左眼。 肿胀的眼睑遮蔽了视线,他却坚持记录每个病理变化,这是继青霉素之后,他又一次以身为炬照亮医学黑暗。 当国际学界最终承认“汤氏病毒”时,他右眼视力已永久受损。 这种以身试险的壮举,与其说源于科学家的偏执,不如说是战时养成的决绝。 在昆明防空洞培养青霉菌的日子里,他早已习惯将个体生命置于民族存续的天平之上。 1988年某考古队在滇西战场遗址发掘出锈蚀的竹制药筒,内藏未启封的国产青霉素。 玻璃瓶身冰花纹与汤飞凡实验室器皿如出一辙,仿佛封印着那个时代的寒光。 而当今中国占据全球青霉素原料药70%市场份额的产业版图,恰似当年防空洞培养皿的时空投影。 从每支药剂数万元的“液体黄金”,到惠及亿万普通患者的常规药品,这条跨越八十年的生产线,始终流淌着汤飞凡团队在煤油灯下培育的菌株基因。 汤飞凡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他用来计时培养过程的怀表,表盘裂纹如冰河解冻的纹路。 每年清明,总有白发苍苍的老兵在展柜前洒落青霉素药粉,这是战火年代最奢侈的祭品,亦是献给破壁者的无言礼赞。 防空洞里的菌种仍在繁衍,正如汤飞凡留给后世的启示,真正的科学壁垒,从来不是技术封锁,而是甘愿为千万人抱薪赴雪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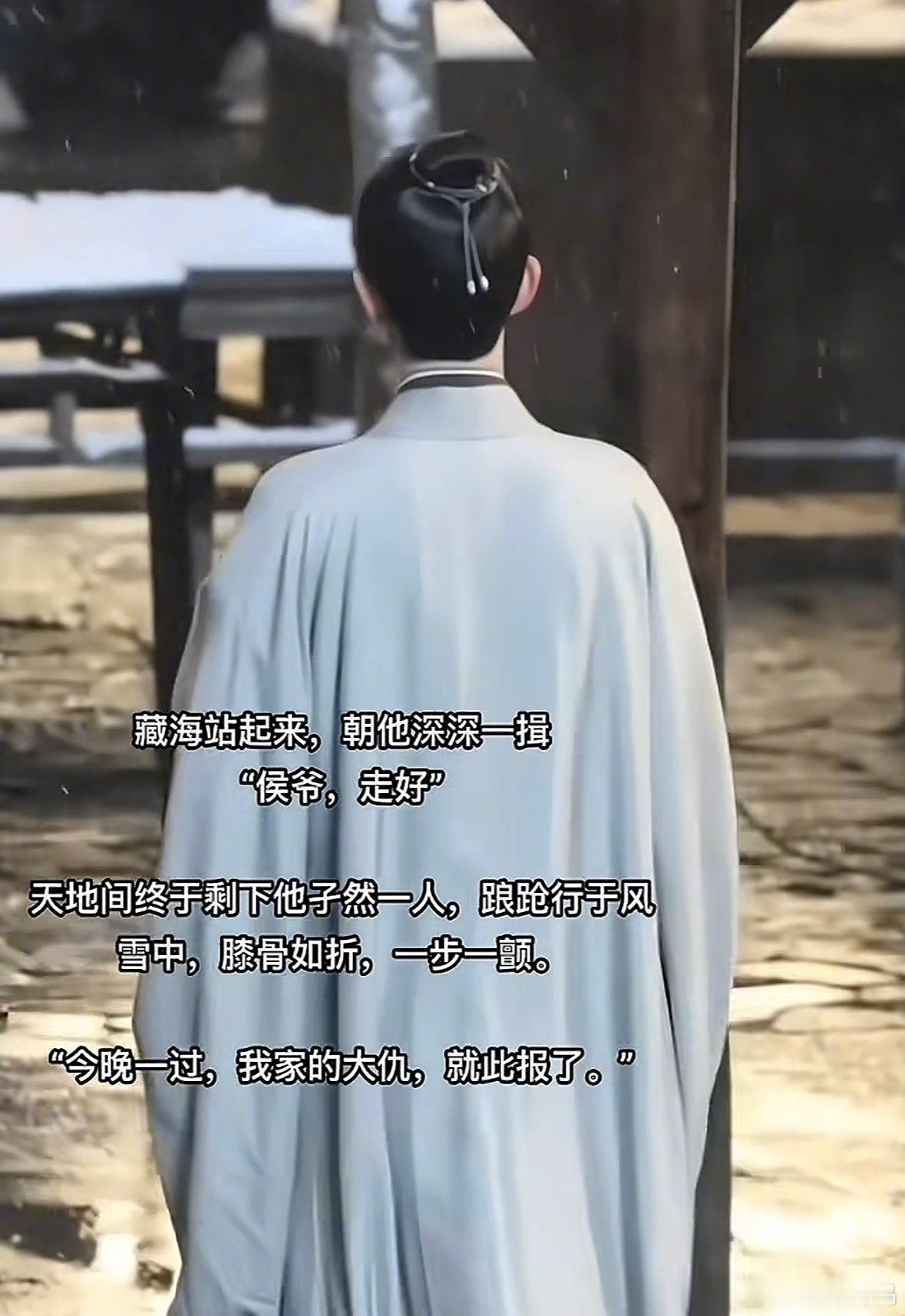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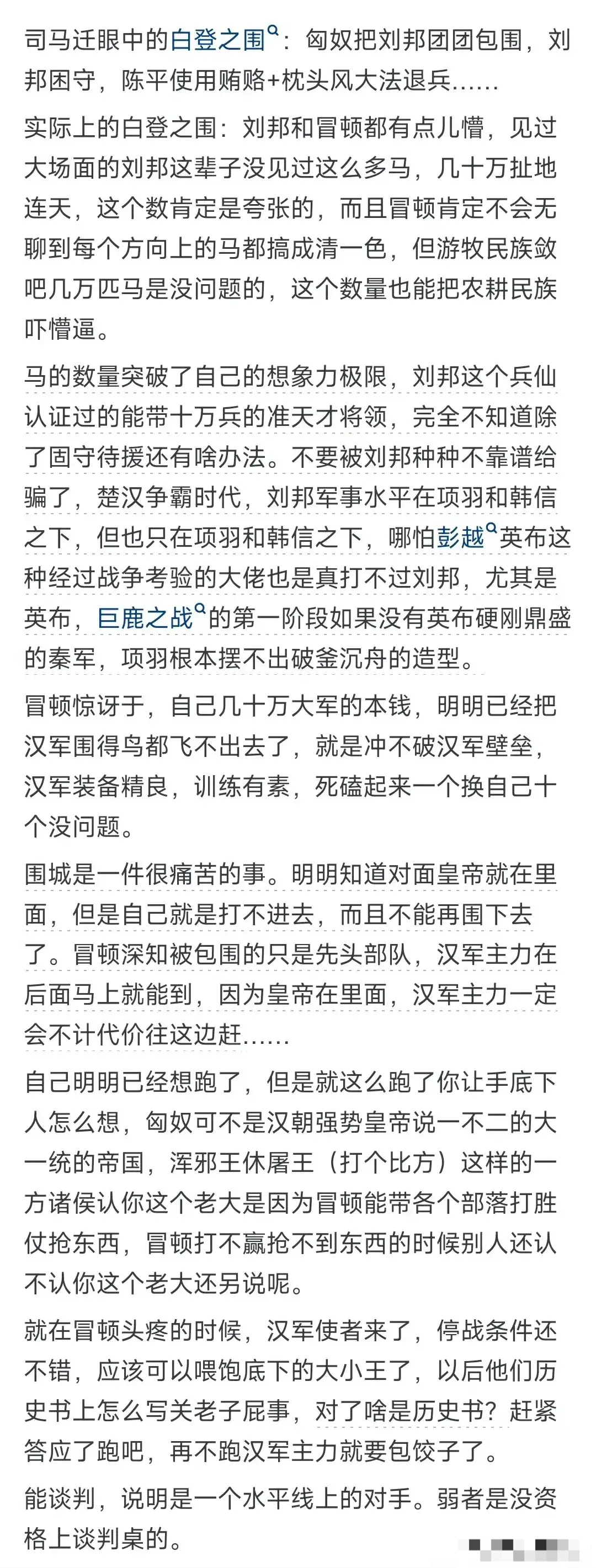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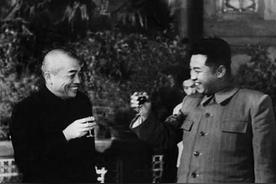

xu峰
致敬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