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鸡泛滥成灾,为何很少有人吃?当地农民直言:“别说吃了,我们甚至都不敢招惹它! “张大爷,你家苞米地又被野鸡刨了?咋不设个陷阱呢?”“可别瞎说!这玩意儿现在碰不得,上次邻村老李头就因为捡了只受伤的野鸡,派出所的人直接找上门了。” 在东北的田埂上,这样的对话时常能听到。 如今的东北农村,野鸡群飞的景象早已不新鲜,它们在春耕时啄食种子,秋收时糟蹋庄稼,却鲜有人敢对其动心思,这背后的缘由远比想象中复杂。 清晨,天不亮就有村民扛着竹竿往自家稻田走。露水打湿了裤脚却顾不上擦,远远看见十几只色彩斑斓的野鸡正在稻穗间蹦跳,立刻挥舞竹竿驱赶起来。“这些‘祖宗’比人还精,你一转身它们就回来,一天得守着八九个钟头。”村民指着田埂边散落的稻粒十分心疼。 这种被称作“雉鸡”的野生动物,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过度捕猎濒临消失。当时东北林区的捕猎队常用套索和排铳围猎,市场上野鸡肉每斤能卖到 80 元,漂亮的尾羽更是成为工艺品原料。直到雉鸡被列入“三有动物”名录,才让这一物种得以喘息。 但保护与民生的矛盾也随之凸显,当地农作物因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中,野鸡破坏占比超过一半。农民们试过各种土办法:在田间挂铃铛吓唬,结果野鸡很快适应了声响;用反光带制造光影,连阴天就完全失效;扎稻草人更是成了笑话——野鸡会直接落在稻草人的肩膀上梳理羽毛。 归根结底,法律的红线是多数人不敢招惹野鸡的首要原因,曾有某村民为保护自家菜地,架设电网电死数只野鸡,最终因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 不过从生态链的视角看,野鸡的泛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大兴安岭林区,它们的存在确实控制了松毛虫的数量,每亩林地的虫害发生率下降了许多。但在农耕区,这种“生态益鸟”却成了“粮食小偷”。 更棘手的是,野鸡的排泄物中携带沙门氏菌、禽流感病毒等病原体,前几年辽河流域某养殖场就因野鸡接触引发禽流感,造成近千只蛋鸡死亡。这让本就对野生动物心存顾虑的农户,更不敢有食用的念头。 而面对愈演愈烈的 “人鸡冲突”,有些地区设置“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农户可以凭借村委会开出的证明和损失评估报告申请补偿。而有些地区则尝试在农田周边种植野鸡不喜食的沙棘、柠条等灌木,形成天然隔离带。只是这些措施虽初见成效,但相较于每年的农业损失,仍显杯水车薪。 其实东北野鸡的故事就是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一个缩影——当野生动物从“稀缺”走向 “过剩”,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保护的决心,更要有平衡的智慧。 文丨小王 编辑丨史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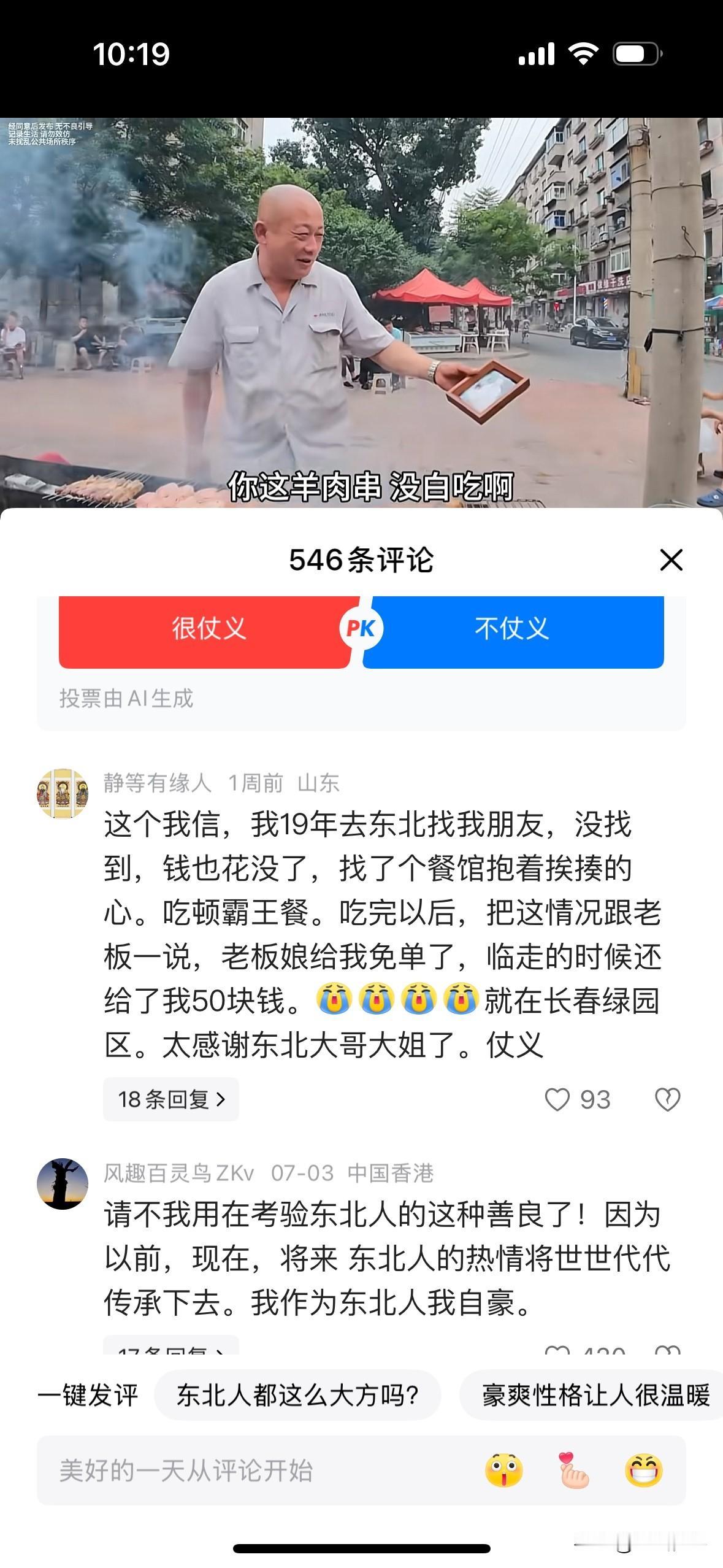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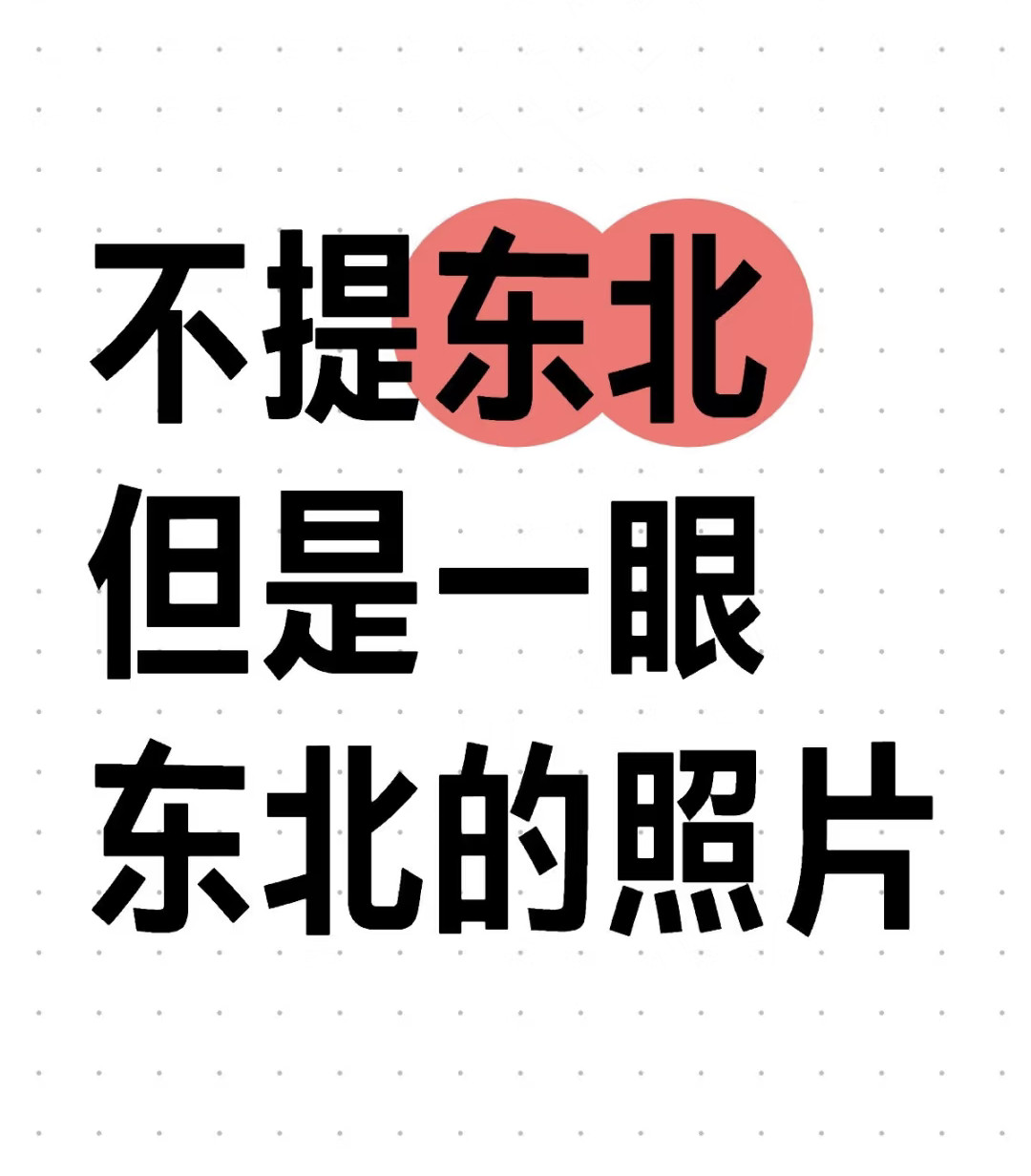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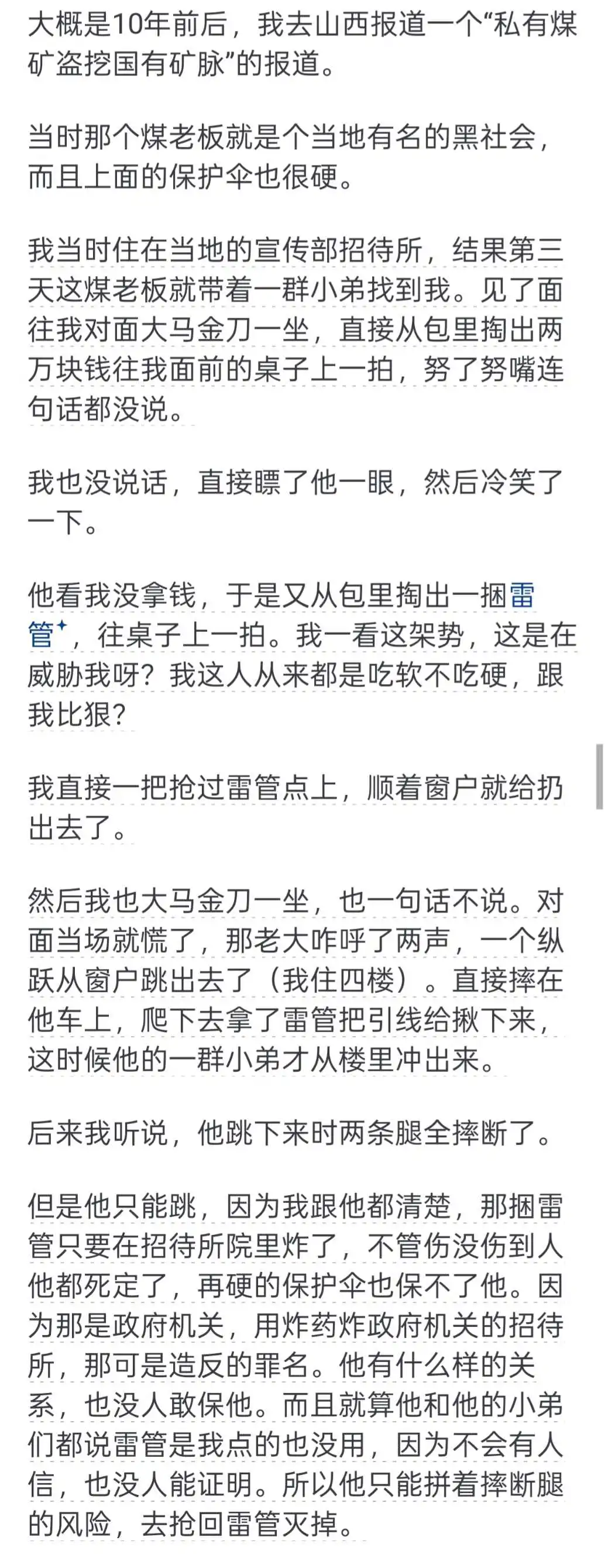




用户10xxx85
呦,这是小野鸡炖蘑菇吃腻了,想尝尝老祖宗的蘑菇炖飞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