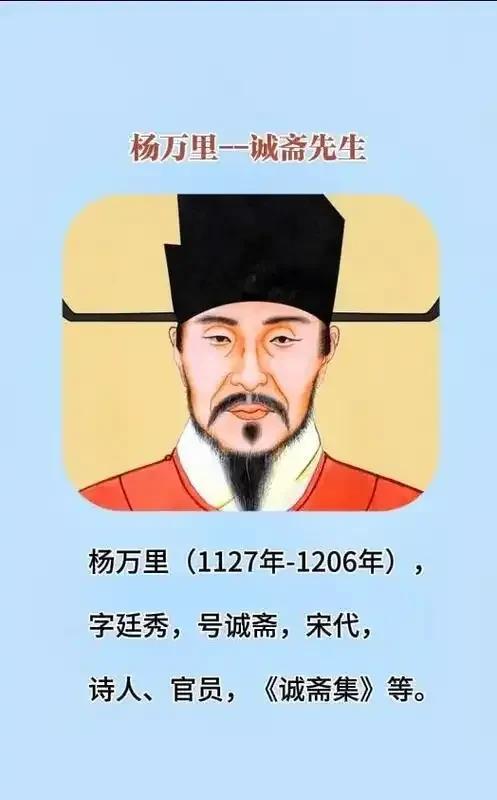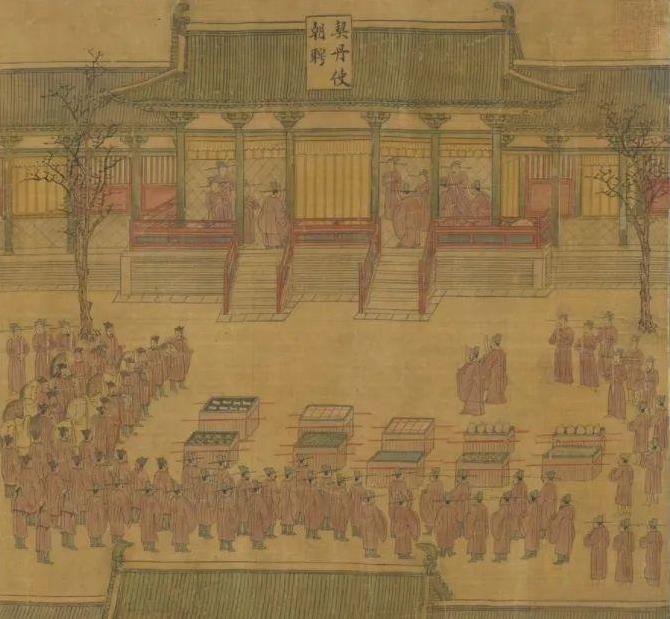1206年深冬,80岁的杨万里躺在病床上,突然挣扎着要起身。儿媳慌忙按住他:“您都三天没吃东西了,到底要干啥?”老人盯着窗外飘雪,突然用尽最后力气大喊:“韩侂胄误国!” 喊完这句话,老人胸口剧烈起伏,喘了几口粗气,便再没了声息。儿媳扑在床边哭,泪珠子砸在被褥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知道,公公这口气,是被朝堂上那桩糟心事憋死的。 说起来,杨万里这辈子,活得像他写的诗,透亮又实在。他是江西吉水人,二十几岁考中进士,先在地方当县令,后被调到京城。为官几十年,没贪过一分钱,没结过一个党,就认一个理:当官得替百姓着想。他在常州当知州时,碰上旱灾,百姓快饿死了,他不等朝廷批文,先打开粮仓放粮,有人劝他“小心被参”,他说“百姓都快死了,参我怕啥?”后来朝廷果然有人告他,他却理直气壮:“救民如救火,晚一步就多几条人命,这罪我认。” 他不光会当官,诗也写得好。“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些随口吟出的句子,读着就像看见眼前的景,老百姓都爱听。可没人知道,这位写得出温柔诗句的老人,骨头硬得像山里的石头,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半分不让。 这硬气,偏偏撞上了韩侂胄。韩侂胄是当朝权臣,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在朝堂上说一不二。他总想着干件“大事”留名,琢磨来琢磨去,盯上了北伐——打北边的金国,收复失地。这主意听着提气,可懂行的都知道,南宋当时国库空,士兵疏于操练,仓促北伐就是瞎折腾。 杨万里那会儿已告老还乡,住在吉水老家,可每天都让儿子读朝堂邸报。听说韩侂胄要北伐,他连夜让人磨墨,颤巍巍写了封奏疏,派人快马送进京城。信里说:“北伐不是儿戏,得先攒够粮草,练强士兵,安抚好百姓。现在啥都没准备好就开打,是把天下人往火坑里推啊!” 奏疏送进去,如石沉大海。韩侂胄嫌他碍事,对人说“这老头早该在家带孙子”,转头就下了北伐令。杨万里在家听儿子读战报,刚开始还能强撑着骂几句“胡闹”,后来听说宋军节节败退,金兵杀到淮河边上,抢了百姓的粮食,烧了村庄,他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打那以后,他就没好好吃过饭。家里人劝他:“您都八十了,管不动朝堂的事了。”他拍着桌子骂:“我是大宋的官,吃着大宋的俸禄,看着百姓遭罪,能闭眼不管?”他想起年轻时在临安当官,见过金兵南侵后逃难的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抱着孩子哭,那景象刻在心里几十年,如今竟要再看一遍,他怎么受得了。 入冬后,杨万里就病倒了。先是咳嗽,后来浑身发烫,迷迷糊糊中总喊“粮草”“士兵”“淮河百姓”。儿子找来大夫,大夫说“心病难医,得宽心”,可他哪宽得了心?每天让儿媳读战报,听到“金兵破城”“百姓流离”,就直挺挺地躺着,眼泪从眼角往下淌。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水米未进,嘴唇干裂起皮。窗外飘起雪,大片大片的雪花打在窗纸上,像极了他年轻时在北方看到的雪。那会儿他跟着朝廷官员巡查,见过黄河两岸的麦田,见过百姓丰收时的笑脸,可现在,那些地方怕是又成了战场。 所以他才挣扎着要起身,像是想再看看北方的方向,想再喊一声让朝堂上的人醒醒。那句“韩侂胄误国”,不是骂,是疼——疼百姓遭的罪,疼江山被折腾,疼自己拼了一辈子想护着的安稳,就这么被急功近利的人毁了。 老人走了,可他的话没白说。没过多久,韩侂胄的北伐彻底失败,南宋不得不割地赔款,朝堂上终于有人想起杨万里的劝告,追赠他“文节公”,说他“以诗名世,以节立身”。百姓更记得他,不光因为他写得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灵,更因为他到死都揣着一颗护着百姓的心。 如今去江西吉水,还能看到他的故居,院里种着他写过的荷花。每年夏天,荷叶田田,荷花映日,当地人说,风一吹,荷叶沙沙响,像极了杨老先生在念叨:“当官的,心里得装着百姓,才能立得住脚啊。” 参考《宋史·杨万里传》《诚斋集》《南宋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