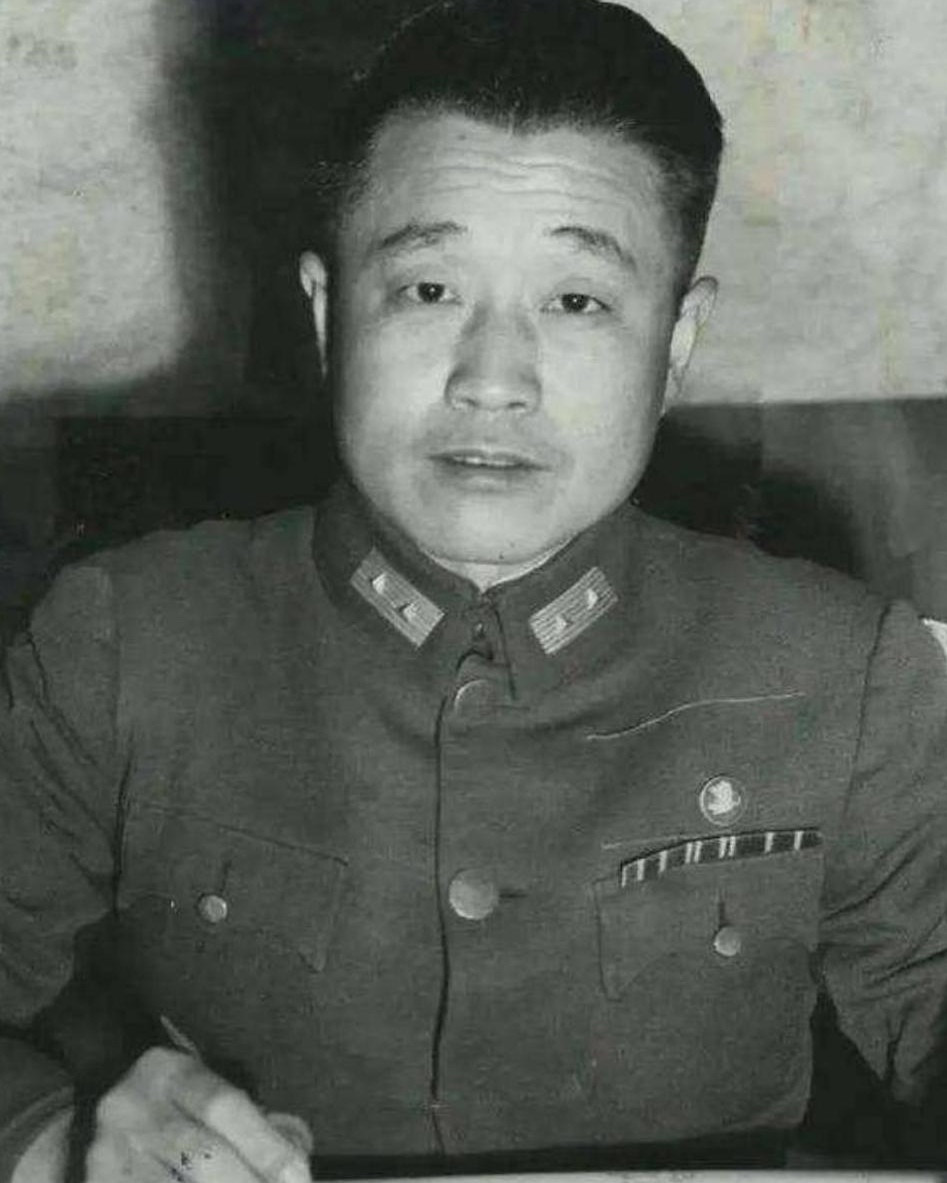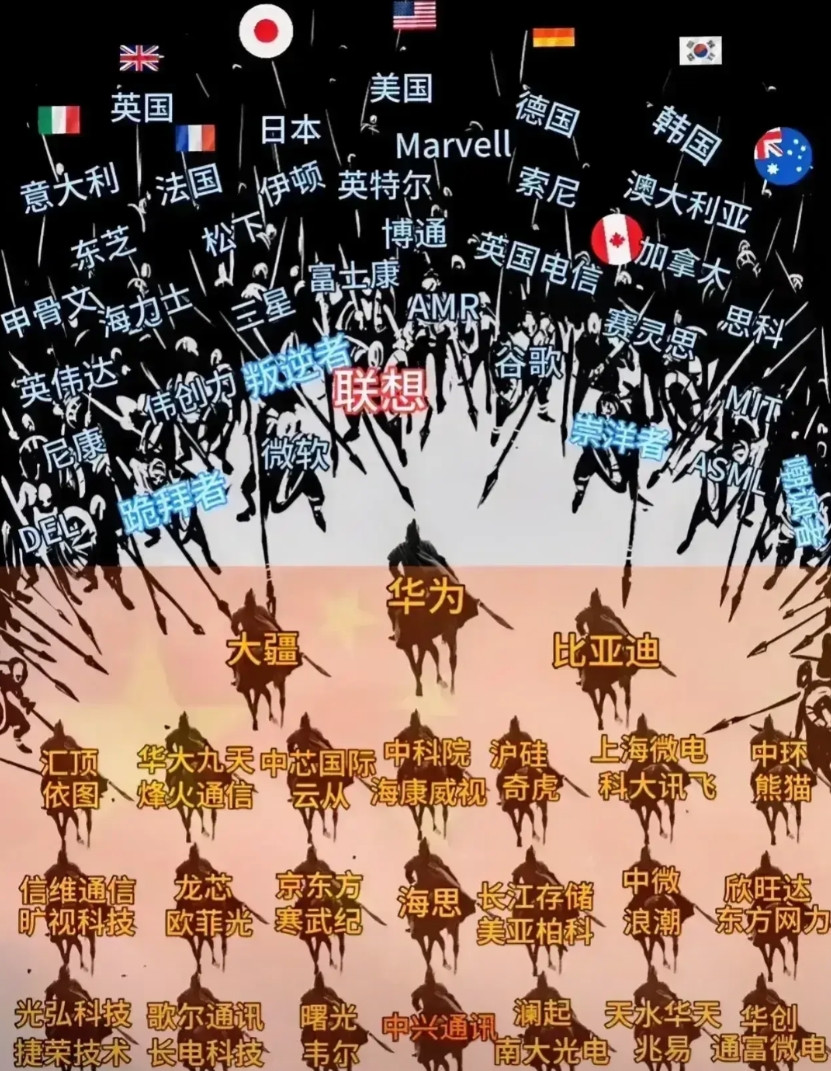05年宋任穷弥留之际,同女儿宋勤留下遗愿:我死后替我祭奠肖永智 【2005年1月6日,北京301医院病房】“小勤,过几天你得替爸爸去山东一趟——记得给永智上柱香。”声音短促,却像命令。九十六岁的宋任穷清楚地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不多,他要把那份压在心头六十年的歉意交给下一代。 病房外是隆隆的心电监护声,老人的思绪却飘回战火纷飞的1943年。那年深秋,冀南麦浪刚黄,他在作战会议上签下同意书,让旧伤缠身的肖永智继续留守陈官营。短短十几天,战友被流弹夺去生命。消息传来时,宋任穷握着电报沉默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只留下一句话:“所有战损报告照常呈交。”谁都看不到他指节的发白。 很多朋友好奇,两人并不算同乡,为何情谊如此深。原因要追到太行山。1938年3月,神头岭伏击战打响前夜,宋任穷时任129师政治部主任。天亮前,他在山坳临时指挥所碰到一张稚气面孔——二十三岁的772团政委肖永智抱着卷土褥,衣服被雨水浸得透亮,却提议把机枪阵地后撤三十米,“山风大,枪口抬高三度,敌人的辎重队正好在射界。”这番言简意赅的话救下了一个加强团,也让宋任穷记住了这位小老乡。 肖永智的锋芒并非一夜练成。1915年,他出生在湖北黄安的穷山窝。黄麻起义后,十来岁的孩子跟着父兄写标语、传情报,被乡亲称为“最瘦的童子军”。十五岁当县苏维埃通信员,十六岁已是红四方面军少共团委书记,履历亮眼得让同龄人咋舌。对外人来说,他似乎天生就该在枪林弹雨里开路。 1940年改编成新八旅后,旅里成分复杂,摩擦不断。有意思的是,肖永智没写条文,也没开长会,他拎来一个西瓜递给排头兵:“整瓜难分,切开才甜。”一个比喻就让干部们明白团结的要义。从那以后,新八旅内部再没因为山头问题闹过矛盾。老兵们回忆,这位政委开枪凶狠,放下枪却像邻家大哥。 真正让日伪军心惊的,是1941年的燕店奇袭。八路军三小时拔掉据点,缴俘七十余人。按照惯例,群众主张枪毙恶伪出气;肖永智却坚持全部宽大处理,“留一条活路,他们才有可能弃暗投明,咱的损失才能小。”对话不长,却扭转了冀南战场的俘虏政策。后来统计,新八旅靠这一招策反了近三百名伪军。 然而命运并未给他更多时间。1943年9月,新一轮“机动扫荡”迫在眉睫。组织决定送他去太行山休养,腿伤化脓已无法蹲姿射击,他却摇头:“这片地我熟,敌人要来,熟的人不顶,谁顶?”宋任穷理解他的倔强,却没想到这次点头成了永诀。10月21日清晨,陈官营西北,一个迫击炮弹划过玉米梗折断的旷野,年轻的政委来不及呼喊口令,已倒在血泊。 噩耗飞抵太行指挥部,刘伯承蹙眉无语,邓小平只叹“可惜”。宋任穷签收电报,第一反应不是悲痛,而是自责。他后来回忆:“那天明明可以用师部预备队换他下来,是我决断慢了半拍。”一个“慢”字沉入内心,再也拔不出。 冀鲁豫党委很快以烈士名义设立“永智县”。可宋任穷觉得,这远不够。战争结束后,他每到冀南都会先去陈官营旧址,蹲在荒草前默念战友的口号。1955年授衔那天,他敬酒给老部下,没人敢提祝贺,大家都懂他的心门尚未关闭。 转眼半个世纪,宋勤已是中年知识分子。父亲的遗愿,让她年年清明搭夜车去聊城莘县鲁西北烈士陵园。陵园里最大的墓碑就是肖永智,碑文简短,“抗日英烈,诸事从略”。有人问她缘由,她笑得克制:“这是父亲欠的债,我们晚辈替他还。” 2014年,民政部首批抗战英烈名录公布。肖永智之名排在中部,寥寥十二字说明。媒体采访家属时,侄孙一句话颇有分量:“我们家当兵的不少,可真想立功,先得把永智的那份血性学够。”短短一句,把血脉的传承讲得透彻。 不得不说,战争年代的友谊往往不需要长篇告白,一句生死与共已足够。宋任穷与肖永智,一个晚年高寿,一个英年早逝,命运差异巨大,却在共同的信念里留下浓厚交集。如今躲在档案堆里细读那封带血的家书,仍能感到纸张背后那股决绝。英雄已逝,山河无恙;而一封遗愿、一炷清香,正是后人对信仰最朴素也最庄重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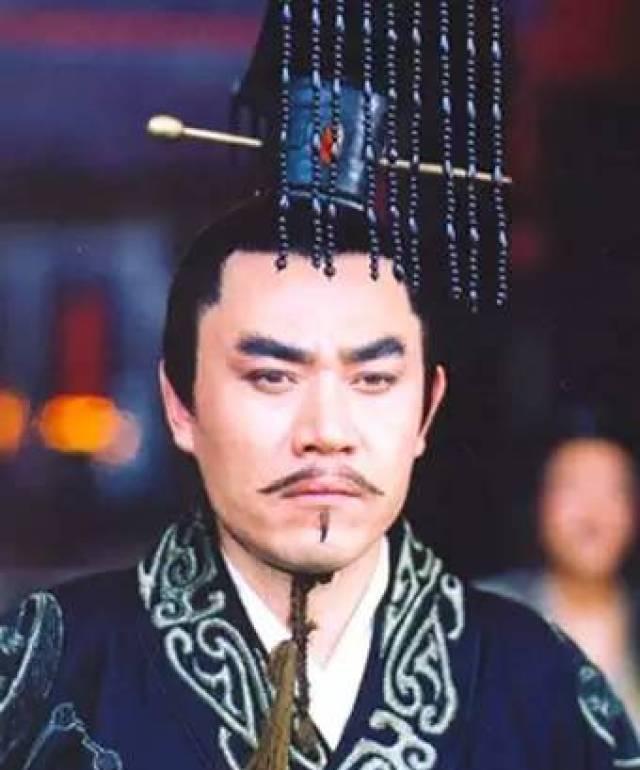


![马筱梅那么瘦吗[???]???看她以前的老照片,都是圆脸的,脸蛋胶原蛋白满满挺](http://image.uczzd.cn/60441043600032426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