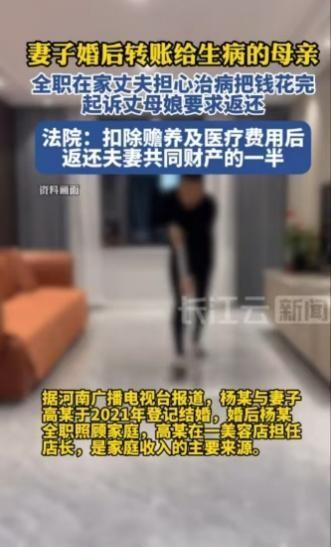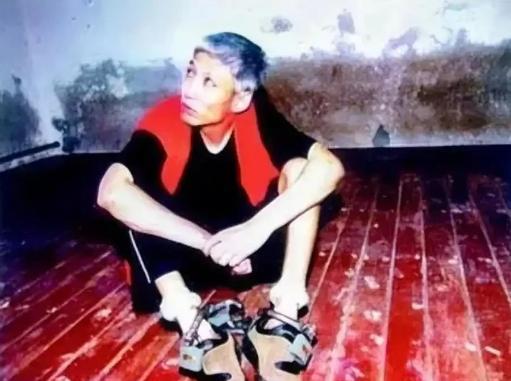1978年,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妻子在菜市场摸了一下冬笋,售货员见她的衣服上布满了补丁,翻了一下白眼,不客气地说道:“老太太,买不起就不要乱碰,冬笋很贵的,碰坏了你赔不起……”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寒冬的北京清晨,西单菜市场早已人声鼎沸,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挎着洗得发白的布兜,在蔬菜摊位前驻足。
她粗糙的手指轻轻抚过沾着晨露的冬笋,指节处还留着实验室里被仪器烫伤的旧疤。
售货员斜眼打量着这个穿着补丁棉袄的老人,突然一把拍开她的手:"老太太,这笋三毛五一斤,摸坏了你赔得起吗?"
布兜里静静躺着一张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工作证,照片上的何泽慧眼神锐利如当年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一般。
这位中国首位物理学女院士此刻只是笑了笑,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粮票和零钱。
她想起昨天刚完成的核乳胶实验数据,那些在显微镜下跳动的粒子轨迹,比冬笋的纹理精妙千万倍。
菜市场的嘈杂声中,没人认得这位与钱三强并称"中国的居里夫妇"的科学家,她身上那件穿了十五年的棉袄,袖口还留着在山西五七干校劳动时磨破的痕迹。
当年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用云室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学者,此刻正认真数着找零的硬币。
有顾客挤过来时,她下意识护住胸前口袋,那里装着给研究所年轻人修改的论文草稿。
胡同口卖豆浆的老张头倒是认得这位常客,他总记得何老太太每次都要把空碗舔得干干净净,有次看见她蹲在路边捡起撒落的黄豆。
老张不知道的是,那袋黄豆后来成了实验室里测量粒子轨迹的教具。
中关村的老邻居们偶尔会议论,钱家夫妇明明拿着双份院士津贴,怎么过得像低保户,他们看不见书房里那盏彻夜不灭的台灯,也看不懂桌上那些写满德文公式的草稿纸。
冬笋最终被放进布兜时,何泽慧摸到兜底那枚金质奖章,那是1946年法国科学院颁发的荣誉,曾经闪耀在塞纳河畔的勋章,此刻沾着菜叶的露水。
她想起丈夫钱三强昨晚的咳嗽,盘算着要不要再买些白萝卜熬汤。
身后传来售货员的嘀咕:"穷酸样还装文化人。"菜市场的水泥地上留着昨夜未干的雨渍,倒映出灰蒙蒙的天空,就像她1948年回国时在天津港看到的阴云。
研究所的年轻助理小王恰巧路过,看见何老师正弯腰捡起掉落的冬笋壳,他想上前帮忙,却被老太太抢先一步把笋壳塞进垃圾箱。
去年核乳胶实验失败时,也是这双布满老年斑的手,稳稳地调整了千分尺的精度。
小王记得何院士总说"实验数据不会骗人",就像她此刻认真检查冬笋是否被压坏的神情。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科院物理所档案室还保存着何泽慧那天的实验笔记,泛黄的纸页上,原子核径迹图谱与菜价清单奇妙地共存。
在"冬笋3.5元"的笔迹旁边,是用红色铅笔标注的粒子碰撞数据,当年菜市场的售货员早已不知所踪,而老太太摸过的冬笋价格涨了百倍,她留下的核物理公式依然在实验室的黑板上熠熠生辉。
何泽慧晚年仍保持着每天步行的习惯,九旬高龄还挤公交去研究所。
有次被门卫误认成拾荒老人,她只是默默掏出工作证。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位参与研制我国首颗原子弹的科学家,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奖金全数捐给了西北地区的希望小学,她总说真正的富足不在碗里有肉,而在脑中有星辰。
菜市场的冬笋早已不是奢侈品,何泽慧手写的实验报告成了国家档案,当新一代科学家在宽敞明亮的实验室操作千万级设备时,玻璃展柜里那件打满补丁的棉袄静静讲述着另一种珍贵。
老太太当年数硬币的手指,曾调试过改变中国科技命运的仪器;那个被嫌弃的旧布兜,装过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论文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