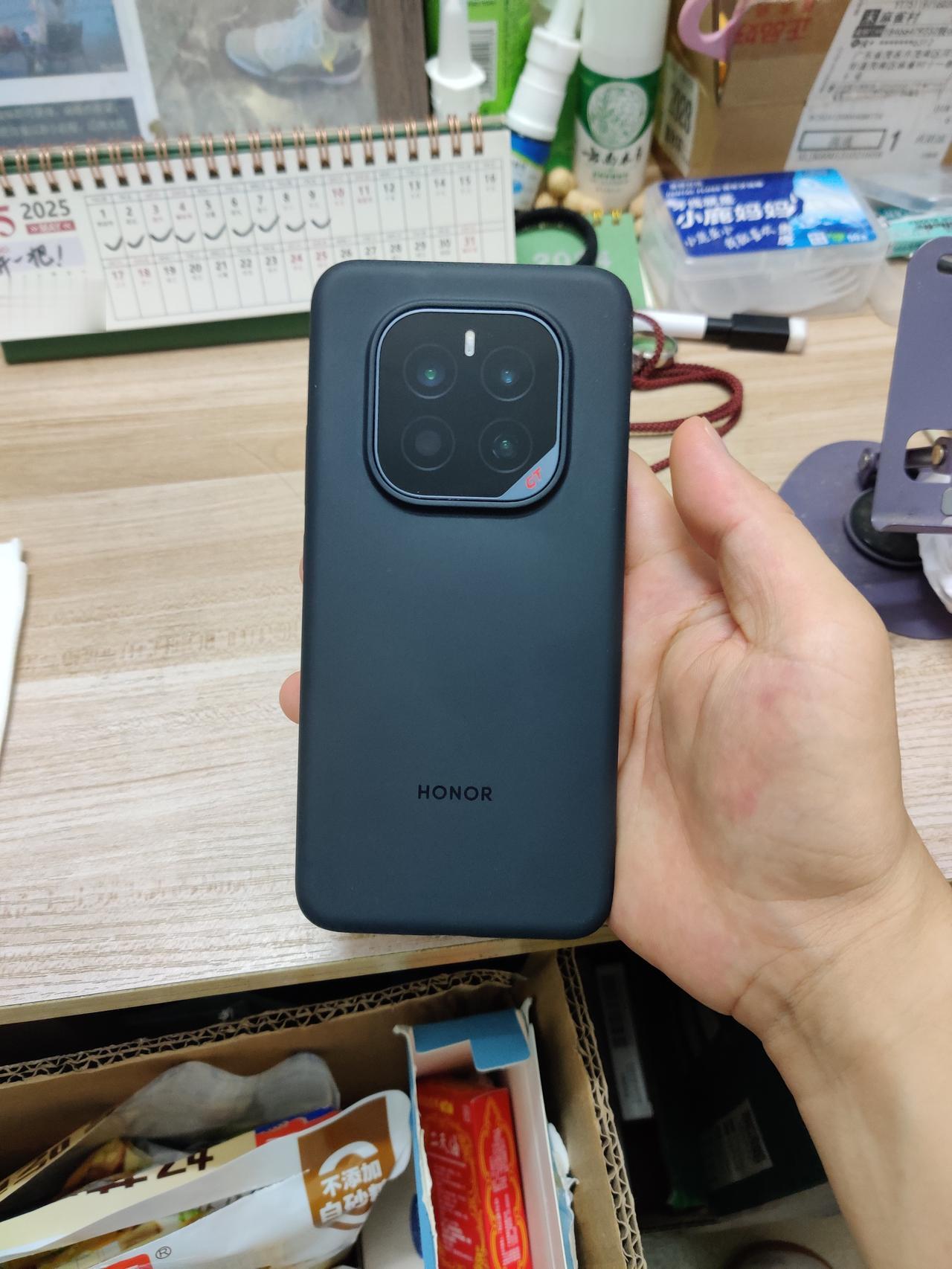再议《沉默的荣耀》与无名英雄广场纪念碑铭文 关于《沉默的荣耀》 《沉默的荣耀》,以隐蔽战线勇者与正义者为致敬对象,其激励意义核心立意,清晰可见。该剧亦可视作推动两岸统一的积极举措之一?即便暂不深究这一属性,其在凝聚民族共识、唤醒共同记忆层面仍具重要意义。 另外,全国百姓及全球华人、华裔,特别是大陆台湾人民,希望祖国尽快统一的,参与辨识并剖析阻碍统一的各类力量。最基本目标:推动两岸军队统一。在实现两岸军队统一的基础上,暂维持其他领域现。这一思路契合台湾百姓的核心诉求: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期望两岸维持和平发展局面,保持现有社会生活节奏与治理模式;而对于这一方向,大陆百姓亦普遍认同 —— 大陆民众既迫切期盼实现国家统一,也普遍接受 “先实现两岸军队统一” 的路径,绝大多数人对此完全能够认可。 关于纪念碑铭文 该铭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撰写,全文如下: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从总体上看,铭文在化用苏轼《留侯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情的拓展与发挥。这段文字立意高远、情感深厚,刻画了民族危亡中 “无名大勇者” 的精神内核,无论是对 “大勇” 的定义,还是对勇者牺牲的描摹,都兼具文气与力量,感染力极强。 然而,在铭文中,许嘉璐先生把“无故加之而不怒”中的“故”改为“朕”。此修改或可视为一处缺憾。推测许嘉璐先生觉察“无故加之而不怒”不十分恰当,于是作此修改,用其“征兆”之意。确实,苏轼原文中的“无故加之而不怒”不太合适。对于这些无名英雄来说,往往是“有故加之”,也可能有“无故加之”的情况,还存在其它复杂情况。不过,许嘉璐先生改用“朕”字,“无朕加之而不怒”意思仍不恰当。况且自秦始皇以降,“朕”一般为皇帝专属,臣民鲜有用者。 即使非要用,应该用“征”以对应后文用的“猝”(因原文为“卒”;卒、猝,通),以表明皆为现代文字风格,或者用“眹”,且保持苏轼原文“卒”字,以彰显古风文字风格。用“眹”不是更好吗?明显的,还不如用庄子的“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再者,“无朕加之” ,场景不符。“无朕” 是 “无征兆、无痕迹的冒犯”,更像突发的、直接的挑衅。但隐蔽战线勇士面对的 “冒犯”,往往是长期的、伪装下的 —— 可能是敌人的试探、同伴的误解,甚至是亲人的不解,而非 “猝然的无征兆冒犯”。 还要考虑,不少隐蔽战线上的正义之士,或许多受多方赞誉,而非受谴责。即使把“无朕加之而不怒”作出更适当的修改,此铭文的描摹重心或多集中于‘忍辱负重’的隐蔽战线勇者,尚未完全涵盖其他类型 —— 那些同样牺牲奉献、兼具智勇与忠诚的隐蔽战线正义之士。 综上所述,此铭文应该作出适当修改,至少是要改“无朕加之而不怒”。这应该也是许嘉璐先生揣摩过的句子。作出修改,既是表示对整个隐蔽战线上无名正义英雄群体的尊敬,也是对字斟句酌需改则改的写作态度的坚持与认可。 对许嘉璐先生的几句话: 晚辈才疏学浅,本无资格与您探讨此类专业议题,亦绝无冒犯之意。仅出于对铭文行文优化的研究初衷,冀望让无名英雄纪念铭文更趋完善,更能承载对英雄群体的敬意。晚辈有些穿凿,甚至吹毛求疵。望海涵。若拙见尚有可取之处,恳请您再作斟酌。如果意见不对,则请多批评指正。 (最后:隐蔽战线人员,虽有忍之必须,然而,隐蔽战线人员的精神内核,始终以刚毅、气节、智慧、正义与机敏灵活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