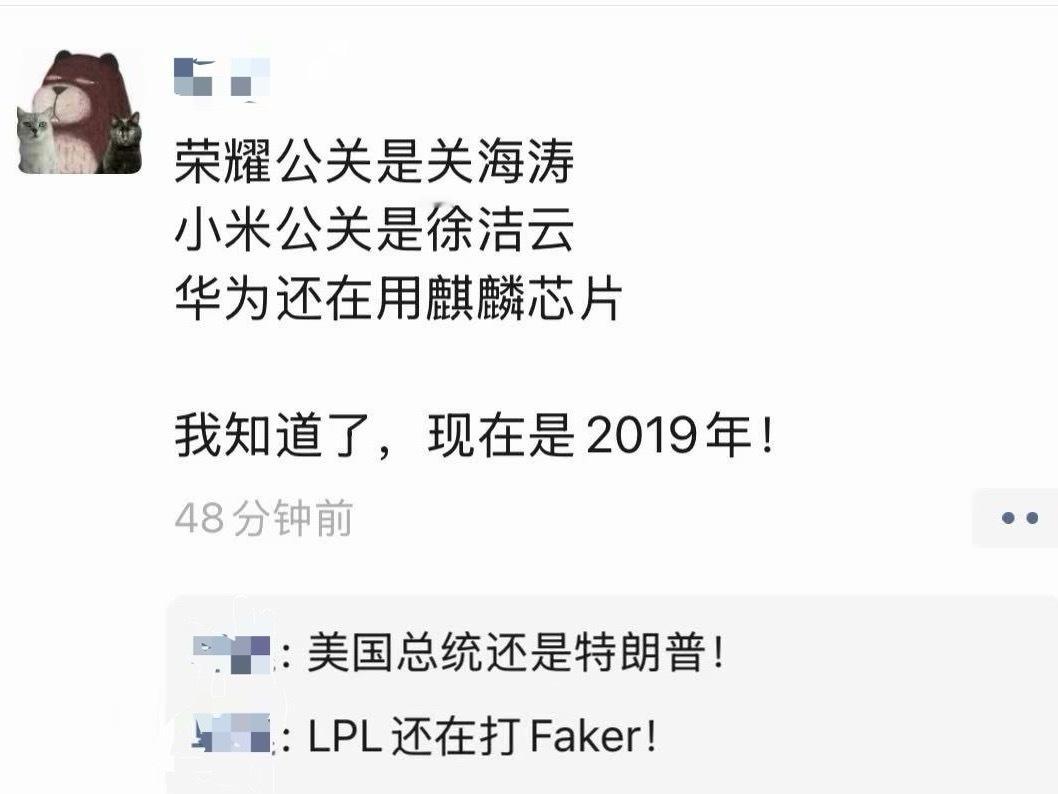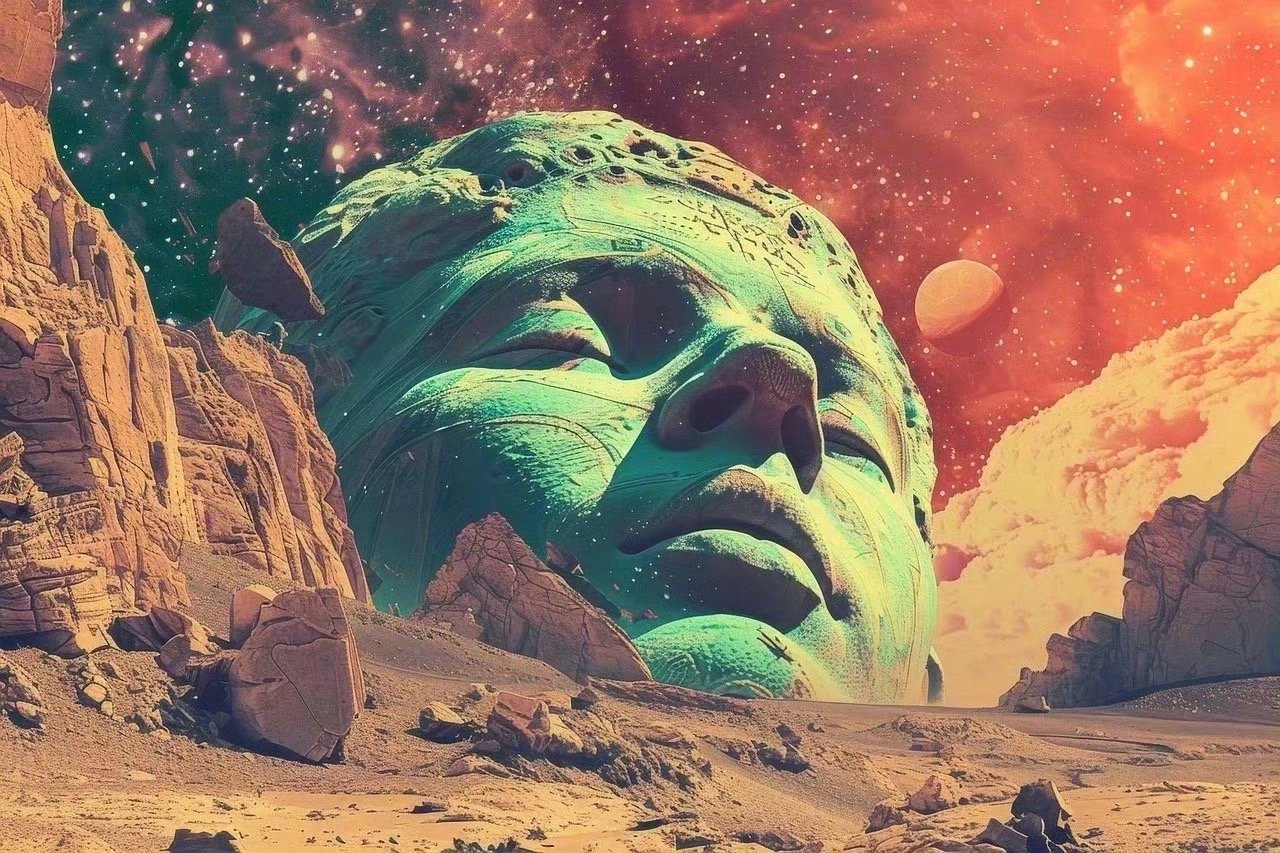非常深刻的一段话: “人活到六十岁,最不愿承认的真相就是,人生其实没有意义,不管你是生儿子,还是生女儿,三代后,时间会抹平你存在的一切痕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着一切都是空欢喜,死了一样也都带不走,如果说人生有意义,那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我活过。” 箱子比我预想的还要沉。把它从阁楼拖出来时,灰尘在午后的阳光里翻滚,像极细的金色沙粒。母亲去世三个月了,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整理她的遗物。 箱盖开启的瞬间,樟脑丸和旧时光的味道扑面而来。最上面是那本墨绿色的相册,封皮已经磨损发白。 我随手翻开一页。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在照片里朝我微笑,眼神明亮,嘴角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羞涩与庄重。那是外公,母亲曾说他是村里第一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可如今,村里早就没人记得他了。 再翻一页——父母结婚照。父亲的手紧张地搭在母亲肩上,两个人都笑得那么用力,仿佛要把一生的幸福都浓缩在这一刻。而此刻,父亲躺在城西的墓园,母亲的名字刚刚刻在他旁边的石碑上。 我的手指停在一张婴儿照片上。那是我,穿着臃肿的棉袄,像个小肉球。母亲常说,我出生那天她一夜没睡,就为记住我每一个表情。可现在,连我自己都记不清儿子婴儿时的模样了。 “爸,这些还要吗?”儿子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戴着耳机,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滑动。 “你先去写作业吧。”我说。 他如蒙大赦般离开。脚步声渐远,我突然想起,三十年前,我也这样对父亲说过同样的话。 箱底有个铁盒,锈迹斑斑。打开时,我愣住了。 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外公的立功证书、父母的结婚证、我的出生证明、第一张工资条、儿子满月时的脚印拓片……每一张纸都微微发黄,边缘脆弱得像是轻轻一碰就会碎裂。 最下面是本薄薄的笔记本。翻开,是母亲的笔迹: “1985年6月12日,小辉会叫妈妈了。” “1993年9月1日,送小辉上初中,他头也不回。” “2008年5月8日,小辉带女朋友回家,姑娘很文静。” “2019年11月23日,孙子考了全班第五,真棒。” 全是这样的片段,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这些琐碎的、被时间冲刷得几乎消失的瞬间。 我坐在地板上,一页页翻看,直到夕阳西斜,把整个房间染成橘红色。 儿子又来了:“爸,我饿了。” “等会儿,”我没抬头,“我给你奶奶记点东西。” “记什么?” “今天,2023年10月17日,小杰来找我两次。” 儿子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有什么好记的?” 我没解释。有些道理,需要时间才能懂,就像我直到五十岁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爱翻看这些“没用”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粒尘埃,在无边的黑暗里漂浮。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这么永远地飘着。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第二天,我继续整理。在箱子的最角落,发现了一个更小的木盒。里面装着三枚勋章是外公的;一支磨秃的钢笔是父亲的;还有母亲用了半辈子的顶针。 我把它们摆在桌上,看了很久。这些物件曾经那么重要,承载着荣誉、知识和关爱。可现在,它们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被遗忘。 “人都没了,留着这些有什么用?”妻子轻声问。 我说不上来。直到那个周末,儿子学校要求写一篇家族史。他难得地主动来找我:“爸,太外公真的是战斗英雄吗?” 我们一起翻看那些老照片和证件。我给儿子讲外公如何在一个雪夜背着受伤的战友行军三十里,讲父亲如何用那支钢笔写下给母亲的第一封情书,讲母亲如何用这个顶针为我们缝补了无数件衣裳。 儿子听得很认真,偶尔提问。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人生确实没有终极意义。三代之后,不会有人记得我的模样,不会有人在乎我是否存在过。所有的悲欢,所有的得失,最终都会归于尘土。 但这不是悲伤的事。就像此刻,午后的阳光照在儿子的侧脸上,他指着照片里年轻的外公说:“爸,你的眼睛和太外公真像。” 我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2023年10月21日,和小杰一起看老照片。他说我的眼睛像太外公。” 箱子里的一切,终将被时间抹去。人生空欢喜?也许是。 而活过,本身就是全部的答案。 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慨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我们总想留下永恒的印记,却忘了自己本就是永恒的一部分。 《传习录》记载王阳明与学生对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存在本身就是意义。我活过,所以我见过春天的第一场雨,听过夏夜的蝉鸣,爱过人,也被人爱过。这些体验不会因为终将消逝而失去价值。 佛陀在《金刚经》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接受虚无,但不沉溺于虚无。承认一切终将逝去,但更要珍惜正在经历的此刻。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建造永恒的纪念碑,而在于认真度过每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