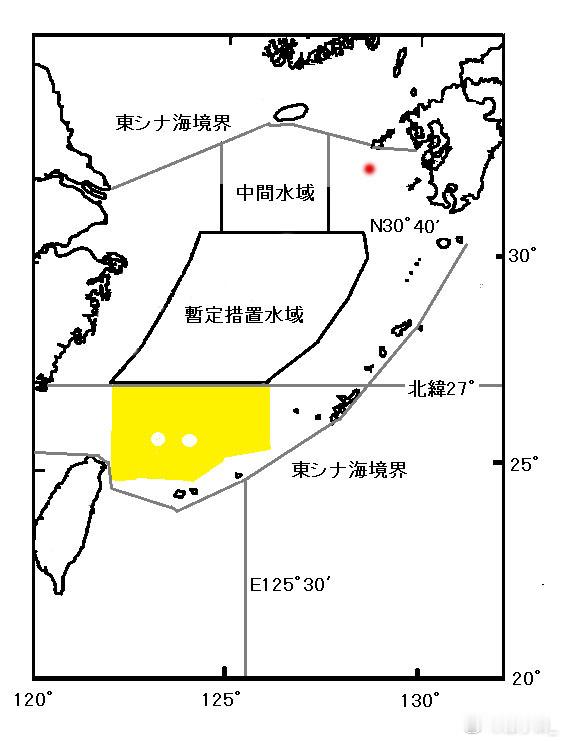1967年的重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跳楼身亡,然而14年后,公告指出:他根本不是自尽,这又是怎么回事? 死者名叫罗广斌,是从渣滓洞、白公馆血海逃出的幸存者,也是写出《红岩》的那位作者。很快,一纸冷冰冰的通报把这一切盖棺定论:“叛徒罗广斌畏罪自杀。” 就在这份结论发出的前几个小时,胡蜀兴接到一张悄悄递出的纸条,纸条上没有“诀别”,只有罗广斌匆匆写下的几样日用品和粮票数目。 一个在国民党牢里挨过竹签、坐过老虎凳的人,当年在死人堆里拼出一条生路,如今在新社会里,前一晚还认真盘算着烟和口粮,第二天一早却被说成“畏罪自绝”,怎么都让人转不过弯。 要看懂这桩“自杀案”,绕不过罗广斌的前半生。这个出身忠县富裕家庭的“小少爷”,父亲是秀才,母亲在法院任职,哥哥做到国民党中将,本可以顺着家里安排走上一条安稳仕途。 少年时代的罗广斌,却在洪雅、在西南联大附中接触到另一种世界。抗战的硝烟、校园的风潮、老师和同学的议论,把这个“幺老爷”一步步推向地下党,把家庭的门第和个人的选择撕开了一道口子。 1948年被出卖后,罗广斌先后被押往成都稽查处、渣滓洞、白公馆。那是一段连夜色都显得阴冷的日子,审讯室里的灯永远太亮,刑具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面对威逼利诱,这名年轻党员咬紧牙关,把组织交代的纪律当成最后一道底线。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国民党想用汽油和子弹把证人统统灭口;白公馆里,罗广斌却抓住看守杨钦典的惶恐,用“证明改过”的承诺打开了牢门,让十九名被囚者分组突围。 新中国成立后,罗广斌把在“人间炼狱”里记下的对话、教训、血债,一笔笔整理出来,形成狱中报告和“狱中八条”。这些材料既是对旧政权的控诉,也是给新政权的提醒,其中一条直指特权和腐败的危险,希望有一天掌握权力的人别重蹈覆辙。 后来与战友合作创作的《红岩》,用文学的方式把江姐、许云峰写进千家万户,七百多万册发行量、十九种外文译本,让一个城市的记忆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 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这段经历和这本书,在十几年后被翻成新的“罪证”。当社会陷入狂热,家世被反过来当成原罪,越狱功绩被恶意解读为“内幕”,《红岩》被扣上“为叛徒翻案”的帽子,“渣滓洞幸存者”一下子被推向批斗台。 1967年2月初,外地红卫兵和本地造反组织相继发文点名,罗广斌被抄家、被押往军队院校的楼里,连续多日轮番审问。 那栋楼的三楼卫生间后来成了案发地。看守口中的画面是,罗广斌脱下大衣、围巾,把钢笔和手表放回口袋,爬上窗台,高喊一句口号后纵身而下。这个说法伴随“畏罪自杀”的结论,压了胡蜀兴十几年。 胡蜀兴不只是不愿相信,更是有自己的判断:在国民党手里没有低过头的丈夫,多次表态绝不会走自尽这条路;额头巨大的伤口、尸体离墙较远的落点、家属被隔绝在外匆匆火化,这些细节处处透着不对劲。 直到1980年代初,随着对“文革”问题的清理展开,重庆方面重新勘查当年的现场。调查人员站在三楼窗前,比对高度和当年记录的位置,很快得出和常识一致的推断:如果是一跃而下,落地位置应靠近墙脚,而当年血迹斜洒出去,尸体距离墙面明显偏远,更接近被人用力推出的轨迹。 结合当年证言和失踪的申诉材料,1982年的结论终于写清:罗广斌死于非命,是在批斗中遭殴打致死后抛尸伪装。 从渣滓洞逃出的共产党人,终究没能在自己参与建立的新国家里安然老去。留下来的,是一部《红岩》,一份“狱中八条”,还有那张向家里要粮票的小纸条。 纸条上的字很普通,不过是烟、日用品和口粮的清单,却比所有口号都更让人难忘。那是一种活下去的本能,是在黑暗里仍然相信明天会有饭吃、有书写的倔强。 罗广斌的遭遇提醒后人,革命者最初想改变的,是权力踩在普通人头上的那只脚。如果某个时刻,拳头和皮靴又把无辜者从楼上推下去,那么无论口号多响亮,都与他当年在狱中写下的理想背道而驰。 真正值得纪念的,不只是书页上的英雄形象,更是那句写在血与泪之后的叮嘱:警惕特权,警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