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童年,是浸润在一种特定的光影与声响里的。
夏日的午后,或是某些特定的纪念日,学校会组织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走进那时还算新式的影剧院。灯光暗下,一束光从背后打来,空气中飞舞着微尘,银幕上便上演着黑白的苦难与暴行。那便是《南京大屠杀》。
许多细节已然模糊,但那几种意象,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烙在了心版上:明晃晃的刺刀,扎进婴儿柔嫩的身体,随即那小小的身躯被像一件玩坏了的玩具般抛向阴沉的天空;绝望的年轻母亲,衣衫在淫笑声中被撕扯殆尽;还有那机关枪,喷吐着火舌,将奔跑的无辜百姓当作活靶,最后,所有这些沉默的、破碎的躯体,被如牲口一样,推入巨大的、仿佛永远也填不满的坑中。
没有嚎啕大哭,影院里常常是死一般的寂静,间或有几声压抑的、忍不住的抽噎。然后,是长长的、集体性的噤声,我们排着队走回学校,夕阳依旧很好,街市依旧喧闹,但我们都沉默着,仿佛共同背负了一个过于沉重、无法与外人言的秘密。
那是一种原始的、未经过滤的恐惧与愤怒,它不讲道理,不由分说,便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精神底色的一部分。于是,“日本鬼子”这四个字,便不再是历史书上的名词,而是与这具体的、血腥的视觉记忆捆绑在一起,成了仇恨的图腾。
这份由集体记忆塑造的情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多年后,当我听到某些来自东邻的、不甚和谐的声音时,那股混合着铁锈与血腥的气味,仿佛又会从记忆深处弥漫上来。然而,个人的、家族的记忆,有时却会以一种更复杂、更微妙的笔触,在这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上,添上几笔令人困惑的灰色。
我的奶奶,是一位典型的北方农村老人,脸上的皱纹,是岁月与风霜刻下的沟壑。有一次,我不知怎地问起她,日本兵有没有来过我们的村子。
她想了半晌,用那种缓慢的、带着泥土气息的乡音说:“来过哩。追八路,到处放枪,啪啪的,吓人得很。”
“那他们杀人了吗?”我紧跟着问,心里预备着听到一个悲惨的故事。
奶奶的描述却让我一愣。“你那些姑姑们,吓得全都跑到离村远的地里躲着去了。有几个年岁大的,没跑,就坐在自家门口。有个日本兵,走到她们跟前,也没说话,掏出几个肉丸子,递给她们。”
“肉丸子?”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啊。”奶奶平静地说,“大家都怕有毒,不敢要,等人走了,就赶紧扔了。我没扔。”
“您吃了?”我惊愕地问。
“吃了。”奶奶的语气里没有任何波澜,仿佛在说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那时候,太饿了。萝卜皮都没得吃,树皮都叫人扒光了,哪能浪费……”
我一时语塞。在我的预想里,日本兵的形象应该是统一的凶神恶煞,他们手中的东西,只能是刺刀和枪炮,怎么可能是肉丸子?这温情脉脉的一幕,与我认知里的历史剧本,格格不入。它像一颗投入静水里的石子,扰乱了原本清晰的倒影。
直到奶奶去世后,有一次与父亲闲聊,我又提起了这个话题。“爸,当年日本兵来咱们村,到底杀没杀人?”
父亲磕了磕烟灰,眼神望着远处,沉默了片刻。“杀了一个。”他说,“村东头的那个打铁匠,人长得高大粗壮些。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日本兵走过去,一句话也没有,端起刺刀,就那么一下,就给刺死了。”
他描述得极其简洁,没有任何渲染,却让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没有理由,没有对答,就像一个随意的、漫不经心的动作,一条鲜活的人命便如草芥般被抹去。父亲最后叹了口气,喃喃道:“日本人,太鬼了……”
我忽然明白了。那偶尔施舍的“肉丸子”,与这随意挥出的“刺刀”,并非矛盾,而是一体两面。它恰恰揭示了那种更深层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本质:他们可以在你的土地上,一面进行着最极致的、非人的残暴,一面却又偶发性地、施舍般地流露出一点近乎虚伪的“温情”。这种“温情”不是仁慈,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残酷,它模糊了善恶的边界,混淆了受害者的感知,甚至企图在事后瓦解你控诉的纯粹性。这比单纯的恶,更显得阴森可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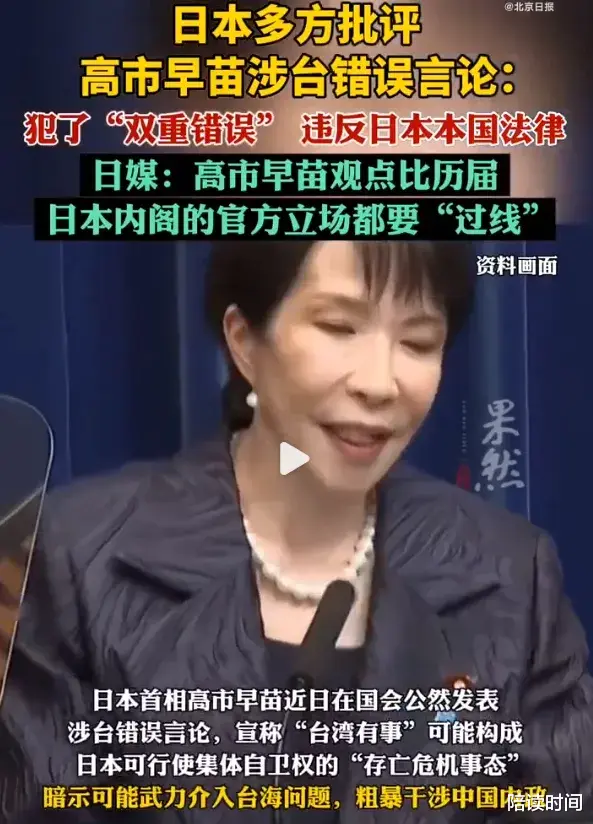
这让我想起山野间的一种经验。越是毒性剧烈的蛇,其斑纹往往越是艳丽夺目;而真正致命的陷阱,也常常覆盖着繁花与绿茵。这或许是一种属于岛国的、极端环境孕育出的生存哲学,一种将菊与刀、礼与虐奇妙地融于一体的民族性。表面上,他们可以鞠躬如仪,秩序井然,呈现出一种近乎洁癖的文明姿态;但其内在,却可能潜藏着对力量绝对的崇拜,以及对生命极端的漠视。我们必须警惕的,正是这种表里不一的“花哨”,这种深入骨髓的“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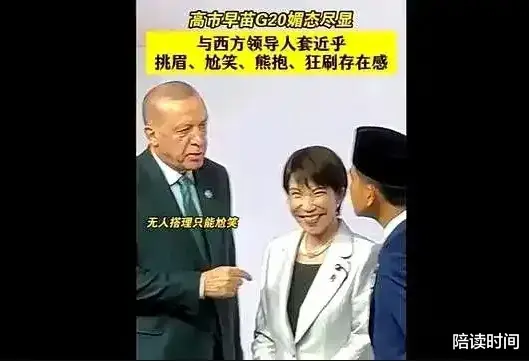
历史的书页,是由无数个体的记忆装订而成的。有些记忆,是影院银幕上巨大的、不容置疑的集体呐喊;有些记忆,是祖母口中那个在极致饥饿下咽下的、味道不明的肉丸子;还有些记忆,是父亲眼里那个无声倒下的、无辜的打铁匠。这些记忆叠加在一起,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才构成了历史的全部重量。
我们铭记仇恨,不是为了延续仇恨的循环,而是为了认清仇恨的根源。我们讲述苦难,不是为了浸泡在泪水里,而是为了从苦难中淬炼出清醒的认知与不屈的脊梁。

那句来自东邻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我们听来,之所以如此刺耳,正是因为它轻易地拨动了那根深植于我们血脉中的、由无数惨痛记忆拧成的警惕之弦。它提醒我们,豺狼的秉性或许从未改变,只是有时会披上文明的外衣。
奶奶吃下的那个肉丸子,父亲口中的那个打铁匠,以及银幕上那些飘向天空的婴儿……所有这些,都是这记忆重量的一部分。它们沉甸甸地压在我们这一代,以及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上。

这重量,让我们无法轻信,无法忘却,更无法低头。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脚下的土地,来之不易;而觊觎的目光,从未远离。我们唯有更强,更清醒,才能让那样的苦难,永远成为历史的回响,而非未来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