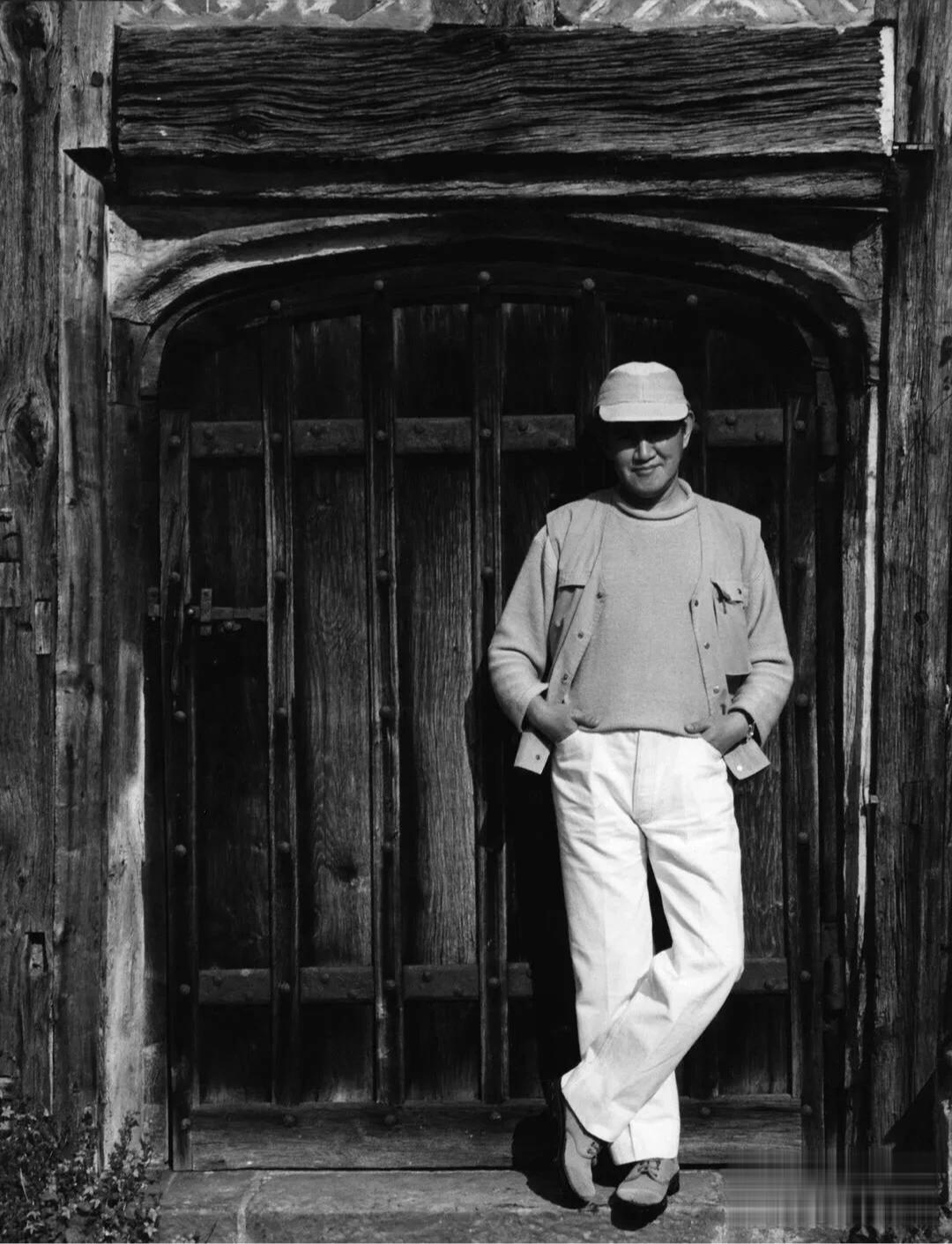嫡姐及笄礼那晚唤我去把脉。
我的手指搭上她皓腕的瞬间,清晰的滑脉如擂鼓般敲在指尖。
我正要开口说出喜脉,眼前却突兀闪过一行半透明的字:
“别说!她要嫁太子,怀的却是别人的娃!”
01
嫡姐苏清容及笄礼那晚说身子不适,悄悄让贴身丫鬟来唤我过去。
我走进她那间暖香浮动的闺房,看见她斜倚在贵妃榻上,锦缎裙裾在烛光下泛着柔滑的光泽,她伸出手腕时衣袖滑落,露出一截皓腕和那只从不离身的羊脂玉镯。
我把手指轻轻搭在她的脉上,片刻之后心中猛然一震,那清晰的滑脉如同擂鼓般敲在我的指尖。
我下意识抬起眼,正对上她看似平静却暗含审视的目光。
话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因为我注意到她身后那个叫碧荷的大丫鬟,右手正若无其事地搭在腰间的荷包上,那荷包里隐约露出一截匕首的轮廓。
“长姐近来可是食欲不振,晨起时尤为不适?”我收回手,语气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惊讶,“脉象上看是脾胃受了些寒湿,加之最近天气反复,才会如此。”
苏清容似乎松了口气,唇角勾起一抹浅笑:“果真如此?我还当是什么大病。”
“我开一副温中和胃的方子,长姐连服三日便好。”我走到桌边铺开纸笔,写下几味再普通不过的药材,其中却暗含能暂时压制孕相的白芍和川断。
写完方子,我借口夜深告退,踏出房门时夜风一吹,才发觉后背的衣裳已经汗湿了一片。
回到自己那间偏院的小屋,我闩上门,从袖中摸出一样东西——那是苏清容刚才用过的茶盏,我趁她不注意时用帕子包了藏入袖中。
此刻对着烛光细看,杯沿内侧残留着极淡的褐色药渍。
我凑近轻嗅,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杏仁味。
这是避子汤的味道,而且药材用得极猛,若非体质特殊,恐怕早就伤及根本。
难怪她要找我诊脉。
正思忖间,窗棂忽然传来极轻的叩击声。
我推开窗,外面空无一人,窗台上却多了一方折好的素笺。
展开后,上面只有一行小字:“勿言喜脉,香囊藏毒,速寻解药。”
字迹潦草,墨色尚新。
我心头一凛,立刻从怀中取出苏清容前几日赏我的那只海棠纹香囊——当时她笑着说里头装的是安神的香料,让我随身戴着。
我用银剪小心拆开香囊,倒出里头的干花和香料,指尖拨开层层花瓣,果然在底部摸到一小包用薄绢裹着的暗黄色粉末。
我用银簪挑起些许,簪尖立刻泛起一层不自然的乌青色。
是“七日醉”,南疆传来的秘毒,混在香料中无色无味,吸入七日后会心悸而亡,死后查不出痕迹。
我捏着那包毒粉,指尖冰凉。
02
我把香囊原样封好,假装什么都没发现,然后翻出母亲留下的那只旧樟木箱。
母亲曾是名动江南的女医,五年前因一场时疫病逝,留下的医书药典装了满满三箱。
我在最底层的夹层里找到一本页面泛黄的《南疆毒物辑录》,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正绘着“七日醉”的图文。
解药名为“七心丹”,需以七日莲为主材,配以六味辅药炼制。
书页边缘有母亲娟秀的批注:“七日莲生于极阴之地,京中唯两处可见,一为东宫暖阁药圃,二为城南鬼市药铺‘回春堂’,然此花十年一开,价逾千金。”
我合上书,窗外天色已经泛白。
次日一早,我叫来从小跟着我的丫鬟兰心,低声嘱咐她去城南鬼市打听,就说家中有人中了热毒,急需七日莲入药,无论价格多高都先记下来。
兰心应声去了。
我又想起母亲生前最信任的旧仆孙嬷嬷,如今在城西的庄子上养老。
午后我借口要去庙里上香,乘一顶青布小轿出了侯府,在城西的静安寺后门悄悄见了孙嬷嬷。
几年不见,她头发已经花白,见了我便红了眼眶,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
寒暄几句后,我问起母亲去世前的事。
孙嬷嬷抹了抹眼角,压低声音说:“姑娘,有件事老奴憋在心里五年了。夫人走前那几日,曾瞧见大夫人身边的周嬷嬷,深更半夜和一个面生的婆子在角门说话,那婆子手里还抱着个包袱。”
“包袱?”我追问。
“看不清里头是什么,但形状……像是个襁褓。”孙嬷嬷声音更低了,“没过两日,夫人就染了疫病被移去废院,老奴想送药进去,守门的婆子死活不让,说是大夫人的吩咐。”
我心里一沉,又问:“母亲可曾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
孙嬷嬷想了想:“夫人临终前给了老奴半块玉佩,说是将来若姑娘问起,便交给姑娘。”她从贴身内袋里取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头是半块雕着龙纹的羊脂玉佩,断口处参差不齐,像是被硬生生掰开的。
我接过玉佩,触手温润,玉质极好,绝非凡品。
“嬷嬷可知这玉佩的来历?”
孙嬷嬷摇头:“夫人只说,这玉关系着姑娘的身世,另一半在何处,她也不知道。”
我把玉佩仔细收好,又给了孙嬷嬷一些银钱,嘱咐她保重身体,这才匆匆离开。
03
回府后没两日,兰心从鬼市带回消息,说回春堂的掌柜透露,三日后会有一株七年生的七日莲拍卖,起价一千五百两,而且已有好几家暗中打听过了。
一千五百两,对我来说是天价。
我这些年攒下的月例和母亲留下的体己,加起来也不过二百两。
正发愁时,苏清容那边又有了新动静。
我买通她院里一个负责洒扫的小丫头杏儿,得知苏清容最近常在夜里偷偷收拾首饰细软,还让碧荷去外头打听租船的事。
杏儿说,她听见大姑娘和碧荷低语,提到了“三日后”、“贤藏街”和“宋公子”。
宋公子,指的是礼部侍郎府的二公子宋谨言,一个才华出众却因庶出身份屡遭压制的年轻人。
苏清容和他,竟已到了要私奔的地步。
我思忖片刻,转身去了父亲的书房。
父亲永恩侯苏怀远正在练字,见我来了有些意外。
我行礼后忧心忡忡地说:“父亲,女儿今日听外头采买的婆子说,近来京中不太平,有好几户官宦人家遭了贼,专挑夜深时动手,女儿担心府中安危,特来提醒父亲。”
苏怀远放下笔,眉头微皱:“确有此事?”
“女儿不敢妄言,父亲可派人打听。”我顿了顿,“尤其是西侧门那边,临着巷子,更要加派人手。”
苏怀远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知道了,你退下吧。”
第三日夜里,果然出了事。
那晚父亲原本在吏部侍郎府赴宴,据说宴至中途忽然心悸不适,提前乘马车回府。
车行至贤藏街附近时,车夫说看见巷口有两个人影拉扯,其中女子的身影很像大小姐。
苏怀远命停车查看,结果正好撞见苏清容提着包袱,和一个青衣书生站在巷子深处。
那书生正是宋谨言。
场面一时僵住,苏清容脸色煞白,宋谨言则迅速松开了拉着她的手,后退半步,躬身行礼:“晚生见过侯爷。”
苏怀远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苏清容:“你……你这孽障!深更半夜在此作甚!”
苏清容咬了咬唇,忽然跪下:“父亲,女儿与谨言两情相悦,求父亲成全!”
“成全?”苏怀远怒极反笑,“你可知你是太后亲指的太子妃?私奔乃是死罪,还要牵连全族!”
宋谨言这时开口,声音平静却疏离:“侯爷息怒,晚生与苏小姐只是偶遇,说了几句话而已,绝无私奔之意。晚生这就告辞。”说罢竟真的转身就走。
苏清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的背影,眼泪夺眶而出。
就在这时,街角又驶来一辆马车,四角悬着的琉璃灯在夜色中格外醒目。
马车在众人面前停下,帘子掀开,露出一张清俊而淡漠的脸。
正是当朝太子萧景昀。
04
萧景昀的目光在苏清容泪痕斑驳的脸上停留片刻,又扫过苏怀远铁青的脸色,最后落在我身上——我因为不放心跟了过来,此刻正站在父亲身后。
“侯爷,深夜在此,可是府中出了事?”萧景昀的声音听不出喜怒。
苏怀远连忙躬身:“惊扰殿下,是臣管教不严,小女……小女偶感风寒,臣带她出来寻医。”
这借口拙劣得连我都不信。
萧景昀却并未戳穿,只淡淡道:“既然如此,便早些回府吧。对了,三日后宫中选秀,侯府应有女儿参选?”
苏怀远额角渗出冷汗:“是……小女清容……”
“孤记得,侯府还有一位女儿,与大小姐是同日所生?”萧景昀忽然问。
苏怀远愣了一下,忙道:“是,是臣的次女,苏棠音。”
萧景昀的目光第二次落在我身上,这次停留得更久了些,然后他点点头:“甚好,选秀那日,孤希望两位苏小姐都能到场。”
帘子放下,马车缓缓驶离。
回府的路上,车厢里死一般寂静。
苏清容一直在低声啜泣,苏怀远闭目不语,脸色阴沉得可怕。
一到侯府,苏清容就被关进了祠堂思过,苏怀远则把我叫到书房。
他盯着我看了许久,才开口:“棠音,今日之事你也看见了。清容她……恐怕不能嫁入东宫了。”
我垂首:“女儿明白。”
“但太子妃之位,必须出自苏家。”苏怀远的声音带着疲惫,“三日后选秀,你若能被选中,我便将你母亲记入族谱,归还她所有嫁妆,还会给你弟弟请最好的先生。”
我抬起头,看见父亲眼中交织着算计、愧疚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
“女儿愿意为父亲分忧。”我轻声说。
苏怀远松了口气,从抽屉里取出一枚乌木令牌递给我:“这是东宫的通行令,若遇到紧急情况,或许能用得上。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保住侯府,就是保住你自己。”
我接过令牌,触手冰凉。
从书房出来,我去了库房,将母亲留下的几件贵重首饰包好,让兰心悄悄拿去典当。
无论如何,我要先拿到七日莲,解了身上的毒。
选秀前一日,兰心带回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七日莲拍到了,花了整整两千两。
坏消息是,鬼市的规矩,交易双方不见面,药材三日后才能拿到。
而我的毒,还剩四日发作。
05
选秀那日,宫中派来的马车一早就候在侯府门外。
苏清容从祠堂放了出来,换上一身浅碧色宫装,脸色苍白,眼下有着淡淡的青影。
她看到我时眼神复杂,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上了前面的马车。
我跟在后面,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海棠香囊——毒未解,我只能继续戴着它,以免打草惊蛇。
进宫的路很长,马车在青石板路上碾出单调的声响。
透过纱帘,我看见宫墙越来越高,朱红的宫门次第打开,将我们吞进这座天下最华丽的牢笼。
选秀设在储秀宫,几十位官家小姐依照家世品级排列,我和苏清容站在前列。
太后、皇后和几位高位妃嫔端坐殿上,太子萧景昀坐在太后下首,神色淡然地看着台下。
轮到苏家时,苏清容上前行礼,姿态优雅无可挑剔。
皇后问了她几句诗书女红,她都答得流畅得体。
就在我以为一切顺利时,一直沉默的萧景昀忽然开口:“苏小姐近日似乎清减了不少,可是身体不适?”
苏清容指尖微颤,勉强笑道:“谢殿下关怀,只是夏日炎炎,食欲稍差。”
“既如此,不如请太医诊个脉,也好安心。”萧景昀说着,示意身后的宫人,“去请王院判来。”
苏清容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我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能清楚地看见她袖中的手在发抖。
王院判是太医院院使,专精妇科,若让他诊脉,喜脉之事绝对瞒不住。
电光石火间,我上前半步,在苏清容耳边极轻地说:“长姐莫慌,呼吸放缓。”
同时,我借着衣袖遮挡,将一枚小小的药丸塞进她掌心——这是我用最后一点药材赶制出的“乱脉丹”,服下后一个时辰内脉象紊乱,难以诊断。
苏清容怔了一下,随即迅速将药丸含入口中。
王院判很快就到了,请苏清容到偏殿诊脉。
约莫一炷香后,他回到正殿,躬身回禀:“苏小姐脉象弦滑,似有肝气郁结之症,需静养调理,并无大碍。”
萧景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再追问。
选秀继续进行,轮到我的时候,太后多看了我两眼,问:“你与清容是姐妹?”
“回太后,臣女是庶出,长姐为嫡。”我垂首应答。
“抬起头来。”
我依言抬头,太后端详片刻,笑道:“眉眼倒有几分像你母亲,当年她在京中行医,哀家还找她看过诊。”
我心中一动,正要说话,太后却已转向萧景昀:“昀儿觉得如何?”
萧景昀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平静无波:“尚可。”
便是这两个字,决定了我接下来的命运。
选秀结束,苏清容被留在宫中“学规矩”,而我则被指为太子侧妃,三个月后入东宫。
出宫时,苏清容在宫门口追上我,将一个绣着竹叶纹的香囊塞进我手里,声音哽咽:“棠音,把这个交给谨言……告诉他,我等他。”
我握着尚带她体温的香囊,点了点头。
马车驶离宫门,我拆开香囊,里面没有香料,只有一封信和一枚私章。
信上是苏清容的字迹,写满了对宋谨言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字字泣血。
而私章上刻着“谨言”二字,边缘已经摩挲得光滑。
我收好香囊,掀起车帘望向窗外。
宫墙巍峨,暮色渐浓,远处的殿宇飞檐在夕阳中勾出冰冷的轮廓。
兰心在府中等我,一见我就迎上来,压低声音说:“姑娘,孙嬷嬷让人捎信来,说找到当年那个接生婆了,人在城北的慈安堂,病得很重,怕是撑不了几日。”
我脚步一顿:“备车,现在就去。”
“可现在天色已晚,侯爷那边……”
“就说我去庙里还愿。”我打断她,转身朝侧门走去,“有些事,再不问就来不及了。”
马车驶入渐浓的夜色,车辙碾过长街,声音沉闷而绵长。
我不知道慈安堂里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三个月后踏进东宫,又会面对怎样的命运。
但我知道,从母亲死去的那一天起,从我戴上那个有毒的香囊起,从我接过那半块玉佩起,我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路还很长,夜还很深。
而我要的答案,或许就在下一个黎明。
06
慈安堂是城北一间破旧的小庙堂,收容的多是无家可归的病弱老人,空气里常年弥漫着草药与腐朽混合的气味。
孙嬷嬷已在后院的厢房外等我,她指了指虚掩的木门,低声说:“就在里面,神智时清醒时糊涂,姑娘抓紧问。”
我推门进去,屋里只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昏暗。
靠墙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干瘦的老妇人,头发稀疏花白,双眼浑浊地望着屋顶,嘴里含糊地念叨着什么。
我走到床边,孙嬷嬷跟进来,凑近老妇人耳边提高声音说:“陈婆婆,您看看,这是当年林大夫的女儿,她来看您了。”
陈婆婆缓慢地转动眼珠,目光落在我脸上,看了很久,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连忙扶她半坐起,喂她喝了点温水。
等她喘匀了气,那双浑浊的眼睛忽然清明了一瞬,她盯着我,哑着嗓子问:“你……你是阿芷的女儿?”
阿芷是我母亲的闺名。
我点头:“是,我是棠音。”
陈婆婆伸出枯瘦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
她凑近我,压低声音,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当年……侯府夫人生的……其实是个死胎。”
我浑身一僵。
“夫人怕失宠,就让老身去外面抱个健康的女婴回来顶替。”陈婆婆急促地喘着气,“老身当时在城外卖豆腐,正好碰上逃难来的一个年轻妇人,她怀里抱着个刚出生的女娃,自己快不行了,求老身给孩子找个活路。”
“那妇人……长什么样?”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记不清了,就记得她脖子上挂着半块玉佩,和你娘后来给我的那半块……一模一样。”陈婆婆说完这句,像是用尽了力气,瘫回床上,又开始含糊地念叨起来。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苏清容,竟然不是侯府真正的嫡女。
而我那半块玉佩,原来不是母亲的,是我亲生母亲的遗物。
“姑娘,您没事吧?”孙嬷嬷担忧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从荷包里取出几粒碎银子放在陈婆婆枕边,转身走出厢房。
夜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兰心在马车边等着,见我脸色不对,没敢多问,只默默掀开车帘。
回府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半块玉佩,想母亲从未提起过的身世,想苏清容那个可笑的太子妃梦。
如果她不是真正的侯府嫡女,那太后当年的指婚,根本就是个笑话。
而我这个庶女,反而可能是某个落魄家族真正的血脉。
这个秘密,现在只有我知道。
07
三日后,兰心终于从鬼市拿回了那株七日莲。
花瓣是罕见的浅金色,七片叶子舒展开,在昏暗的室内散发着淡淡的莹光。
我连夜按母亲医书上的方子配药,将七日莲与其他六味药材一起放入药罐,文火慢煎了整整六个时辰。
天亮时,药成了,是一碗浓稠的琥珀色汤药。
我端起药碗,一口气喝了下去。
药很苦,苦得我眼泪都要流出来。
但喝下去没多久,心口那种隐隐的窒闷感开始缓解,指尖也不再发麻。
解药见效了。
我活下来了。
与此同时,宫里传来消息,苏清容在学规矩时晕倒了。
太医诊断说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皇贵妃便恩准她回府休养几日。
苏清容回府那天,脸色比之前更差,整个人瘦了一圈。
她看到我时,眼神躲闪,匆匆回了自己的院子。
我让兰心暗中留意她院里的动静。
果然,当天下午,碧荷就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去了城东一家不起眼的茶楼。
兰心跟去看了,回来告诉我:“姑娘,碧荷见了宋公子身边的小厮,递了个包袱过去,里面好像是些首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