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文译文如下:
长山有位姓安的老人,生性喜爱从事农业劳作。到了秋天,荞麦成熟,他让人把收割下来的荞麦堆在田埂边。当时附近村子有偷盗庄稼的人,安翁于是吩咐佃农趁着月色用车子把荞麦运到晒谷场,等佃农装车返回后,自己留下来巡逻守卫。随后他就枕着兵器躺在露天里。

眼睛刚有些闭合,忽然听到有人踩在荞麦根上发出 “咋咋” 的声响。安翁心里怀疑是强盗,急忙抬头,却看见一个大鬼,身高一丈多,红头发,胡须蜷曲浓密,距离自己已经很近了。他极度恐惧,来不及想别的办法,猛地起身,狠狠用兵器刺向大鬼。大鬼发出像雷声一样的叫声后消失了。安翁担心大鬼再回来,就扛着兵器返回。他在途中遇到佃农,把自己看到的情景告诉了他们,并且告诫大家不要前往晒谷场。众人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

过了一天,众人在晒谷场晾晒麦子,忽然听到天空中传来声响。安翁惊恐地说:“鬼怪来了!” 于是拔腿就跑,其他人也跟着跑。过了一会儿,大家重新聚集起来,安翁命令设置多副弓箭来防备鬼怪。又过了几天,鬼怪果然又来了,众人一起射箭,那怪物害怕地逃走了。之后两三天,鬼怪终究没有再出现。

麦子已经收进粮仓,田间残留的禾秆杂乱堆积,安翁吩咐把这些禾秆收拢起来堆成垛,并且亲自爬上去把禾秆踩结实,堆到几尺高。忽然他向远处望去,惊恐地大喊:“鬼怪来了!” 众人急忙寻找弓箭,那怪物已经朝安翁冲了过来。安翁被扑倒在地,怪物咬下他的额头后离开。大家一起上前查看,发现安翁的额头被咬掉了手掌大小的一块骨头,他已经昏迷不醒。众人把他背回家中,不久安翁就去世了。后来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个鬼怪,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怪物。

《聊斋志异・荞中怪》篇幅虽短,却情节紧凑、充满奇幻色彩。故事开篇,主角张某在田间种植荞麦,一日夜间发现荞麦地里常有怪异动静,不仅荞麦秆频繁倒伏,还伴随不明声响,扰得他心神不宁。张某起初怀疑是田鼠、野兔之类的野兽作祟,便深夜潜伏在田边观察,却意外撞见一个 “身如簸箕,目似灯笼” 的怪物 —— 它通体覆盖着细密的绒毛,行动时悄无声息,专挑成熟的荞麦啃食,所过之处荞麦秆尽数折断。

张某惊恐之下不敢贸然上前,次日召集乡邻一同查看,却只见到满地狼藉的荞麦地,怪物踪迹全无。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 “山精作祟”,也有人觉得是 “天地异象”,建议张某祭拜祈福。张某半信半疑,按照乡邻的说法在田边摆放祭品,可当晚怪物依旧出现,甚至将祭品也一并席卷而去。无奈之下,张某只得求助当地一位颇有见识的老秀才,老秀才推测怪物是 “荞麦之精”,因张某今年荞麦长势过盛,又未及时收割,精气凝聚而成,只需尽快将荞麦收割,怪物便会自行消散。张某依言而行,连夜组织人手收割荞麦,次日清晨,怪物果然消失不见,此后荞麦地再无异常。
三、内涵
1. 人与自然的 “平衡之道”
故事中 “荞麦之精” 的出现,本质是人与自然失衡的象征。张某因荞麦丰收而拖延收割,导致地里的 “精气” 过剩,最终孕育出怪物 —— 这一设定暗含蒲松龄对 “人与自然关系” 的思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需有 “度”,过度贪婪或忽视自然规律,终将引发反噬。在现代社会,这一思考仍具现实意义:从过度砍伐导致的水土流失,到过度捕捞引发的海洋生态危机,人类对自然的 “无度索取”,不正是现实版的 “养怪”?而故事中 “收割荞麦以除怪” 的解决方案,也隐喻着 “尊重自然规律、及时修正行为” 才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键。

2. 对 “未知恐惧” 与 “盲目迷信” 的批判
故事里,乡邻面对怪物时的反应极具代表性:有人因 “未知” 而恐慌,有人将其归为 “神明惩戒”,主张用祭品祈福 —— 这种 “遇怪即拜” 的盲目迷信,恰恰是蒲松龄批判的对象。老秀才并未被 “怪力乱神” 的表象迷惑,而是从 “荞麦生长规律” 出发分析问题,最终找到解决办法,这一对比鲜明地传递出 “理性思考胜于盲目迷信” 的观点。反观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少人面对未知事物时,习惯用 “玄学”“迷信” 解释,忽视科学与理性,《荞中怪》的故事恰似一面镜子,照见这种思维的局限。

3. “小隐患酿大问题” 的警示
怪物并非一开始就出现,而是在张某拖延收割、荞麦 “精气过剩” 后才成型 —— 这一细节暗藏 “小隐患不及时解决,终将酿成大麻烦” 的警示。从个人生活中的 “拖延症”,到社会治理中的 “小问题忽视”,许多困境的产生,都源于对 “小隐患” 的轻视。正如荞麦地里的 “怪”,若张某在荞麦成熟初期便及时收割,便不会有后续的恐慌与损失,这也提醒我们:对待问题需 “防微杜渐”,莫等 “小患成大怪” 再追悔莫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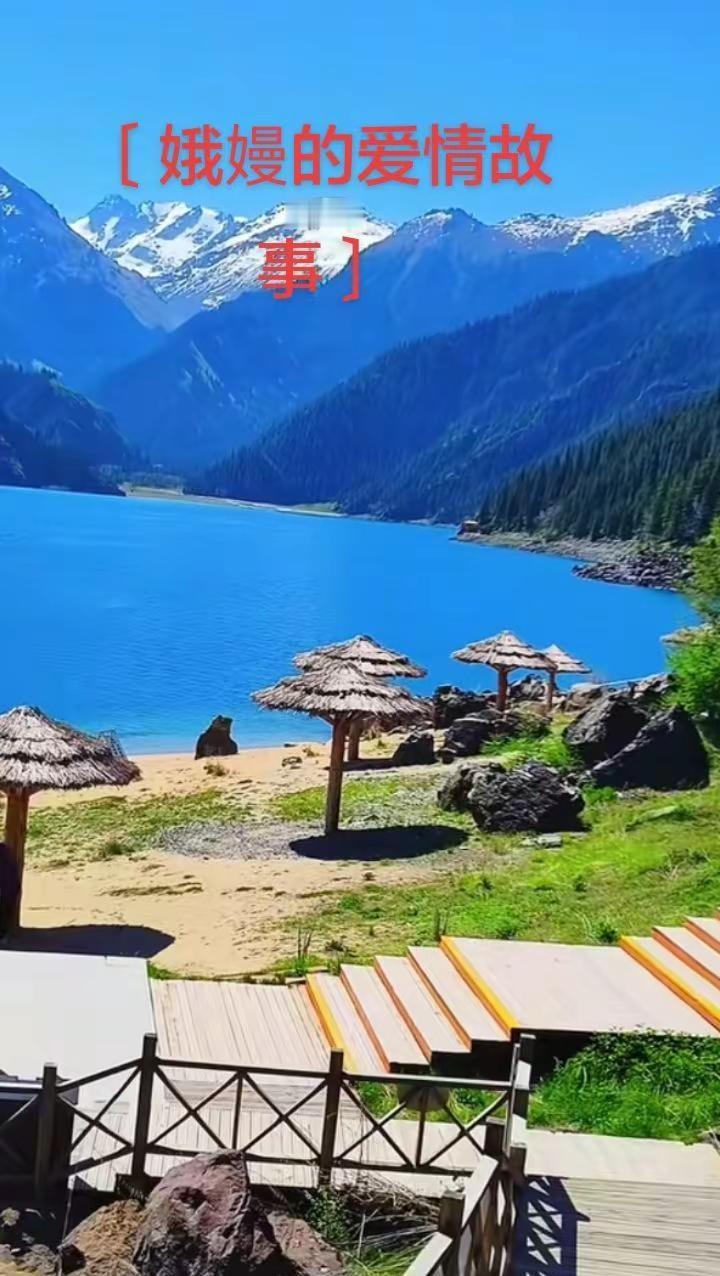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