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岁的莫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到一名男教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但莫言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窥探,竟断送掉自己升中学的机会。而且,这一辍学就是17年!
60年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变了,学校里不光教书,还得搞各种活动,学生们忙着干这干那,书本知识反倒放一边。莫言12岁那年,正上小学五年级,成绩好,眼瞅着能升中学,家里也攒了点希望。可谁也没想到,一件小事彻底把他的人生轨迹给改了。 那是在1967年秋天,村里学校跟全国一样,热火朝天地搞活动。学生们被要求凑钱买红袖标,算是响应号召。莫言攒了八毛钱,买了个红底黄字的袖标,套在胳膊上满村跑,觉得特神气。可没过两天,他发现姐姐的袖标是红绸子做的,上面黄丝线绣的字,漂亮得不得了,关键才花了五毛钱。莫言心里犯嘀咕,这多出的三毛钱哪儿去了?更让他起疑的是,每天放学后,学校办公室总飘出炒花生的香味。那年头,粮食紧缺,普通人家吃饱饭都难,花生可是稀罕货。莫言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怀疑管钱的几个老师把学生们的钱拿去买花生吃了。这事儿在他心里埋了个疙瘩,总觉得老师们不地道。 有一天晚上,学校安排莫言去干点杂活,天已经黑了。他路过老师办公室,闻到那股熟悉的花生味儿,忍不住凑过去瞧瞧。办公室窗户上糊着纸,有个小洞透着光。莫言踮起脚,凑近一看,里头一个男老师正一边吃花生,一边往年轻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笑得前仰后合,声音特别响。莫言年纪小,看不懂这算啥,但直觉告诉他,这事儿不正经。老师们白天一本正经,晚上却这么闹腾,还吃着学生们可能被克扣的钱买来的花生,莫言心里挺不是滋味。 第二天,他没忍住,把这事儿跟同学张立新说了。张立新是个胆大爱画画的家伙,听完就来了劲儿,跑到村里大队的一面白墙上,刷刷几笔画了幅漫画。画上男老师一脸坏笑,手里抓着花生往郑红英衣服里塞,郑红英笑得花枝乱颤。画得夸张又生动,村里人围着看,议论纷纷,有的笑出声,有的摇头叹气。这幅画让郑红英成了村里的笑柄,她的名声算是栽了。莫言虽然没动手画,可他是“情报源”,郑红英很快猜到是他捅了娄子。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一年后,1968年,村里办了农业联合中学,算是给小学毕业生一个继续读书的机会。莫言那年正好小学毕业,成绩没得说,家里也盼着他能上中学。张立新家是烈属,背景硬,没人敢拦他,顺利入学。可莫言家是中农,身份不上不下,升学得看老师和村干部的脸色。郑红英这时候在学校有点话语权,她抓着机会,直接说政策规定中农的孩子只能读到小学,没资格上中学。莫言姐姐去求情,也被她一口回绝。就这样,莫言的升学路被堵死了,13岁的他只能放下书包,去公社当小社员,干起了放牛的活儿。每次赶着牛从中学门口过,他都不敢抬头,怕听见教室里传出的读书声。 辍学对莫言打击不小,家里人也跟着受累。农村那会儿,读书是少数能跳出农门的路,莫言这一停学,家里人觉得前途暗了。他知道自己闯了祸,招惹了郑红英,害得自己没学上,还让家里抬不起头。可他没放弃读书的心,晚上常点着油灯,偷偷看哥哥的初中课本,抄写课文,学数学,啥都啃。村里人看他放牛还带本书,都说他是个怪小孩。1973年,莫言去了县里的棉花厂当工人,填履历表时,他硬着头皮写上“初中一年级”,想给自己加点分。可厂里有人认识他,戳穿了这事儿,莫言臊得脸通红。 1976年,莫言参了军,征兵表上又写“初中二年级”,觉得自己这些年自学了不少,勉强算得上这水平。部队生活让他接触到更多书,尤其是文学作品,他开始试着写点东西。198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总算在文学路上迈出一步。部队里没人深究他的学历,他也默认自己是“高中生”,但每次填表,他都捏把汗,怕露馅。这么多年,他一直为学历的事儿犯怵,觉得自己像在夹缝里讨生活。 到了1984年,莫言听说解放军艺术学院招文学系学生,报名已经截止了。他不甘心,带着自己写的小说,直接跑到北京找学校。教文学的徐怀中看了他的作品,觉得这年轻人有真才实学,当场拍板让他考试。莫言考了个高分,9月1日,他背着行李,正式走进军艺,成为货真价实的大学生。这一下,17年的学历阴影总算散了。从放牛娃到大学生,莫言靠着自学和倔劲,硬是闯出了一条路。 这17年,莫言吃了不少苦,但也攒下了宝贵的经历。他放牛时听村里老人的故事,棉花厂里看工友们的喜怒哀乐,部队里读名著、练笔头,这些都成了他后来写小说的养分。他的小说,比如《红高粱》《丰乳肥臀》,满是高密东北乡的烟火气,写尽了农民的苦乐和人性的复杂。2012年,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中国第一个获这奖的作家。村里人听说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年的放牛娃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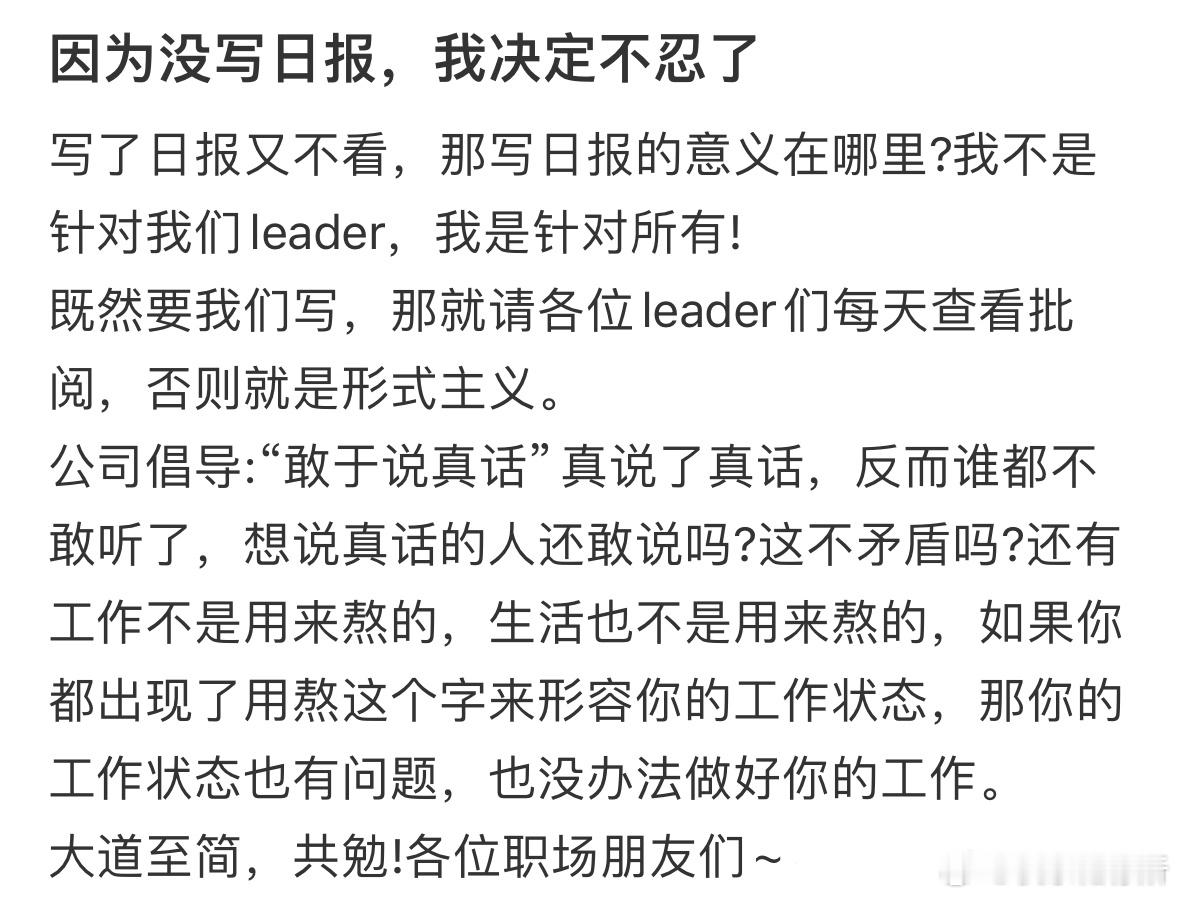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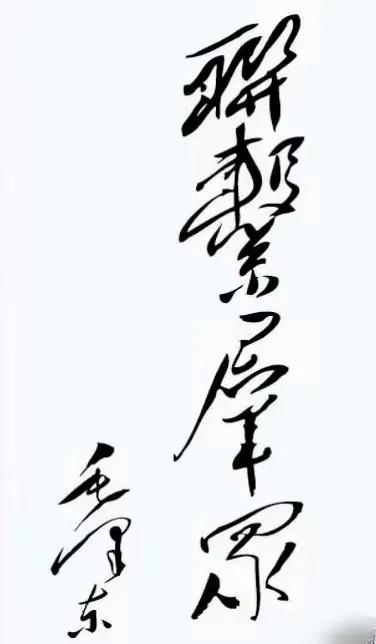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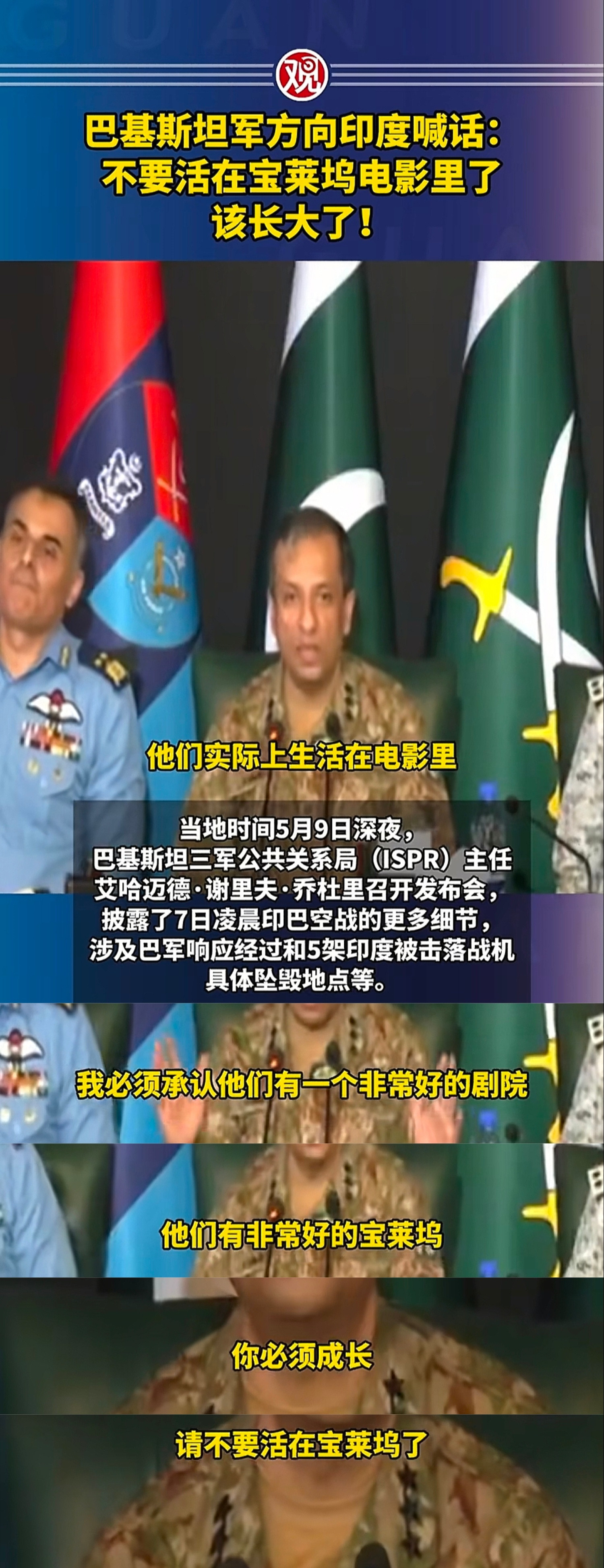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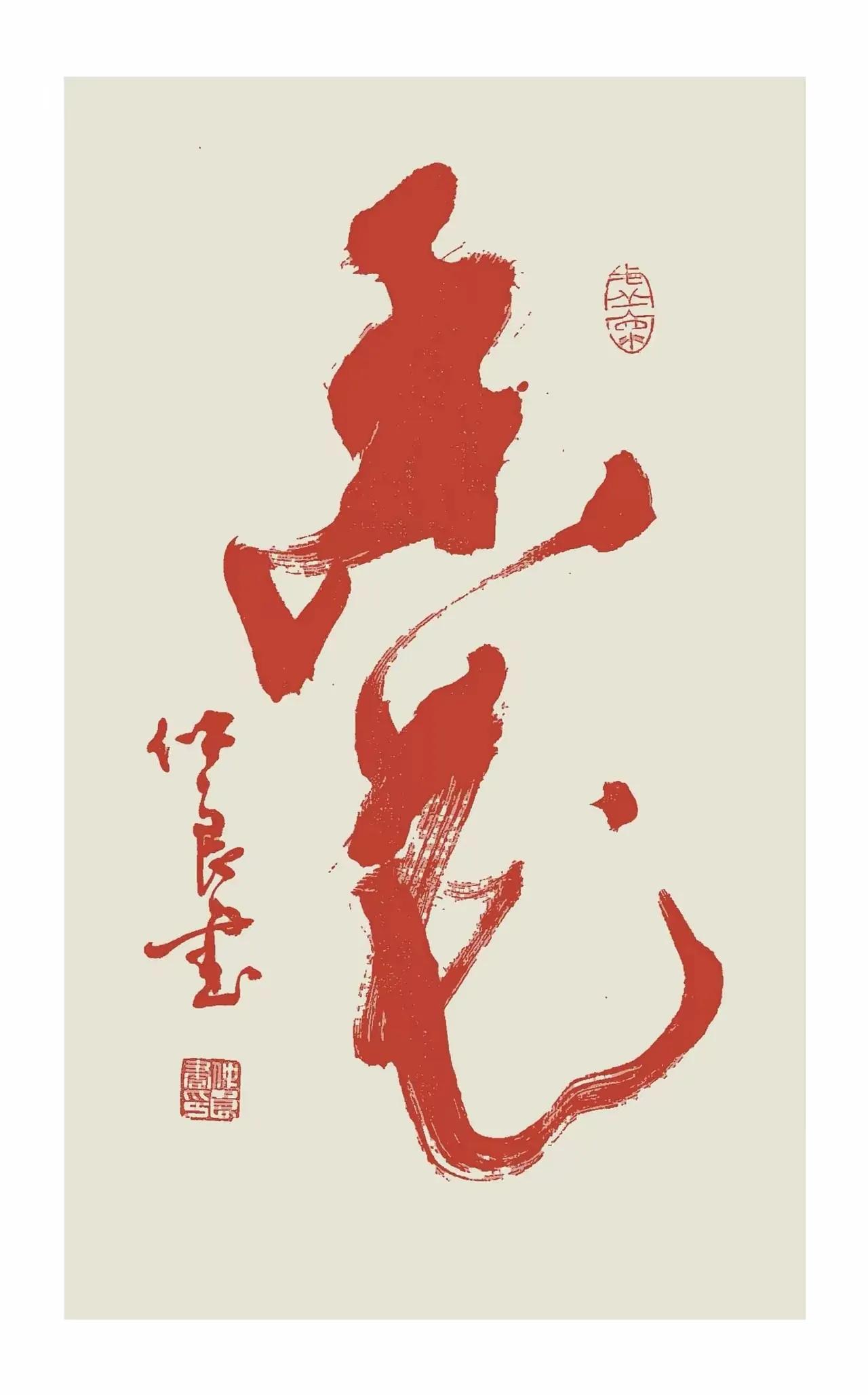


沧浪之水
学历造假,对体制内的人来说这是大事。况且通过这个假学历获利,依照《纪律处分条例》应当给予党内和政务处分,并撤销因此而得到的职务和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