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46岁的雍正翻牌子,手一抖翻到了48岁齐妃的牌子,太监忙咳嗽了一声:“皇上,后宫有一位25岁的舒舒觉罗氏刚安置好。”雍正听了头微微一抬说:“就她了!”
众所周知,雍正继承大统,史上一直有存疑,清史上发生了著名的“九子夺嫡”事件,说的就是这段。
雍正最初并没有把握能够胜出,因此在这段凶险的历程中,他先是低调蛰伏,观察各位皇子的动态,随后找准时机,心狠手辣、清除障碍,并迅速上位,他这番操作,着实让很多兄弟看的是目瞪口呆,恶从胆边生。
雍正清楚的知道,自己登基上位,必然会遭到其他兄弟的不服,想要坐稳江山,就顾不得兄弟情谊,因为“皇权天下”争的就是个你死我活。
康熙晚年,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此时胤禛、胤禩(八爷)、胤禵三人都从中嗅出机遇的味道,其中胤禵仗着从小深受康熙宠爱,呼声最高。
康熙为了锻炼胤禵,给他统管兵部,有一次准噶尔叛乱之际,康熙给了胤禵统兵十万,让其出任抚远大将军。
其实康熙的这种安排另有深意,但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要把胤禵作为继承人培养。因此即便同母的四哥胤禛,也难免对胤禵揣着一份防范之心,胤禵的确很优秀,这一番锻炼下来,军事能力尤为突出。
雍正上位后,最先打压的人是八王爷。八王爷败在了女人身上。
雍正登基之后,为了笼络人心,他先是将胤禩封为了廉亲王,后又特意昭告百官。在百官前来廉亲王府祝贺的时候,却被刚烈的八福晋关在了门外,八福晋一点情面不留地回复门外的官员们:“府中并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
这不是妥妥地打了皇上的脸面吗?雍正至此再也不能容忍这位八弟了,他搜罗了八王爷几年来谋逆的证据,比如谋害太子胤礽、居心叵测谋夺皇位等罪名。
雍正认为胤禩“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为我朝之玷”,还革除了胤禩的爵位,把他圈禁宗人府从族谱中除名,将胤禩的名字改为“阿奇那”。
清算完八王爷之后,雍正并没有饶过八王妃,勒令胤禩休妻。
处理完八王爷,还有一个最棘手的人物,就是雍正同母胞弟胤禵,前面我们说了,胤禵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甚至有野史中称,康熙原本要立的就是十四阿哥胤禵,后来遗诏被雍正篡改,成为了四阿哥胤禛。
因此登基后的雍正,怀着复杂的心情,还是对老十四下了手。登基第二天,雍正立即下旨降胤禵为贝子,并且收回抚远大将军的印信,与此同时雍正派出100多位御前侍卫亲自“保护”胤禵回到京城。
回京后的胤禵就和众家眷一起被软禁在家,此时十四阿哥心中郁闷,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侧福晋舒舒觉罗氏。舒舒觉罗氏是一个员外郎的女儿,但生的如花美眷,更兼知性美。深得老十四的喜爱。
康熙的灵柩下葬遵化景陵时,雍正终于可以安置这个十四弟了,为了提防胤禵和胤禩串通,他不顾太后反对,强制下令让胤禵去给康熙守陵。
老十四知道自己无回天之力,只提出要带走最心爱的女人舒舒觉罗氏,没想到雍正不仅连这个念想都给他掐灭了,还把这位弟媳接入宫中,做了自己的侍女。
太后心疼小儿子,于是,太后想了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挑选了一位貌美的宫女,由内务府送到雍正身边,替换掉舒舒觉罗氏。
雍正看到这位宫女后,立即明白了,雍正当即把宫女撵走,并说:你快回去,别逼朕杀你!
宫女吓得回禀太后,太后盛怒,亲自找到他说:“天下貌美女子多的是,你为何非要舒舒觉罗氏伺候?”
雍正反问太后:“额娘以为我是好色之徒?此女平日里教唆胤禵,我只不过要亲自管教罢了。”
雍正的确并非好色之徒,他一生勤政克己,皇后也仅有两位而已。而这次他把舒舒觉罗氏放在身边,却是别有一番用意。
最初舒舒觉罗氏对雍正是非常抗拒的,她认为雍正首先得位不正,其次不顾纲常人伦,把她从自己弟弟的手中抢过来,分明是个登徒子。
雍正自从把她接进宫来,常常召她深夜陪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舒舒觉罗氏发现雍正并非胤禵说的那样不堪,反而经常批阅奏折到深夜。
雍正感激地道:朕每天四更起身,做事要做到子时,胡乱睡一两个时辰,还常常半道里惊醒,身边连个说句话的人都没有。
朕每天批的奏章,最多的一万多字,最少的也有五六千字,每天接见众臣工有时接连十几起,朕为了什么,他们还要处处和朕拧着干,到处给朕出难题,说朕的坏话,你曾经是老十四的人,也是最恨朕的人之一。
朕把你留在身边,就是要让你看看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朝一日,朕放你出去,你要替朕说句公道话。”
据说舒舒觉罗氏伺候雍正的时间并不长,在太后去世后,雍正就放舒舒觉罗氏回家了,前后也就相处了一个多月。但这一个多月舒舒觉罗氏已经改变了对雍正的看法,雍正元年,胤禵和侧福晋舒舒觉罗氏的儿子弘春被雍正封为贝子。
从伦理上来说,雍正对自己弟弟的所做作为,的确难以自圆其说。但论皇帝政绩,勤政爱民的角度上说,雍正又的确是一位兢兢业业合格的帝王。这也许就是他留下舒舒觉罗氏的目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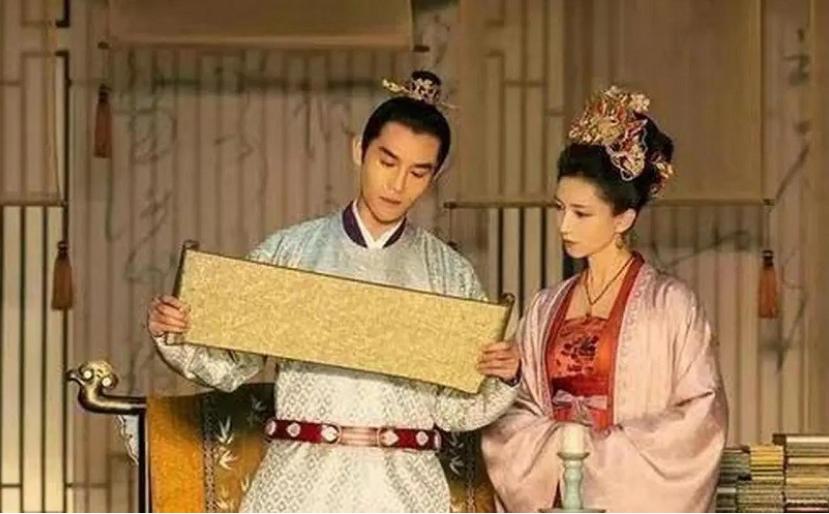

宇化贤
满清十大酷刑、闭关锁国、不思进取、文字狱、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驱使奴隶、鞑子一人管十家,银乱中国女子,欺男霸女、康熙乾隆六下江南挥霍奢靡、四库全书篡改禁毁15万册古籍、隐藏满清罪恶事实、抹黑明朝历史、禁锢思想、打断人民的脊梁骨、误人子弟,误导国人成为奴隶、阉割中华文明,使我国回到漆黑蒙昧的原始社会、凡有水旱,坐视不管、重徭役、纵贪官污吏,官以贿得邢以钱免,腐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国库空虚、圈地运动,百姓流离失所、民族压迫、宁与外邦不与家奴、割地赔款、不战而败、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百年屈辱、祸国殃民、扼杀维新、残暴专制、种族灭绝、赵州之屠、畿南之屠、潼关之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常熟之屠、四川大屠杀、金华之屠、南昌大屠杀、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汾州之屠、大同之屠、广州大屠杀、潮州之屠……几乎将明朝全境上下屠了个底朝天,整个华夏大地十室九空!中国文明领先世界几千年,直到满清统治时期才急剧衰落到世界贫穷国家。由于满清持续篡改两百多年的历史,很多罪恶都被掩盖!这些还只是已确认过的真实事件,不信的请自己先查一下有没有这些事再说。